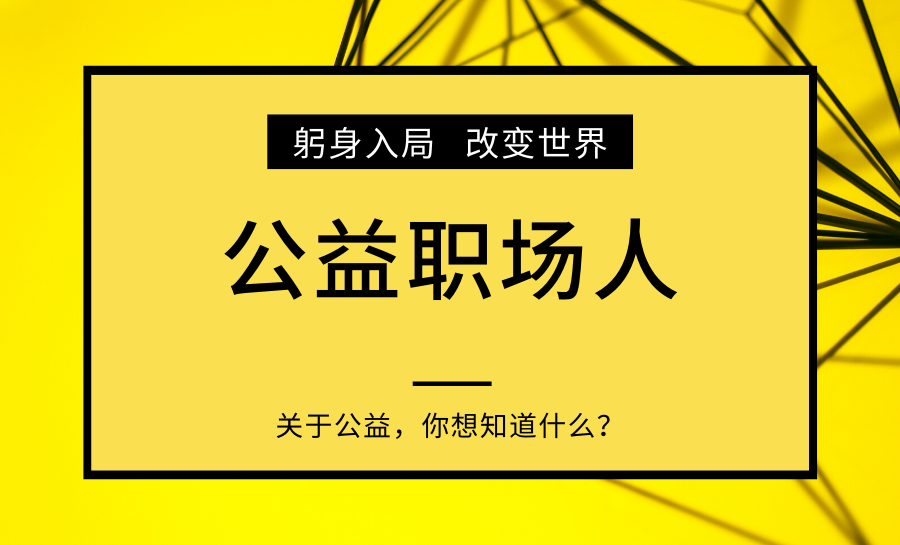2021-12-23
2021-12-23
 385
385其实思考这句话已经好几年了,最初听到类似的一句话是“理想人生的最后一份工作是投资”,当然我是不太认同的,直觉地感触是投资这项工作离人情味有点远,把它放在人生的终极追求上,终究是觉得不够温暖,尤其是在人之将死之际,一切物欲繁华看尽,内心深处更需要的应该是宁静与温暖。当然或许我的认识里有中国知识分子穷酸的老毛病,总是书写那些隐逸山林、自绝红尘的文人雅士。
随着年纪增大,又一个人的故事触动了我的灵魂,那就是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他有一个人生三大不幸的名言:第一大不幸是年幼时出生优渥,未能吃上苦;第二大不幸是青年时,未经努力就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第三大不幸是临终时,未把财富回馈给社会,可耻地巨富而死。卡耐基说出这样的话,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富人才有说出如此高调言论的权力,对于平凡的普通人,他们即便保有一个以善业为终的愿望,又有何种条件可以实现呢?
年纪再增大,又一个人的事迹再次触动了灵魂,那就是台湾的证严法师,集合妇女们用每日菜钱里节约的分分钱,汇集起来去帮助穷人。对于普通妇女而言,分分钱无伤大雅,但汇聚的人越来越多,能帮助的人和事就叹为观止了,一个团聚起上亿普通群众的爱心团体慈济就形成了。她的力量和善业比肩任何历届诺贝尓和平奖的人物都不为过,最主要的是她让千千万万的平民得以善业为终,终身有善相伴。她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该引以为傲的人之一。
所以,昨天我被邀请回到北大做个小分享,北大人是中国社会里最受瞩目的一群人,也是最受期待也常受批评的一群人,“精致利己者、北大不再是当年的北大”时刻在鞭策着这群占尽天时地利的人,要志存高远、要胸怀天下。最起码北大人是最应该长出慧根和善根的人,既幸福自己、也幸福别人。
尽管我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甚至仿佛带有极端色彩的善业布道者,但我从来不认为善业有什么神圣和高人一等之处,原因正是在于她可爱的平民性。之所以很多人尚未步入平民善业的爱河里,不是你的能力不够、财富不足,而是你尚未觉醒,也怪我们社会尚未出现更多的善业布道者。
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个不错的业余马拉松跑者,同样经历了一个从抵触到尝试到习惯到热爱到自发布道的过程,我相信很多业余跑步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很难想象,短短几年,跑步运动成了最普及的平民健身社交运动,社会一旦觉醒,蔚然成风之势,人人皆为布道者。
跑步为了健身,善业更为健心,身体好了,我们的心灵怎能落下。一年365天,可否有5天属于公益、属于善业呢?一年收入的1%可否成为善款呢?一个班级可否自发形成一个积少成多的乐善基金呢?一场活动可否节约些包装和礼品,捐赠给需要的人呢?人生何处不善业,善行无时不可为。从从不行善到年行一善到月行一善到日日行善,最后融入灵魂随心所欲不逾矩,身体、性情、心灵得到由内而外的安宁祥和。其实不难,关键在于你愿意觉醒吗?我更愿意看到普通人种下的善果。
我知道我这种啰里八嗦天天布道,仿佛是个碎嘴的和尚,烦人透顶。但面对这些北大人,我有责任把话说透,因为社会向善向美的带头人,你们不做是愧对先师的。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接受自己临终时将可用的器官捐给医学机构,与其一把火烧掉,不如做点善事,从这个侧面也说明,人生的终点归于公益。所以,我们要在活着的时候勤加体会和练习,别等到临终之时被迫公益而手忙脚乱。这是一场终身的心灵修行,以善相伴、善业为终。
理想人生的最后一份工作应该是公益。

以下内容为古村之友汤敏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校友会换届大会上的发言内容。
公益如何饱满我们的人生体验与事业成就
各位校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深研院的领导们给我这么一位公益创业者,或者说主要为贫穷和弱势群体服务的职业,一次这么难得的分享机会,我的确心存感激也诚惶诚恐,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职业,我想今天在场的,除了我应该还有王芳师姐了。
所以大家应该对这个领域或多或少都是有些陌生的。社会上对我们这样的人通常有这么两个极端的认识,要么说"这么年纪轻轻地,不去好好挣钱,来搞什么公益,跟乞丐一样,可惜了",这种说法仿佛和说出家年轻人一样,"这么年纪轻轻就出家当和尚了,也不好好挣钱娶妻生子、照顾老人,实在白瞎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极端的说法,神化这些公益从业者,说"真有大爱、真有情怀,全社会都在疯狂搞钱,他们却去帮助那些贫困和弱势群体,太高尚了",甚至也说"这样的人上辈子一定是菩萨,大和尚转世"。有趣吧,说好的、说不好的,都说我们这类人像和尚,你们看我像和尚么。
其实大家既没必要惋惜公益人,也没必要神化他们,其实和大家的工作一样,首先是一份职业,都要服务好自己的阵地。比如学校老师要服务好学生,卖产品的要服务好买单的客户,我们这些公益人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贫穷和弱势群体上,我想这是最大的差别,就是公益人的立身之本是贫穷与弱势群体。
如果各位的工作中也兼顾关注着贫穷和弱势群体,大家也可以算半个公益人,比如老师在班级里特别留心去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多花些时间去辅导那些后进的同学,而不是只关注成绩好的、父母条件好的学生,这也是公益行为。各位卖产品的不只是净做高端、高净值人群的服务,也开发些亲民的系列,也算是一份公益。
至于全职来干公益的确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我相信我和王芳师姐在这条路的背后,一定都是有不少抉择和故事的。但有个共同点,是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的差别相关,以我来说,我学的是本科学的是园林设计、景观设计,来北大又学了些人文地理、历史地理以及北大独特的五四精神之类,教科书里、耳朵边全都是梁思成未能保护下北京城的遗憾,满眼看到的就是那么多古村落、文化遗迹遗憾消亡,自然会走上这条路。
你想在座诸位中,一定有很多学科技的、学经济的,你们的行业和前辈给大家讲述的更多是一个繁荣、朝阳的故事,和我们这种人文类或多或少带有些悲情的不同,你们这些行当没有太多历史包袱,更容易轻装上阵,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而我们就可能花了大半生在历史的悲伤里打转。
我这里想说的是,全不全职干公益不说明什么,更多是各个行业的价值追求和人生历程的差别客观带来的。再说北大人干公益的传统应该说从五四时期就是注入基因里的,家国担当、毁家纾难、弃笔从戎、视死如归这些精神和公益担当,我们今天在和平建设时期干的这点公益,只有望其项背、更加努力的份。
前面我一直在给大家进行公益去魅建设,是想引入下一个话题,大家不见得都全职公益,但大家都可以轻松践行公益。首先公益一定不等于捐钱,在公益的学术界和实践界,基本都形成了共识,捐助型公益越来越退居二线了,佛家也讲"财布施不如法布施、法布施不如无畏布施",说通俗掉就是给钱不如给方法,给方法不如激发斗志。

我想在座的北大校友们最擅长的就是方法,不然怎么考得上北大呢?所以更需要的是大家开动聪明的脑瓜去思考如何帮助贫困和弱势群体的方法,不一定是捐钱,当然你们把没必要浪费的钱拿来捐掉,那也是鼓励的,比如我们很多不常用的伴手礼费用就可以折合成现金捐了嘛。我也可以特别自豪地和大家说,我和我的组织这些年并没有捐太多钱去帮助古村落和村民,也没这个能力,而是我们的方法帮助了上千处古迹得以保护,数十万村民得到实惠,并且这些方法仍在呈指数倍增长的形式帮到他们,此刻大家是可以给我掌声的。
回到你们这些艰苦拼搏校友们的人生公益体验,我想每个人都应该自懂事起伴随公益体验,去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用一句特别俗的话"德财配位",求财和积德是螺旋上升的,而不是只是一味求财,认为财富够了再积德,这是一场苦途,因为错过最美妙的公益体验,对孩子的教育也是巨大帮助。不能指望人人的孩子都能出类拔萃、人中龙凤,但通过公益体验获得饱满的人格成长和健康的身心发展,这个是做得到的。
就像前不久我陪清送一起回了趟他的老家,清送就意识到不管挣了多少钱,最起码的一个身份要是老家的乡贤,人们都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奉献社会的方式,这样的人生和人格才是完整的。所以大家可以每年给自己做个公益时间的预算,比如一年52周,有一周七天的时间是用来奉献社会的,当然这七天是可以分开的。一年可以挣100万,有2%两万块钱是该用来帮助他人的,哪怕一年只挣10万块,也可以有2%两千块是用来做公益的,这样也可以逼着大家节约,节约也就在锤炼品德了。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结尾,我忘记了是谁说的了"幸福的人生是让投资成为最后一份职业",我想改一下"幸福的人生是让公益成为最后一份职业"。想想看呢,即便活着时候实现不了,死的时候也可以捐献器官或遗产,这不也终归公益了么?谢谢大家,我是汤敏。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