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14
2021-12-14
 440
440信息爆炸时代,公益人需要读什么?
在飞速前进的世界里,车、马早已被升级、淘汰,但是对于公益人而言,一封电子邮件总是会在周末如约而至。它很耐看,不“老”派,把握着公益万象之“新”——《公益慈善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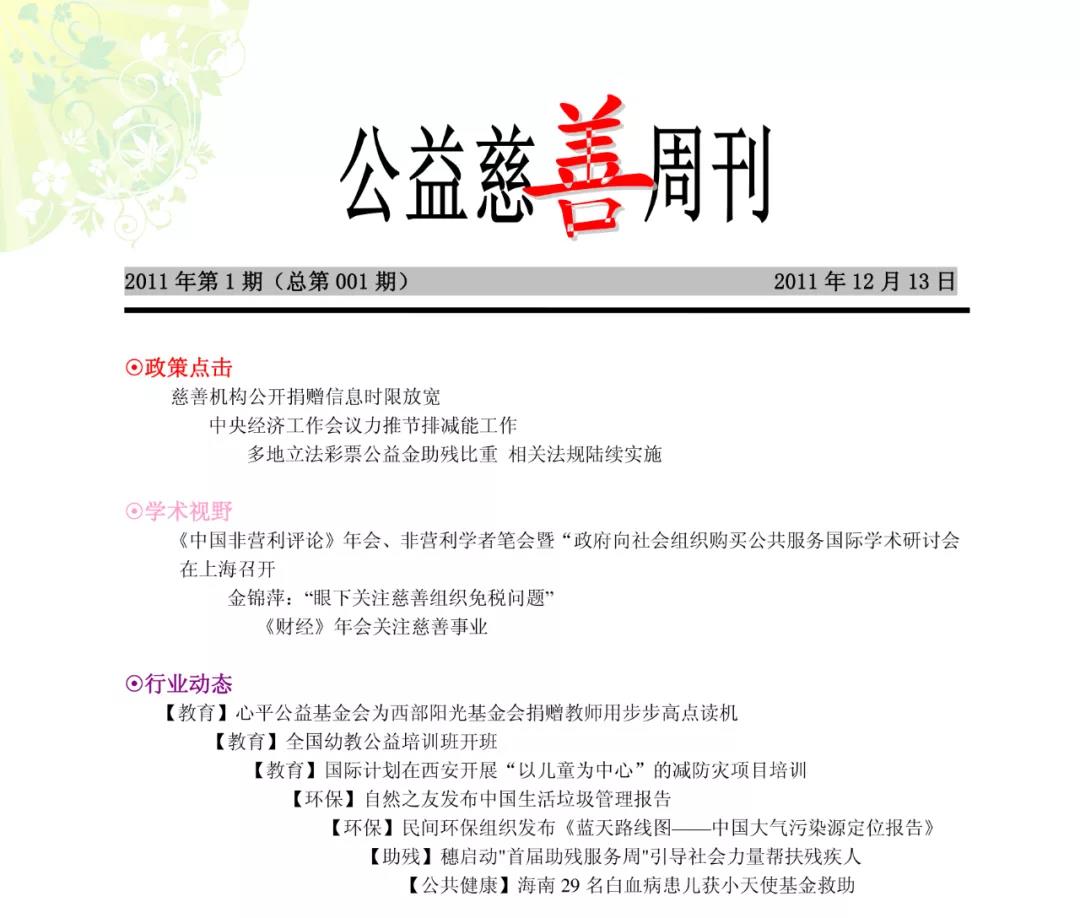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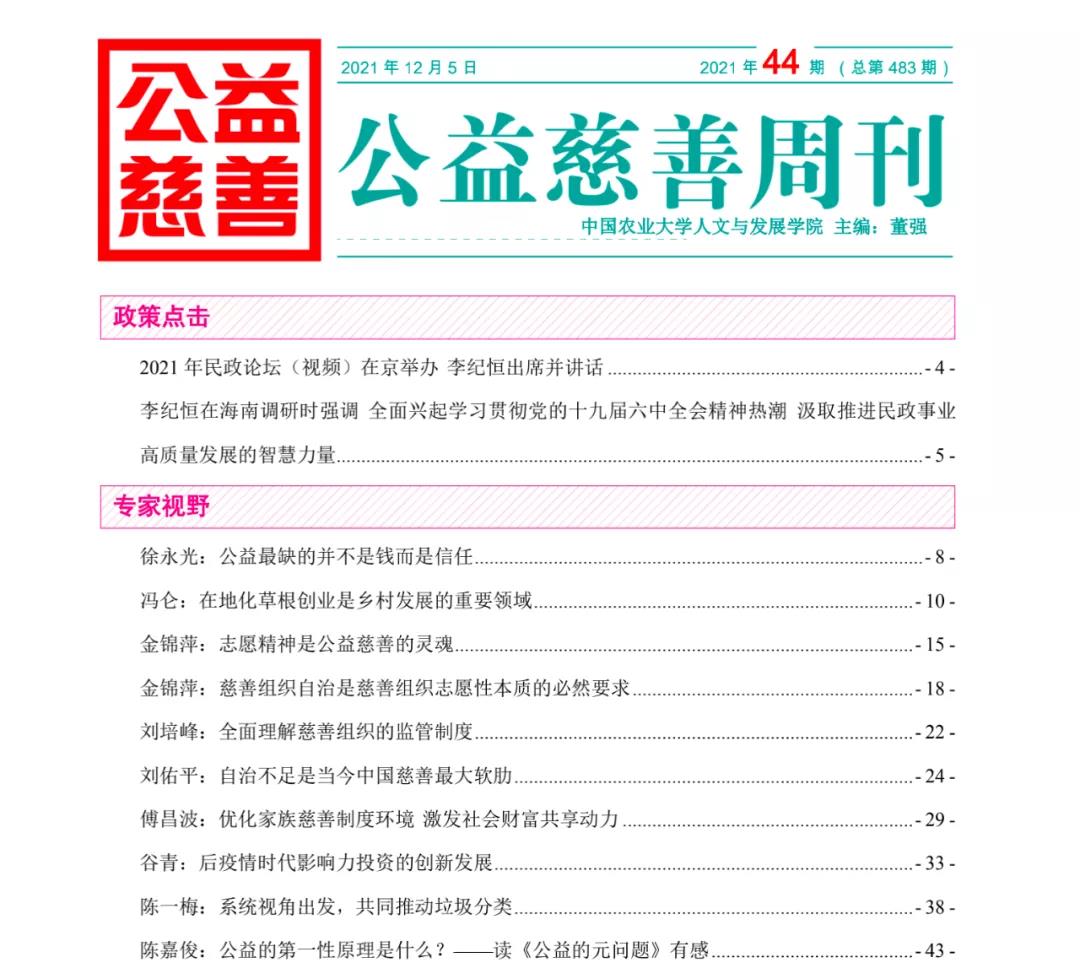
▲《公益慈善周刊》第一期首页(上)以及十周年总第483期首页(下)
从2011年创办《公益慈善周刊》之前,董强就一直思考“公益人需要读什么”这样的问题。彼时,他已经在中国农业大学任教4年有余,在观望形势后,决定不再停滞于反思和呼吁,开创了这个定期更新的公益资讯平台,许下了一个没有时间期限的承诺。
十年如一日,董强每周都会特意花一个半天的时间,筛选、编辑来自四面八方的公益界资讯,汇集成册,广泛传播。这份承诺让万千公益人受惠,他很清楚坚守的价值——身处五光十色、千变万化的社会之中,公益人不仅要躬行实践,还需要眼观世界,把握时机。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副教授,董强带领着他的学生共同完成《公益慈善周刊》每周的编发工作。一期百余页的体量,一个人总归势单力薄,好在董强的学生们是得力的助手,他们会广泛搜集、整理信息。
像铁打的营盘一样,周刊见证了董强的学生们从“新兵”到“老手”的成长,培养了他们广阔的观察视野。同时,一届届学生们的加入,也让周刊充满生机,持续运作得越来越好。《公益慈善周刊》是董强10年的坚守,更是团队力量的延续。
《公益慈善周刊》似乎没有所谓的“核心”读者,也很难画出一个极为精准的用户画像。这并不是说周刊“乏善可陈”或者“曲高和寡”,相反,它的读者遍布中国,常常让人意想不到。从钻研公益慈善的学者,到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的员工,再到身在一线的公益实践者,甚至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都能成为周刊的忠实订阅者。董强也表示,周刊本质上是“中立”的,是“开放”的,不设圈层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它的读者,与它一起成长。
2011年12月,《公益慈善周刊》第一期正式发出。在语气诚挚的刊首语中,我们虽然没有看见波澜壮阔的蓝图,没有听到改变世界的宣誓,但能够感受到一种让公益向上生长的力量、一份对公益蓬勃发展的期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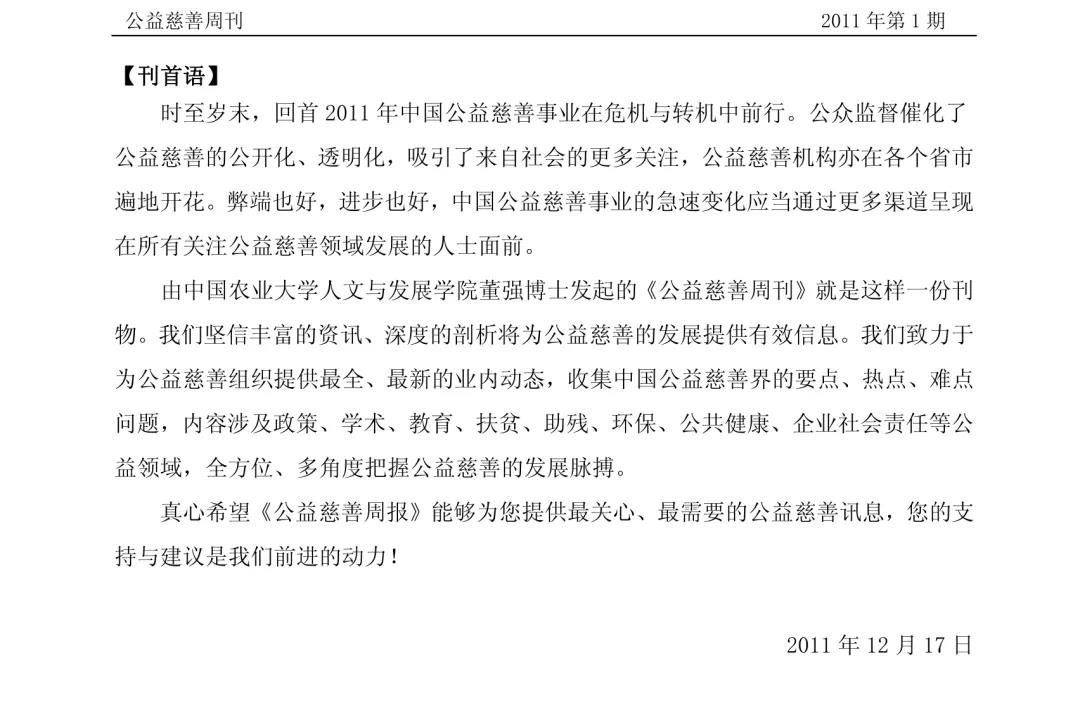
▲《公益慈善周刊》刊首语
首次登场,它就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厚道地讲述着所见所闻。只不过,我们谁都没想到,这位老朋友已经悄然陪伴了我们10年。下一个10年,它还会在吗?
01
“聚合”的力量,把握万象世界

▲董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公益慈善周刊创始人,公益评论影响力奖发起人,小云助贫中心理事长、总干事。
CDB:您为什么要创办《公益慈善周刊》?创办之初的中国公益大环境是什么样的?
董强:对我而言,创办《公益慈善周刊》是有多个动力和诱因的。首先,我认为一个“内容平台”具有连接和动员的作用。2002年,我接触到了中国发展简报,随后还作为志愿者加入到了该机构NGO名录的翻译工作中。一方面,阅读简报的纸质刊物能了解公益行业的概况,另一方面,发展简报还会组织年度活动,邀请各方面的公益行业人士交流畅谈。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接触了包括朱传一老师在内的很多公益资深人士,开阔了公益视野。
其次,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公益,投身公益。在此之前,公益的关注量不算高,甚至一场在北京友谊宾馆的大会议室举办的研讨会,就能基本容纳下当时的资深专家和公益领袖了。但是,2008年以后,公益界出现了很多新面孔,更多鲜活的案例迸发出来,大家需要进一步掌握行业动态,才能紧跟时代发展。
后来,基于对社会组织发展等方向的研究工作,我对于公益慈善领域的信息需求更高了,也感觉到中国公益领域资讯供给跟不上大家的阅读需求了。
其实在学术界,很多学者都会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汇编资讯。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每周都会做出一个关注“国际关系”的简讯,既搜集了动态,也对自身研究有益,还能带动自己的学生一起参与。这让我印象深刻、备受启发。
做一个公益慈善领域的“资讯平台”,是一件有挑战的事情。最开始,我很犹豫——自己是否有能力接得住?接下来了是否有毅力坚持住?在卸下压力后,我不再把这件事看作负担,也不去承诺能坚持多久,尝试着从“0”到“1”去搭建这个平台。
回首十年的探索与发展,我发现自己经受住了考验,也坚持了下来。
CDB:《公益慈善周刊》区别于其他资讯平台的特点是什么?有哪些核心栏目?
董强:在2011年前后,中国是有很多与“公益”相关的内容平台的,除了发展简报以外,有恩派创办的《社会创业家》、NGO发展交流网、《中国财富》杂志等,有综合性公益类报纸《公益时报》,也有《京华时报》《新京报》等媒体开设的“公益”版块。
这些内容平台各有千秋,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公益行业各个方面的视角和声音。但不可否认,单一的公益内容平台仍然“追”不上大家多元的需求,公益人也很难花费大量时间去逐一阅读。
我并不想跟他们“竞争”,在没有强大的原创内容团队的支持下,也很难拼得赢。所以,我就用“聚合”的思路去做好《公益慈善周刊》。
“聚合”,就是把所有关注公益、报道公益的内容平台都囊括进来,搜集他们的资讯信息,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门户网站等大众媒体,还有公益行业的媒体。
在长期汇编的过程中,周刊内部形成了一套工作机制:学生们会广泛撒网,追踪各级政府、各类媒体的动态,也形成了不断完善的“跟踪”名单;我会逐一审阅,以专业的视角和公益人的阅读需求再次筛选,最终定稿,免费分享给大家。
聚合内容、多次遴选、定期分享,这让《公益慈善周刊》具有了多元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公益行业的思想变化。
02
见证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
CDB:您在甄别和筛选信息的时候,有哪些标准?在设置《公益慈善周刊》栏目方面有哪些思考?
董强:面对公益慈善领域的海量信息,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些编辑经验,首先,选择一条资讯,主要取决于它对于行业整体的价值;其次,我们会在判断文章来源是否“权威”,是否对行业有意义;最后,文章的质量很关键。不少媒体会刊登“软文”性质的广告,我们一般不予考虑。
《公益慈善周刊》的每一个栏目设置都有其背后的考量。第一个栏目是“政策点击”,主要关注民政部以及相关的国家部委与公益相关的政策出台动态,也会关注北京、上海、广东、四川等重要省份民政部门的信息。
只要是与公益组织相关的政策,我们都会选进来。为什么要关注政策?因为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并不是完全自发孕育的,它的发展与当下的政策密不可分,必须时刻关注政策带来的机会和空间,社会组织要据此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
第二个栏目是“专家视野”。其文章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专家学者,多数基本都在高校从事公益慈善领域的研究;一类是实践领袖,他们经由长时间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上升到理论层面去认识、启发公益行业类,商玉生先生、何道峰老师、王振耀老师和徐永光老师都提出过许多真知灼见。某种程度上,这两类人是公益界的“思想领袖”,他们引领并且推动着我们去思考。社会组织可以根据这些观点了解公益行业基本形势,调整工作中的一些思路。
在政策指导和专家视野的连通之下,第三个栏目“行业观点”会以更加多元、庞杂的视角观察行业发展,涵盖了公益慈善的方方面面。来自于主流媒体、大众媒体、行业媒体,甚至是“自媒体”的观点性文章都会有所体现。现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等枢纽型平台也涌现出一些新鲜观点、优质内容,我们也会摘取进来。“行业观点”栏目就像扩音器,有左声道、右声道,传播大家的观点、传播新鲜的声音。
接下来的“行业动态”“国际观察”“企业社会责任”“公益布告栏”等就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公益资讯进行筛选和分类,全面了解公益各个细分领域。有时,我们会设置一个“专题报道”,类似于“刊中刊”,整理近期发生的重要事件相关报道,比如雅安地震、尼泊尔地震、河南水灾等,便于读者快速了解公益行业内的“大事”。
CDB:《公益慈善周刊》的栏目有哪些变化?您进行过哪些创新和尝试?
董强:纵观《公益慈善周刊》十年来的内容,它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公益人阅读诉求和需求的变化,也见证了公益行业信息交流层面的变迁。
我们观察公益行业的方式和标准没有改变,因此从栏目框架上看,没有很大的改动;从栏目内容上,我们却能看到很多变化。
比如,“政策点击”栏目中能感受到,原本关于社会组织的政策多是出自民政部门,但现在相关部委同样会在文件中体现,这说明社会组织在变得“主流化”;原本地方上的政策会很多,但现在中央发布的政策变多了,两者之间的连接性更强了。如果你仔细看其他栏目十年间的内容变化,会发现很多现象和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专家视野”和“行业观点”栏目中,我们愿意推出一些新鲜面孔,带来更多样化解读,但是依然不尽如人意。基于这个观察,我们创新尝试,做了3年的中国公益评论影响力奖的活动。总结经验、表达观点,这是需要很长的过程。公益“新”人必须先敢说,再考虑如何说得好。
公益行业要让新生代、中生代有更多的机会历练,有更多舞台去展示。
03
思想的力量,滋养公益生长
CDB:《公益慈善周刊》有哪些读者?对他们来说,周刊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董强:目前,《公益慈善周刊》会在电子邮箱和微博等渠道进行传播,大约有2万多名长期订阅用户,辐射近10万名读者。
周刊的读者范围是比较广的,有时候都会出乎我的意料。比如在2020年9月,我到云南瑞丽调研,一个中缅边境的NGO领导人就说她每周都看,了解公益动态。我很讶异,也倍感欣慰。
首先,《公益慈善周刊》是“低门槛”“零成本”的。西南边陲的社会组织没精力在网上看资讯,没机会去北上广参加会议,但是当他们订阅了以后,就可以凭着这份垂直性很强的资讯聚合体,快速把握时下最新资讯。这意味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信息壁垒,缩减了信息鸿沟,让精选的高质量资讯变得更加普惠化。
其次,《公益慈善周刊》浸润于公益慈善领域多年,是可以向学术领域纵深的。在学术界,很多人都向我提及过它,有一位来自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授说他每一期都关注,编教材、做教学都会依赖周刊的精心整理。同样,我也是因为每周的搜集和整理,对公益慈善领域有了一个更全面的把握。2015、2016、2017连续三年,我为杨团教授主编的《慈善蓝皮书》写了年度盘点。可见,资讯并非是“浅”的,它可以生发出多种可能,对行业产生更多影响。
同时,周刊也希望公益组织能重视“公益传播”。总体来看,公益慈善部门的声量是比较弱的,公益组织就更需要学会推荐自己、总结自己,把握恰当的传播点,把生动的公益故事讲出去。
CDB:您认为要做好信息平台,是需要引领读者,还是要迎合读者?《公益慈善周刊》在扮演什么角色?
董强:我觉得《公益慈善周刊》既不是在引领读者,也没有刻意迎合读者,我们想做好触发公益人“生长”的支持者、陪伴者。
周刊在聚合信息,提供营养。这意味着我们不是一本“武功秘籍”,得到人们不一定会“如有神助”,相反,不同的人阅读周刊会有不同的收获,有的人吸收了观点,有的人看到了机会。
《公益慈善周刊》不是给公益人行动支撑的,而是旨在培养公益人的价值判断和思维能力,用优质、及时、多元的信息资讯助力公益组织茁壮成长。因此,这很难说是一种绝对的“引领”。同时,我们也不过分地迎合,因为“保持中立”始终是我们恪守的价值。
CDB:您认为公益资讯平台有什么价值?行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公益信息资讯平台建设处于什么环境之中?
董强:《公益慈善周刊》在创办10年的过程中,受到了几家基金会的支持,包括南都公益基金会、亿方基金会、敦和基金会和银杏基金会。我很感谢这些机构的关注和认同,这对周刊来说很重要。
资讯平台的价值,其实是不言而喻的。每个人都需要去阅读,去学习;每个组织也都要紧跟时代,及时发声。但是在周刊10年的观察和追踪的过程中,公益资讯平台可以说是“生生死死”。
公益资讯平台就像很多行业基础设施一样,当它们消失了,人们就发现这是问题痛点;当它们正常存在,人们就觉得理所应当。这些行业设施仿佛没有生命力一般,都是在一轮一轮地建设。原因之一就是公益行业的资源配置的战略、决策常常变化,行业生态的基础设施始终都会陷入到“轮回”的局面。
这个问题并不是一方造成的,而是涉及到社会多方对于公益价值理念、公益资源配置的认知决策。现有的公益价值似乎都是过于追求“短平快”,急于看到项目的成效。同时,公益行业缺少一种让人长期专注做事的机制。
如何让资源配置在不“惊天动地”却“润物无声”的领域呢?政府需要有更多相关的激励政策;公益资源配置也要重视长期主义……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公益人持续反思的问题。
所以,《公益慈善周刊》能否有下一个10年?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仅仅是我能否再坚持10年,也与行业对于公益内容平台等基础设施的重视程度相关。因为个人精力、团队的不可持续、资源无法筹措等方面的因素,我也在考虑是否要结束这样一个资讯平台的运行。
CDB:《公益慈善周刊》创办10年,给您带来了哪些改变?
董强:在创办之初,我曾担心过周刊能否被大家接受。在十年之后,无论是资深人士还是民间组织都予以了大量关注,我的底气变足了,也更有信心去做好周刊了,这是第一个改变。
第二个改变,是我对于公益的“热爱”与日俱增。近500个周末,我都会抽出时间编排周刊,从各个角度观察、记录着公益行业。无论大小,在这份坚持和承诺的背后,我感受到了“责任”的分量。
第三个是《公益慈善周刊》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助。在调研走访的过程中,我时常碰到一些周刊的读者。当我亮出身份,他们对我展现的亲切和认可,让调研变得更顺畅。同时,周刊作为内容平台,连接了很多组织和人,搭建了一个网络,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
同时,《公益慈善周刊》让我成长,也让我的学生成长。其实,很多周刊团队的学生之前并没有接触过公益慈善领域,但是他们在一篇篇资讯中感知,在一次次阅读中学习,有些学生就会在毕业后致力于公益事业,去实践,或是去深造。公益的理念和价值嵌入到了他们的人生里。
我也希望,《公益慈善周刊》能在很多人心中埋下公益的种子,在温暖的阳光和充足的营养中,生长成参天大树。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