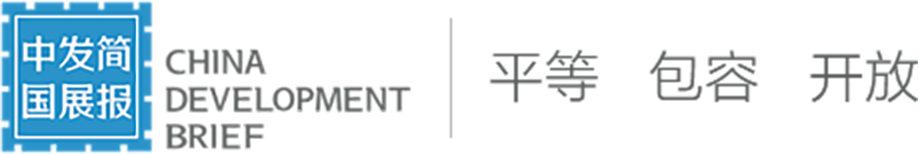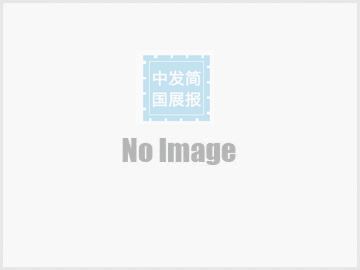2013-04-18
2013-04-18
 1229
1229
协会秘书处项目组身处阿拉善当地,七八个人,主要工作是深入农牧区甚至需要经常居住在村里,目标是实现保护生态平衡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一致,也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具体内容是实施一系列措施,如限制牲畜数量,封育森林草场,安装阳光灶,修建沼气池,改造水渠,改良牲畜品种,植树造林,栽培苁蓉,蔬菜温棚,以及相关的教育培训……最重要的是,这一切决不是采用陈旧的模式(如行政命令、财政补贴、领导发动等),而是(除了一些协作和委托项目)全部纳入一种叫做“社区发展”的全新模式中进行的。
——《阿拉善生态协会战略考察报告(2006)》
SEE的执行团队也有梦,要让老百姓有权利,有平等的机会,他们认真而神圣。考察团看上这些草根环保团队的工作能力及献身精神,社区工作受老百姓欢迎,连盟党委副书记都说要拿政府的项目与SEE合作。
企业家不熟悉这些非政府组织(NGO)的语言,他们就给设道槛儿,非要爬过这道门槛儿,才跟你对话。年轻的成员清晰地给考察团一个信息:企业家,你们虽然出了钱,但NGO有价值理念!
张树新也犀利地指出:这不光是你们的NGO,这是我们的NGO,我们出钱还出时间做公益事业,不是更有道德优越性吗?并不是所有商人都唯利是图,不能因为我们做了商业,就剥夺我们理想的权利。家寰甚至要我帮忙打开邓仪的脑袋,团队的回答总是绕来绕去云里雾里,说不完的故事。企业家以目标为导向,接下来的问题直截了当:社区只有四五个项目点,能否复制?团队不回答,还是答不了,不得而知。
国际上这样定义第三部门:通过外部介入活动,改善弱势群体和有需要人群的状况,引导他们参与到发展的进程中来,并成为发展的主体,最终目标是去影响社会发展进程。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基金会,诸如福特等,引进了很多援助和保护项目,也带来西方公平、权利的理念。无论国际国内,在生态和贫困地区做项目,最大的挑战是项目的自我持续性。NGO和国际援助“人走茶就凉”的例子,俯拾皆是!
执行团队的项目有一些社会性成效,村民成立了生态项目管理委员会,自己制定村规民约。生态保护到2006年一时半会儿还很难看出效果,十年树木。如果几年后,嘎查村民的活动不能自我持续,那生态的成效也不会太大。我想先看看这个揽了瓷器活的团队,是否真的能做到“给网”,让目标群体自己行动要有点能耐。这样,我就申请到了香港利希慎基金会的研究资助。
协会项目团队2004年进入阿拉善地区工作,开始只有四五人,活动逐渐扩展到阿拉善地区七八个项目点,有上百个大大小小的项目,包括能源替代、节水农作物试验、牲畜品种改良、农牧圈养、梭梭林保护、苁蓉种植、草场保护、膜下节水滴灌、奶牛股份养殖、合作社、社区基金和小额信贷等。使用的方法和活动数十种:出外培训、参与式推动、集体会议、入户访问、小范围讨论、协助推动、咨询、资助、贷款、村民讨论、村民项目委员会、生态合作社等。
表3-1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社区发展与生态项目统计(2004年6月~2011年3月)
1.吉兰泰镇召素陶勒盖嘎查(一队)(2004年9月~):嘎查距吉兰泰镇所在地32公里,现有人口68户192人,草场面积981000亩,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642510亩,承包草场面积598060亩,牲畜3130头(只),种植面积1099亩,列入公益林83965亩,列入公益林户37户174人,草畜平衡签订责任书11户。
实施项目:能源替代与天然梭梭林保护项目、节柴灶圈、节柴灶、太阳能灶、家畜养殖、风光互补(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沼气池、沙芥种植、苁蓉种植、饲草种植、活动室、苁蓉种植、草籽撒播、三位一体(15项)。
2.吉兰泰镇哈图呼都格嘎查(二队)(2005年6月~):现有59户207人,草场面积667平方公里,可利用草场面积500平方公里,梭梭林面积48万亩。牧业为主。主要放养山羊和骆驼,部分户数种植苁蓉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可达200亩。
实施项目:太阳能灶、风光互补3套、风力发电机7套、太阳能板3套、建筑鸡舍、苁蓉种植、三位一体、人畜饮水窖、风光互补、品种改良、粉碎机、苁蓉种植、生态旅游、鼠害(14项)。
3.吉兰泰镇图格里嘎查(三队)(2008年3月~):现有68户196人,草场面积801000亩,可利用草场面积660060亩,承包草场面积718346亩。列入公益林面积157829亩,列入公益林户30户116人,草畜平衡签订责任书60户。
实施项目:该项目点属于吉兰泰二队自我复制项目点,2008年3月进入SEE项目区域,2008年7月执行项目时已并入吉兰泰合作社,不再单独以嘎查身份申请项目。
吉兰泰镇泰和生态牧业专业合作(包括吉兰泰一队、二队、三队,自2008年7月起,吉兰泰项目片区合并为一个合作社):伴随2007年合作社法的出台,2008年9月原吉兰泰1、2、3队44户牧民(SEE前期项目户)组织起来,正式成立了合作社,并选举执行理事会和监督委员会。经过3年的运作,合作社成员数目由刚开始成立合作社时吉兰泰召素套勒盖嘎查、哈图呼都格嘎查和图格里嘎查的44户逐渐扩大到现在的70户。
实施项目:5户联合养鸡项目、草籽撒播(2项),红柳种植、梭梭+苁蓉种植、地热项目、太阳能光板、“梭梭·千峰骆驼文化节”牧民那达慕、梭梭文化节(6项)。
4.巴润别立镇铁木日乌德嘎查(包括贺兰队、黄土沟,2005年9月~;2008年转为绿源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铁木日乌德嘎查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农牧结合嘎查。全嘎查现有户数170户,656人,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占1/5。退木还草总面积35万亩,耕地总面积4000亩。现人均耕地3.6亩,是全镇人均占有耕地最少的嘎查。
实施项目:黄土沟修路、贺兰队养殖技术、贺兰队粉碎机、黄土沟粉碎机、贺兰队垃圾处理及卫生池、贺兰队土壤改良、贺兰队社区发展基金、黄土沟社区发展基金、贺兰队管灌、棉花种植、贺兰队暖棚圈舍、黄土沟暖棚圈舍、奶牛小区硬件建设、奶牛小区硬件建设、奶牛小区入股买牛、奶牛小区贷款买牛、奶牛小区贷款买牛、奶牛小区饲料周转金、奶牛小区饲草周转金、奶牛小区购牛周转金、股份制奶牛项目财务结算、奶牛小区财务审计、股份制奶牛项目财务服务、奶牛小区绿化项目、黄土沟社区发展基金增股、贺兰队科技培训中心、贺兰队社区发展基金升股、黄土沟沼气抽渣、贺兰队青贮玉米种植补贴、黄土沟防洪坝引水、黄土沟文化活动中心、贺兰队排污管道、捐赠、贺兰队修路、贺兰队图书室、奶牛小区搬迁、HPI-SEE阿拉善社区综合发展项(38项)。
5.巴润别立镇岗格嘎查(2008年3月~):岗格项目点有314户1114人,汉族867人,少数民族247人,男性571人,女性543人。共8228亩耕地,人均耕地5亩,人均年收入4907元。粮食种植为主,靠地下水抽取灌溉。西南靠腾格里沙漠,农业区生态环境恶劣,常年风沙大。
实施项目:社区发展基金、农田防护林、自来水管道铺设、HPI-SEE阿拉善社区综合发展项(4项)。巴润别立镇(2005年9月~)综合项目:杂交小米种植试验、节水灌溉可行性研究报告、太阳能热水器、杂交谷子种植补贴(4项)。
6.锡林高勒镇乌达木塔拉嘎查(2005年7月~;2008年转为查哈尔滩盛源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乌达木塔拉嘎查,户数172户,人口655人,男女比例48.5∶51.5,耕地面积4000余亩,人均耕地6亩,主要种植作物是玉米、棉花、油葵等,以抽取地下水为主要灌溉方式,土壤沙化、退化严重。
实施项目:查哈尔滩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区发展项目合作执行协议、舍饲养殖、社区能力建设(培训)、社区基金、借款协议(棉花种植播种机)、棉花种植试验借款、社区基金、借款完成项目(膜下滴灌项目)、借款完成项目(气化炉)、借款完成项目(气化炉)、借款完成项目(梭梭防风林种植)、沼气、借款完成项目(膜下滴灌周转金)、小米实验、膜下滴灌(试验项目补偿)、珠很高勒吊炕项目、珠很高勒短期育肥羊、合作社节水作物种植补贴、合作社葵花脱粒机、珠很高勒修路、HPI-SEE查哈尔滩肉牛养殖(22项)。
7.锡林高勒镇希尼呼都格嘎查(2006年6月~):希尼呼都格嘎查54户246人,人均草场面积3000亩,人均耕地19亩,植被覆盖较差,水源充足,以地下水为主。草场退化严重。总面积421平方公里,草场可用171平方公里。
实施项目:能源替代、社区基金、能源替代、种植、草籽撒播、草籽撒播、草籽撒播(7项)。
8.额济纳旗吉日嘎朗图嘎查(2006年8月~):吉日嘎郎图嘎查位于达镇西南角,东南与温图高勒嘎查、南与古日乃嘎查、西与巴彦宝格的嘎查、西北与赛韩掏来苏木、东与乌苏荣贵嘎查接壤。总面积2274平方公里,有148户、473人,居住着蒙、汉、藏等民族,是农牧结合的嘎查。种植面积约5480亩,主要种植哈密瓜、棉花、玉米等农作物。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及实验区。
实施项目:社区发展与胡杨林区生态和文化多样性保护项目,能源替代、社区文化、气化灶、气化灶、气化灶、气化灶、气化灶、气化灶、养鸡、饲舍养殖、品种改良技术培训、养殖培训(12项)。
9.额济纳旗乌苏荣贵嘎查(2006年8月~):乌苏荣贵嘎查位于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呼布镇东部,区域面积为894平方公里,人口共计74户209人。乌苏荣贵嘎查的胡杨林状况较好,分布面积也较大,属于额济纳胡杨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与缓冲区。嘎查胡杨林面积65495亩,梭梭林面积4740亩,红柳面积98318亩。
实施项目:社区发展与胡杨林区生态和文化多样性保护项目气化灶、能源、种植、舍饲养殖、社区文化(5项)。
10.额济纳旗其他嘎查(2006年8月~)实施项目:社区发展与胡杨林区生态和文化多样性保护项目,《牧人居民俗文化生态园》电网设施安装及改造工程的合作协议1项。
11.乌斯太经济开发区巴彦敖包嘎查(2009年3月~):乌兰布和梭梭林保护项目中的新社区,地处阿拉善经济开发区西北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成立于1958年,总面积1600平方公里,属戈壁荒漠带。有草场255.8万亩,其中,实际可利用151.4万亩。梭梭林面积较大,但缺少具体面积统计。嘎查蒙、汉、回民族聚居。现有农牧民68户203人。
实施项目:乌兰布和200万亩梭梭林保护项目:草籽撒播、太阳能光板、梭梭种植(3项)。
12.吉兰泰镇巴彦洪格日苏木呼和温都尔嘎查(2009年6月~):乌兰布和梭梭林保护项目中的新社区。嘎查距吉兰泰镇所在地65公里,现有人口68户212人,草场总面积1277355亩,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1039970亩,承包草场面积1039660亩,牲畜12693头(只),种植面积198亩,列入公益林面积125817亩,列入公益林户35户128人,草畜平衡签订责任书29户。
实施项目:乌兰布和200万亩梭梭林保护项目:太阳能光板、节能火墙+节柴灶、吊炕(3项)。
13.吉兰泰镇巴彦洪格日苏木查干温都尔嘎查(2009年6月~):乌兰布和梭梭林保护项目中的新社区。嘎查距吉兰泰镇所在地108公里,现有人口75户201人,草场面积1362945亩,其中可利用草场1112175亩,承包草场面积1111798亩,牲畜10025头(只),列入公益林面积299775亩,列入公益林户38户95人,草畜平衡签订责任书20户。
实施项目:乌兰布和200万亩梭梭林保护项目:太阳能光板(1项)。
14.吉兰泰温都尔勒图镇赛汉塔拉嘎查(2006年6月~):1998年由98户贫困牧民搬迁转移组成。嘎查刚成立时欠下银行贷款十余万元。2003年,有98户337人,耕地4700亩,牲畜3398头,年人均纯收入2432元。嘎查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建立农户资金和扶贫资金的股份合作社,为农户提供农用物质购买和销售,整村推进扶贫工程葵花仁初加工项目。2009年底,全嘎查农户人均纯收入达到5336元。2006年参加培训。
实施项目:SEE社区发展培训、指导咨询(2项);政府扶贫办整村推进:农牧民自组织合作社、嘎查自筹、农用物资购买、农用物资销售、股份基金、葵仁加工、葵油加工、大麻子油加工(8项)。
15.吉兰泰镇锡林高勒沙日布日都嘎查(2009年7月~):现有人口162户522人,低保户20户66人,贫困户8户31人,草场总面积1065000亩,其中可利用的草场面积587685亩,承包草场面积587685亩,牲畜头数20763头,其中骆驼815峰,山羊8357头,种植面积7500亩,其中粮食作物5270亩,经济作物1200亩,列入公益林面积42908亩,列入公益林户8户,人均纯收入4850元。
实施项目:乌兰布和200万亩梭梭林保护项目:太阳能热水器、地热、节柴灶项目(3项)。
16.吉兰泰镇巴音诺日公浩特淖卓尔嘎查(豪斯布尔都苏木浩坦淖尔嘎查)(2007年7月~):嘎查2005年获得SEE生态奖,系巴彦诺日公苏木所属嘎查,畜牧业是主要产业,牲畜主要包括骆驼、山羊,这地方也是白绒山羊的主要产区。民族以蒙、汉为主。人口总数335人,其中男性169人,女性166人,承包草场总面积878209亩,牲畜头数2828头,人均收入6332元。
实施项目:草场保护项目草籽撒播、项目参与户承诺遵守村规民约和减畜还草保护草场条例(2项)。
17.吉兰泰镇巴特尔布拉格嘎查(吉兰泰7队)(2010年1月~):现有人口79户233人,低保户13户35人,贫困户17户53人,嘎查草场总面积1266000亩,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1037100亩,承包草场面积731890亩,牲畜头数17528头,其中骆驼691峰,山羊15271头,种植面积259亩,其中粮食作物231亩,经济作物7亩,列入公益林面积52586亩,19户91人,人均纯收入4821元。
实施项目:乌兰布和200万亩梭梭林保护项目:太阳能板、能力建设与锡盟培训项目(2项)。
18.其他项目为与社区和政府签署的社区发展项目:社区发展与胡杨林区生态和文化多样性保护项目;2009~2010年政府采用了内生式社区发展整村推进扶贫培训;2011年8月为政府15个村子推进内生式社区发展培训(3项)。
自2006年起我每年都访问这个团队,包括离开的成员。前前后后有①来参加培训的志愿者十多人、刚刚进入项目的干事9人;②可以独立执行任务的项目官员8人,担任多个项目的项目主管5人,负责团队管理的项目领袖前后4任。他们有几个是在7年的过程中从志愿者成长起来的,经历了项目的初期到成型的整个过程和各种曲折。团队最多时近20人,观察到50人次上下。我不断地到现场访问他们,他们告诉我许多的故事,我把故事梳理了一下,他们的成长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初入阶段:志愿者
非政府组织其实是社区外部的优势群体,他们意识到目标群体的困境,带着资金来做援助和发展项目。SEE执行团队的目标是,通过项目促使当地农牧民自己行动,改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使阿拉善的生态改善。来做志愿者的成员,在学校里长长短短地参加过不同的公益活动。加入SEE的执行团队,要先做几个月到一年左右的志愿者,或者项目干事。
我与NGO
他们告诉我,在大学当志愿者时,对环境保护、扶贫行动、农村发展、赈灾行动等词汇都有耳闻并参加了一些活动。特别是近些年,NGO在大学中招募假期志愿者,还有专家和教授有社区发展评估项目,他们就跟了去。有个研究生志愿者在做的中间“发觉很多东西很新鲜,是做学生时从来没有学过的……而学科里能实践的东西特少。因为感兴趣,就会想那些(实际的)东西……去看专家做分析”。
他们大都这样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思考那些新词汇和行动的意义。例如,贫困的原因和“参与”的意义。
这些志愿者大部分做过学生领袖,发起大学的环保社团,做环境保育,例如中华虎凤蝶、白暨豚的保护,有的夏天参加国际计划的水域环境项目、孤儿院和艾滋关怀行动。一个志愿者来团队之前:
[我]在大学参加了保护中华虎凤蝶的活动……它们要小灌木提供食物和栖息地。城市发展,[虎凤蝶]生活的环境被破坏,数量急剧下降……后来发现光懂知识和做宣传很没有效果。一个做环保的老师终于发现虎凤蝶喜欢一种植物叫杜蘅,租了半亩地做了一小片保护地。蝴蝶冬天需要阳光,我们把周围的竹子砍掉。做那些事,要冬天夏天跑来跑去。第一年杜蘅长出来后再去观察,发现叶子上有很多幼虫。我们技术组的吴琪老师说了:第一次在一个区域里面发现如此多的虫卵,而且没有花多少钱就开辟了实验地。但要跟社区合作才能扩大保护地,去跟政府要10亩地吧,老师和学生做不到了!
他们“也深入实地做社区项目,但大多失败了,大学生有很多限制”,缺乏经验和能力、资金、指导,“我们主要是参加宣传性活动,没有办法深入,达不到参与式”。
团队成员多半来自农村,公益活动触发思考。一个成员的父亲当过兵做过农民工,后来把妈妈和他们兄弟俩接到城边住。在家人的鼎力支持下,他读完了大学。
大学时,他就做志愿者,重新回到那个一家人已经离开的环境。当自己站在那些和自己父母兄弟一样的村民前面,“公平”“权力”“平等”等词汇触动他重新解读:现实里不合理的东西就嵌在“现代化的”体制内。还有不合理的,例如整个人群“疾病时没有钱的无奈,[我]看到那些陷入不利状况的人群,那些孤儿、艾滋病病人,有过类似[无可奈何]的经历,[我]可以做一些事,改善那种状态”。
这个小伙子毕业后参加了一个NGO,越过种种障碍,去为艾滋病病人送药,去照顾孤儿,去教孩子照顾自己生病的父母。
从心底里涌出来情感,其意义越过了“工作”。一个女成员觉得,“那些办公室里堆在面前几百页的文件、责任,把整个人捆死了,就这么年轻,你就没有什么创造力,没什么自己的思想的话,那太可怕了……去认识这个[实际的]东西,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他们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偏离了老师、父母、权威书本教诲。毕业时要做什么,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当时觉得自己的选择很迷茫嘛,要给自己更多的机会”“……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体制内、企业内、城市办公室内的工作,“不是我想做的事”“不太想去重复那些限制性太大的”“听从的、不合理”的工作。“NGO提供一个做事的空间,就试试。”
“那些参与式、内生式、社区的自动起来做事,是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那是一种新的社会活动”,“我来是为多听听、多看看的,看看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回事,也研究研究[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尝试下去观察,就是这么个心态”。
在实际中思考自己还不确定的东西,思维、道德突破了以书本、政府政策和家长为依归的文化。“毕业了,终于可以选择了!”他们知道自己“有些另类”,与“其他升学和找工作的同学”不同。“周边的同学嘛,考研、当公务员、进入公司企业、当流行的村官的都有。”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容忍自己不确定的意识,给自己的思维一个空间:“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嘛……NGO的存在肯定有它合理的一方面,我的个性是去‘珍惜’,NGO应该是我要珍惜的一个机会吧!”
为了逃避人们不解的询问,有的甚至长期瞒住家里的亲人做NGO。有个小伙子是自己做的组织被报道了,家里人才知道。
将来自己是什么,他们不清楚,身份不确定,前景不明朗,就像在迷茫大雾的山里行走。“在阿拉善做个志愿者是一个可以试试,看看自己想做什么。”确定的是,他们要给自己机会和时间,自己去确定。他们做福特、宣明会、乐施会、爱德基金会、国际保护、艾滋病孤儿等项目,现在选了SEE协会团队,是因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环保任务,是因为邓仪的“内生式经验是好像与其他参与式有点不同”,是因为“它有空间给我,相对其他NGO容忍度高”。
进入实地的感触
最初的志愿者工作大约有两种情况,协助老师和专家做项目;做会议准备、行政杂务,实地评估背器材,或者参与式讨论做纪录。他们多是项目官员的现场跟随,不断接触到新鲜的词汇,像PRA、基层民主等和新的经历。
大家坐在一块,不管是官员也好,村民也好,大家拿个大白纸来画,做很多卡片,是我们那种学习里面没有的。那次之后我就觉得,哎!那个东西挺好的,因为它非常快啊,但是也有很多毛病,但是它有它的优势,要是跟我们人类学的这种详细的长时间的调查访谈结合起来,是挺不错的东西。我最后写的论文好像涉及一点点这个东西呢。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觉得有东西可学。
他们接触的范围很广,有村民、政府官员、学校老师、大学教授和国际各种专家、企业家。“了解一群人在一起做什么,一接触就觉得,哎,那个东西挺好的,才知道这个就是研究啊,知道好多东西吧!”
志愿者没有接受正式培训就直接进入场景中。一个成员曾经到陕西农村一个国际“水与环境卫生”的项目。项目领袖“大概讲解后,就提供各种资料,照着做……项目已经设计好的”。志愿者进入村子和学校,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法做宣传和组织活动,给孩子讲刷牙、洗脸、便后洗手的卫生习惯,改善农村儿童的生活环境。这个组织还为农户从窑洞里搬迁出来提供一些卫生和用水的条件,例如建水窖和干湿卫生厕所等等。志愿者的任务很简单:做宣传并观察孩子没有使用卫生用水的方法。对没有使用的人,继续跟进做宣讲,根据资料向他们讲解使用的好处。在村子待了一个多月后,他们对行动目的的了解还是十分模糊。
开始做活动“发现一个个孩子失学的时候,能让他重新去上学,觉得这是很快乐的事情,自己得到满足。就像把海边搁浅的小鱼扔回到大海里了,是件高兴的事情。后来高兴不了,开始思考这种想法是不是对呢”。
“那个节水的项目执行期短,老百姓缺乏环保和科技知识的,国际项目采取了在村子里自上而下去推行的,操作手法就是动员村领导、村长、村书记跟老百姓接触,靠他们去领导操作。”那种方法“肯定不可能推广……也不是被扶贫的人想要的结果,很多项目不自然地走到这样一种困境。开会(村民们)头天的时候说得很好,几个人的名字都写上准备开始干,第二天全退了,第三天再回复到原来:不干了!不干了!我们还是种我们的庄稼去!”
开始志愿者“非常乐观的,后来就觉得乐观不起来。因为看到现实有好多困难,都是我没有能力去解决的,我也没有办法去改变”。
他们“想了解和研究这个现象,就思考扶贫项目的设计,也发觉他们与村民互动能力很低。调查访谈、项目评估、与农民的沟通啊,都是没有认真想过的东西,学校里没有教过。有项目啦,你感觉要很多能力去应付实际环境,能应付多少自己也不清楚”。
例如,“村民不做财务管理,不计算节水成本,自己与村民交流也讲不清楚。光靠宣传难改变村民的行为!”这个志愿者开始反思自己的能力有什么问题!
一个志愿者回忆:“当初进去的时候,认为这个毕竟算是一件比较高尚的事……比较激进,做着做着心态开始平和了,发现如果想去做事的话,你必须以一个很平和的心态,激情不可少,但必须自己职业化,否则你做不长的。我每天面对艾滋病人,要定期访问、送药检查,调查村子里艾滋病人遇到的阻挠。后来告诉自己,不要把这看做一份高尚职业,只能说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我喜欢这份职业,我的兴趣在这里,不再自认为很高尚了……是我选择了的,后来心态平和了。”
“这份工作不仅仅是救济,不仅仅是使自己得到满足。”对病人的保障、孤儿保育,“有民间在做,有国际NGO倡导,也有政府的责任和意识……通过社会的力量、民间的媒体、国际的压力,也触动了政府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要让政府从没有作为到有作为。后来,2004年始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病人握手、温家宝总理过年时到了感染者最多的村。……是一个整体社会的认识的过程,要整个社会、政府学习,否则很难改变病人的状况,也要其他机构的配合。”
“NGO的行动往往引起媒体的注意,激情冲动的呼声大,而缺少在基层做的人。你可以统计,国内的办公室在北京、昆明、成都城市里很多,下面做事的人不够,除了几个本土的。我们在艾滋病村来回跑,我们缺乏人和支援。资源还在上面,我希望资源下沉,人力、物力、财力。什么做项目的人员流失?他们2005年非要在北京设办公室,说好筹款。开封办公室才400块钱,但那边一套房子就3000块钱……包括人员之间的问题、项目之间的问题、管理团队和项目团队的问题。管理团队不懂!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走,只有平行线没有交叉点,冲突很大,根本没共同语言。我们提出北京办公室的人必须得在项目地选拔,先在这个地方实习。招聘的条件是:工作地方不是上海和北京办公室,而是项目地,然后在项目这中间选拔人才,提拔管理人员。因为这种是很优秀的人才。刚开始我可以靠激情来做;但你发现人多了之后,资源上浮。一个组织出事:一个是资金问题,一个是人的问题。资金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嘛!人怎么去沟通?怎么去做项目?管理团队怎么做?我们看团队发展得不是特别好。我喜欢做事落到实处: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更多地偏向在社区怎么做,希望把脚扎在泥土里面。你可以做一些高喊口号的,但我希望在下面,不希望浮在上面,那是没有用的。那和我的东西正好相反了。我们(NGO)原来是自下而上,现在(趋势)慢慢地偏向那么所谓的主流的NGO去做呢!我疑惑了,在寻找一些组织不这么做的,所以就来了阿拉善!”
最初的任务
NGO“促进、转变啊,不知道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但有人做它就有一定的理由吧!”有些成员参加过培训,“如果参加过主流培训的话,会发现培训的套路是大同小异,一开始很感兴趣,听多了之后思考一下觉得都一样。比如先来个互动,先介绍人员,只是方式不一样,之后再来个什么别的活动,你会感觉没有多大的区别。这里(阿拉善团队)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这里空间给得大,在一种环境氛围里面……给了各种的讲座,是一种意外的惊喜。”
SEE团队的吸引力是,“邓仪对从他的草海项目一直到现在,他对SEE的专注。他对项目的不断的追求,特别是在中国现实环境下,他一步步往上走的追求,不仅是收益上还包括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程度上……这种实际行动已经超出了现在一般项目能达到的效果了。所以,我们听到师姐师哥说,就来学习”。
一个初来的志愿者到腰坝贺兰队住下来,邓老师只是说:“这个平台,你有多大才能你就发挥多大能力。”工作是:“你就去听,多听了就明白了。去认识这个东西,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正好村民在准备建一个自动化挤奶的奶台方便集中挤奶。从2006年春村民开始提议,村民自己慢慢地要沟通,说要建个奶台。他们非常着急了,一直进行了两个月,就是怎么集资啊,怎么建,建在哪啊,我去那会刚好就是经历了这么个阶段。我住在那,村民没事就说这些嘛,我很容易就接触他们。我就待在那里听,前期听不明白,就找他们了解啊,找他谈啊,然后有的人就很乐意跟你说嘛。听多了就明白了。”
团队管理者让志愿者“试一试,给他们空间,找到自我感觉”。这与志愿者的目的吻合了,他们就是来寻找选择的。
随着实际问题的出现,他们遇到冲突:自己的满足感与目标人群的需求,与自己的能力。他们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NGO,他们常常私下交流,发现大家的经验有差异,能学到的东西不同,就互相介绍经验。
在初入NGO时,他们的状态非常不稳定。大部分的NGO缺乏人力资源的支持和辅导,包括SEE这个执行团队。志愿者在大学同学和公益事业同伴中建立起了一个网络,心理上有了“危机”和困惑,就找NGO师哥师姐,天天用手机和电邮交流。师哥师姐们要照顾师弟师妹,帮他们解读受到的冲击,提供心理上的安慰,互相分析情景,议论各自NGO的利弊,讨论着全国每个NGO的领袖的作为。一个冲动或一个好心介绍,一个团队成员就可能跳槽,这常常使团队措手不及,导致项目执行受影响。
例如,一个志愿者看了SEE的网页:“网页上挂的东西吸引我的没有啥,SEE也不太受社会欢迎……最吸引我的是师兄跟我谈的邓仪。我就到会计事务所跟师姐说我要提前终止合同,就来了SEE。”同样的情况有几个,听到朋友讲内生式的故事就来了。他们“确实没想过远大理想之类东西,只想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朋友也说到我们这里来,可以的话就在协会一直待着,不行的话再去别的地方”。
正所谓:NGO聚集了有理想有热情的志愿者。他们长期在社会基层,资金和社会环境的压力、个人成长转折、团队管理、项目前景等等,都使组织和他们自己常常陷入危机,至今成百上千的NGO就三五人的规模。许多组织多次裂变,团队人员来来去去,项目实施不连贯。他们走时又介绍新的志愿者来,来去时也交代去留的利弊。
但在这一阶段,他们倔强而坚持。所以,企业家来了,他们也要把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观亮一亮。企业家对团队对他们是又爱又气。有些价值理念这代企业家甚至30年前就在讨论和考虑,如今碰到比自己当年还要牛的小青年,尽拿些词汇来糊弄卖关子。但他们毕竟刚刚迈出人生第一步。他们也常常被误解为主流工作市场外的另类,有人甚至十年都走不出第一程路。师姐、师妹、师哥、师弟聚会时,甚至抱头大哭,相互宽慰各自的苦楚和迷惑。采访十多个不同项目主管和团队领袖。但对他们来说,“要没有这个经历,就不可能了解之前不可能接触到的,想先要这个经历,然后再追求我想要的生活”。
团队专职成员
志愿者和社区干事尝试了几个月到一年,可以申请留下来做专职项目助理,或者项目官员。但必须考试,有四个问题,每个谈三分钟:一是SEE协会的作用是什么?二是项目的作用是什么?三是项目官员的作用是什么?四是社区项目的主体是谁?主考和旁听的有团队的主任、项目主管和其他成员。
项目意识
项目官员要独立承担项目,“效果”两个字有分量了。自己的责任是“做好一个项目”,或者“做一个好项目”。留下来的人是喜欢挑战的人。
我是特别不害怕变化的人……很习惯从一个角色转换到另一个角色……我特别喜欢工作中和生活中有新的东西不断出现,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状态,但这样的过程我是比较适应和喜欢的。走一步不是盲目的,而是越来越清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学习对他们是一个认识比较的过程。一个项目官员发现,各行各业执行和流程管理有逻辑上的相通之处。
像以前我做那种公共关系啊策划啊什么的,也是这样子的呀,也是遵循一个逻辑关系的,整个过程怎么去控制……我是觉得项目管理这块在各个行业它是相通的,思维方式是相通的。自己在公益事业中没有工作经验而且背景也很弱,但是可以在工作中慢慢去学嘛!
有了感受后,这个成员就找团队领袖讨事做:“[我]希望有机会做些项目方面的工作。”
要探究的重点慢慢清晰起来,进入SEE团队是要来学习做成“发展”的事。
我是来自农村地区的……我一直在思考,如果要摆脱(农村)目前这种状况,无论从经济状况、物质增长,还是从人们的思想啊生活啊有所提高的话,我就读了发展学……但这下我更困惑了,找不着出路了。我的老师有很精辟的见解,如果要实际做的话,就未必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能踏踏实实做点事。SEE协会在行动力方面哦,邓老师做的这个东西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跟师兄谈过,在网上也去看了,从人为因素做到社区发展这一块哦,如果能把发展跟生态都做好,是我更高一步的追求了。看到SEE协会发展这一块,我就来了。……做项目需要整合更多的资源进来嘛,当时没有整体的一个思路,是比较零碎的。从实际过来后,我觉得,更多的感觉是从实践中过来的嘛。
邓老师比较喜欢说的话是:你去听听农民说什么?你下去看看。不要把自己的想法认为是最合理的想法!
项目官员要住到村子里,项目主管给了个嘎查里的联系号码,官员就自己开始安排了。一个官员叙述了他的经历。
我自己坐班车,碰到那个村的一个大嫂也坐车,我说我到“贺兰队”,她就把我带去。到村子里我找到书记家,说明了来历。刚好他们吃中饭,我就跟他们吃了……我住在队部,吃饭每天吃一家。我大概吃了30多家吧,吃了一个半月。这样下来,对村上的每家每户都了解了,就是还没有吃到,也天天露脸,上人家家说说聊聊天啊、干点啥的啊,大家相对来说就比较熟了哦。他们就开始找我说事情了,慢慢我也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了。
白天在村子里走走看看听听闲聊,晚上跟几位村民讨论,周末回到团队跟主管报告,跟团队分享。成员有来自发展学、人类学、公共关系策划、环境科学、农业经济、林业、矿业、计算机的,南京大学、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等,把学过的知识都拿来与实际比较,跟村民自己决策比较。“以前的工作经验放在这里头……觉得有东西可学。”他们就这样开始在比较中积累。
把经历中一点一点零散的经验、大学的知识、不同NGO的项目、村民的看法,每个人把不同场景的经验放在一起,像把过去无意散落的珍珠一粒一粒又拾捡回来,用线串起来。
在这种集体讨论和分享中,在村里,在团队,自我追求逐渐淡出,更多是“老百姓关心什么?他们要想做什么?问题在哪里?不同的人怎样看这个问题?”这是项目官员“做事”的一个逻辑的线头,也是一个重要的认知突破。SEE团队成员曾经有这种安全的环境,团队的头两年里,成员愉快地成长,项目进展顺利。
工作任务
嘎查的水碱分很大,老百姓请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在家里聊天喝水,都“兑一些糖再喝”。“从本科时候开始,跟着老师做项目评估的时候到相当辛苦的一些地方,再加上(我)是从农村来的,有心理准备。”
我问他们:“上这些家除了吃饭聊天,你有特别的任务吗?”
没有!我都希望邓老师给我任务,那我就不用动脑筋了。当时他是这样说的:给你这个平台,你有多大能力你就发挥多大能力,你们是来应聘项目助理的,这个平台就是提供给你的。
他们要找到“农牧民自己愿意做的事,那才叫项目”。这个项目官员就住进了贺兰队村,慢慢知道了“要减缓贺兰山荒漠化,移到腰坝。改种玉米后,生活改变了,收入降低,引起与政府的矛盾,成为著名的上访村。SEE协会提出对腰坝的贺兰山移民做评估,我是跟着邓仪学习,他指导,关键的时候邓会亲自帮助。头3个月,6~9月是对社会的了解。开始经验不足,要邓老师指导,他亲自做推动群众,大家都是在过程中学习做社区基金。主要是给予村民充分的说话的权利、决策的权利。SEE协会成员的角色,是在群众争论中不主导,就把握时间的过程,让各方说出问题,做协商。后来我也学会了。群众有了自主的能力,村委会的能力也提高,项目就很顺利。自己的进步在于,对项目的流程能掌握,并可以反映”。
2006年春天,村民讨论耗了半年的时间,吃饭时村民说,政府的大棚种植不可行,讨论有什么办法?奶台项目是几个养牛户提出来的,大家到乡镇的其他村子看,有兴趣了,我就一起去银川看其他为伊利供奶的村子。回来又与镇政府谈。镇里政府有个养奶牛的项目,要盖养牛小区。这个项目给谁呢?开始,政府要指定一个村子做。后来可能也受我们做项目方法的影响,找了腰坝60~70户人家,开个听证会,有贺兰队,还有另外一个村的一户私人承包户一起投标。投标贺兰队输了,但养牛的几户不放弃,就与外来养牛的大户谈。SEE协会通过一个企业家,认识伊利的老总,伊利的老总又给银川伊利办公室的负责人打了招呼。村民就自己跑到银川去谈奶台修建的要求、牛奶收购的质量、几天结一次账等问题;奶台设备又是另外一家公司的,也是村民自己去谈的商业合同。养牛的村民自己选出有养牛经验的,就成立小管理委员会,因为大管会的人不懂嘛!我也做不了什么,陪着他们跑跑。
半年多村民跑来跑去,2006年下半年达成协议,集资48.5万元建了奶台,有38户村民参加了,集资100股共20万元,SEE协会配比股金25万元,土地折股3.8万元,动工修建挤奶台。
SEE的项目官员“自己是站在这个第三者角度去听去了解去看,看他们怎么争论啊,怎么去选择啊,怎么去自己筹资啊,因为这可能是受邓老师影响吧。我清楚,我自己没什么能力去给他们做些什么啊,或者是给他们决定些啥东西……我更多的可能,就是抱着一种学习啊,这种去观察啊,去了解啊,就这么一种心态。然后他们如果需要我做什么事呢,我就帮着他们做”。
为什么迷上这黄沙滚滚的阿拉善?他们告诉我:“阿拉善地区种玉米、小麦等,人均有4.5亩地,农业人均收入1500元。春灌保墒要抽地下水漫灌农地,有31万亩漫灌,而一亩一年要800吨水。采用漫灌,每年要灌水8~9次,地下水位逐渐下降。大量抽取地下水灌溉,5年后地里盐碱上升,农民只好放弃耕田,搬迁到另一地再开垦。如果种棉花可以增加收入,减少对水的需要量,只需要灌5~6次水。喂牛是秸秆利用对改善环境有好处,以前是整捆秸秆喂牛羊,只有1/3吃了。现在是先轧碎了秸秆,牲口吃的利用率在90%以上。”
两个年轻的项目助理国栋和空军,一人住一个村子,面对的就是这些每天生产、生活的问题。
试验膜下滴灌是政府计划的借鉴以色列的项目,曾派代表团去参观。但两个年轻的项目官员在锡林高勒镇的村子里住了一阵子,发现村民还没有感觉,就先放下这个项目。他们总结:
[一是]说村民的关注和意识吧,村民对节水还没有长期的关注。年纪大一点的人说你“查哈尔滩”十年后还有水吗?我都五六十岁了,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现在有水就行了……[二是]现在村民对统一和大面积种植不能接受。滴灌要求大面积实行。村民都只有几亩到十几亩地,改变种植方法和不种玉米种棉花,农户之间的矛盾也会产生。要大面积统一种植和管理,操作和协调会发生矛盾,有的农户可能要多浇点肥料,而有的人不想种棉花……种植的品种受整体的限制,农户还是习惯自家管理自家的事。[三是]水少用了但投资高了,种植的成本高。种棉花需要大量劳动力采摘,阿拉善缺少劳动力,高价雇人就赚不了多少钱。[四是]还有,换种农业产品市场有风险,棉花能够有买主吗?还没有一定。种玉米这里有三百块钱一亩地,踏踏实实我能赚上;如果有六百块钱能赚钱的机会,但也可能一分钱都赚不上,那他就不考虑了。[五是]另外,农户之间还没有能够协商和沟通。农户不愿意就不能强迫,我们就先放弃了这个项目。
在村子里走访各家,会议上把听来的意见做归纳和梳理,清清楚楚。跟村民开会,他们的讲解明了生动,说话不带盛气凌人的优越感,没有威慑性的语言。
特别的项目评估
国际NGO带到中国一项社会发展的技能、做援助的方法,即PRA,中文叫做“参与式农村评估”,简称“参与式”。这个方法是请村民老百姓参与做项目评估。福特资助温洛克开发了一整套培训教材,训练中国的NGO。
SEE的团队认为,快速的参与式讨论是不够的。NGO有钱,请当地人来“参与”执行外来专家设计好的项目,因为你有钱,人家当然跟着你转,但这不是村民自己愿意做、能够做的。这是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SEE的一套评估方法比较特别,比较慢,但要由村民在自己的组织中决策,承担执行和管理。
项目评估是NGO基本的功夫。关键的问题不是本身的技能,而是理念的差异:项目官员是采取村民“应该做什么”还是“他们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的态度?专家是要满足自身做公益的雄心,还是让当地主体自己决定做什么?而SEE团队定义:“应该做什么”多是上级政府、外来的专家学者定义的目标,是优势群体的经验;本地群体的价值观、行动特征和能力很少被考虑。而“自我需求评估”是村民自我发现和自己的设想。
团队成员告诉我:“需求评估说白了就是去村子里,看人家自己想做什么东西,条件成不成熟。下去第一件事就是跟村里的村委会或者项目管理委员会沟通一下。前期当然有一些铺垫,我们才下去,告诉他们我们来做这个评估,听听大家的想法。评估的第一,先要与地方管理部门沟通,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获得通行证进入村子,包括镇的政府机构,要让他们了解协会团队做项目的目的。进入村子就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沟通,开个村民大会,介绍SEE协会的背景和目的,最重要的是说明:我们不是来做我们的项目,是和你们一起讨论你们的项目。”
第二步,与村民见面和沟通,以大小会议、入户的方式介绍背景。参与式的会议是可以采用的一种方法,了解村民们对自己村子的状况做初步的参与式的评估。大家坐下来,把村子的问题、资源、解决问题的设想,都一轮一轮地讨论。但PRA快速式的方法也有不足。如果NGO项目官员只在当地一两周内做几次PRA的方法,就把外来专家的模式转给目标群体实施,还是不够的。村民经常会上能讨论,但第二天又想不通了,反悔不做了。当NGO的成员一走,项目就停了。所以这个团队改革了项目步骤,一再对村民说:“我们来不是来做我们的项目,是来支持做你们的项目。我是来听你们的想法。今天我们就是听听你们自己的一些藏在心里可能很多年想做,但是还没有能做成的事情。”他们不着急马上找到解决生态种草还是种树的方法。这个方法要老百姓自己拿。
第三步是要在整个村子里做调查。会议上不能了解到问题的全面,用专家的指标也难以衡量所有的问题。“开完会后,我们会一家一户去选,在整个村子里面,也是根据要做的这个项目来先选几户再深入访谈。会上有的人性格较内向,有的怕说不好就不说话。我们选农户有不同考虑,第一是从经济的标准说上等户、中等和经济不好的家庭,各选几家;蒙古族、汉族混居的嘎查,蒙古族要访谈几家,汉族访谈几家,有不同的因素为选择参照。项目官员与村民深入接触,双方的角色定位十分重要。项目官员掌握的是,在心理上把自己外来NGO那种优越感完全撤出了,明确来的目的是协助(facilitate)。他们是主体,他们的意愿是行动的动力。要慢慢地,谈得很细啦。包括说有搬迁的问题,你可以问他:你老家是从哪里搬来的?历史,包括家庭现在的状况、生产情况、生活情况。这种细的访谈里面会涉及他很多细节的情况,像生产上的作物、市场、用水,用水又涉及生态啦。然后养殖和种植也是,养什么羊、饲料哪来。生活上他们会告诉你新柴烧什么、用什么,你再去看他的嘎查能源消耗的结构,背后的传统和价值的东西才可以问出来。所以说,(PRA和社会调查)这两个大的步骤结合起来,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需求评估。我们基本上就是这么做。”
这位人类学出身的项目官员,在PRA和专家的硬的生态指标外,采用了研究访谈的方法,引导农牧民自己理解和重新建构这个小社会的过去,要面对的现在、将来。比如:“你们过去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为什么现在突然要让你们搬迁?这个搬迁是不是你们自己愿意的?”有了真诚的尊重和聆听,村民很快就如冰释水,坦诚相交。
这个第三步的交流是项目官员与村民单独的比较多。SEE成员去一家一户了解时,可以得到许多会议上得不到的信息。村民私下比较愿意讲出自己的困境,不太愿意在公开的会议上说。很多政策研究者做入户调查,也能得到很多信息,然后就满意地回到办公室制定计划。但最重要的被忽略了:村民之间还没有达成共识,最好的从上至下的政策,也往往失败。
社区的集体行动必须有协调,村民要相互了解。第四步,看到村民有想法,SEE团队这一步要引导村民交流和沟通。他们建议有意愿做项目的村民自己开小会,讨论和分享各种想法,在公开、公共会议上分享自己的思考,把归纳和比较的方法都用上。例如200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贺兰队讨论入股集体养牛的方式,小管委会干部请驻村项目官员做开场,项目官员说:
我其实不懂,我就是在贺兰队到处转,听听大家的想法,把大家的意见理出来,给大家对比优点和缺点。第一,入股牛场养殖成本低,统一在牛场,统一挖一个大的取土池,比一家一户挖一个节省人力和物力。在家一个人养四五头牛,一天喂几次,劳动力被限制住。入股后,在牛场一人养50多头牛,你自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赚其他钱。另外一个优点是,议价的权力。一家一桶奶量小,收奶的说多少就是多少。如果养了两三百头牛,有几吨奶,可以与收奶的人讲价把价往上提。另外,在奶场统一饲养、统一防疫、统一管理和销售,这也是一个节约成本的过程。再有,一家人管理不好,前几天谁谁的牛管理不善,就去世了。(大家都大笑起来)我在奶台看到收奶的情况,很多被打回去,有奶过酸的,有偏盐了,含菌量高的,这就是一家一户养殖质量不好控制。牛场统一管理,可以避免这些问题。还有一个是,股份制牛场,所有的股民都有权利管理,可以共同关心,齐心协力,提高养殖水平。缺点和限制有两点:经验缺失,以前没有搞过这样的大规模的集体养殖,管理人员会缺失。另外就是,入股以后,不是一家人说了算要大家一起监督。
三四分钟,项目官员概述了自己的观察,就把话语权交回给村民。他们在村子里的基本功就是观察和聆听,放弃自我地听。半年后,他们就学会了比较和分析的基本技能。我在场做了录像,这么简短而又把观察梳理得井井有条,幽默又在理。
召开会议的技能,是要“调动大家那种互动的氛围,让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看当时的情形,如果有时理解起来比较困难的,就需要诱导,慢慢地把他的思维引过来,把他想说的话让他说出来”。例如,要让草场恢复,要村民减少羊只是很困难的,项目官员就问他们,如果继续居住在草原上,“已经没有草了,羊吃什么?”村民的讨论也很激烈,项目官员就引导他们:“别人怎么看你的意见?资金不够怎么办?集资后怎么管理啊?其他人同不同意啊?”要让他们集体讨论这个社区面对的生态和生计的问题。
第五步是形成村民决策,利用村民委员会提出自己愿意做什么,可以做什么。村民在项目官员启发下,互相交流了。牧转农的贺兰队有人提出了:“我们想养(圈养)羊,但是我们技术不行。”贺兰队有多户提出养牛收入高。当这些话从大多数人的嘴里说出来时,项目官员就知道各家各户的想法有了一些共识了。要保护草场不是一家一户可以做到的。
第六步,村民想要做事了,SEE团队就建议村民成立自己的项目管理委员会,集体开发项目,自己管理。这时,项目团队就撤出来了,只作为项目管理委员会可以寻求的外来资源和咨询机构。当管理委员会里的村民们讨论和提出共同商定的项目—决策后,再来找SEE团队申请支持。例如在他们的小管理委员会会议上,村民经过讨论,意识到每家过多养羊,自己草原上的草就长不起来;嘎查的农牧民都住在相互挨着的草场上,他们要一起面对现在、将来。村民就自己制定了保护草场的村规民约,考虑草畜平衡,把每家羊按照120亩一只的比例减少,每家都卖了三四百只羊,只保留100只上下。他们就制定了全体村民要遵守的村规民约。
第七步,团队在当地设立了项目申报会的公共法权机制,参加评审项目的有几个社区项目管理委员会的代表、当地的专家、政府代表、协会团队的代表。所有的社区项目要在项目申报会上公开宣讲,再由评审团匿名评分,最后总分最高的前十个项目获得资助,但必须根据公共的评议做项目改进。
项目评估就是与村民沟通,引起他们自我做评估。项目官员耐心地听,是有意识地让村民学会表达,引导他们自己考虑做事的条件和资源,如何管理和执行。
团队领队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村民小管理委员会炒了一个项目官员的鱿鱼!一个村民小管理委员会制定了自己的保护草场的村规民约,也与团队签下了生态项目的协议。但这个小管委会成员一致要求团队换掉项目的干事。原因是,在项目过程中,村民发现这个项目干事“用自己知道的套路来教化(村民)”,坚持要他们服从某一个外来的成功模式,还发脾气。
这就是内生式项目方法,内生把外生的挤走。
用什么考试标准来决定一个人留下来或者选择离开?项目官员的看法是:“不是(学习)快慢的问题,是个人带的那种价值观。个人先入为主的这种很难改变的话,会影响对新事物的理解。接触社会少,对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上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很难把握住,要么就是非常极端,要么就是非常不作为。协会团队需要一个非常良性的,能够跟政府,跟村民,跟各个方面处于一个非常好的沟通机制的观念,(有的人)一时半会转变不过来。我们这些学员里头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其他组织里头做过两三年的,会问‘为什么这个(生态)奖要给一个政府做的项目?我们应该给那种很弱势的小的非政府组织,因为他们需要帮助。政府都是假大空的’。年轻人多的社团和组织,我们自己也经历过,很容易被激情的东西控制住而认识不清,只觉得我们在做贡献,政府也不对,整个社会都是不对的,我们需要扭转这种不公平。”看问题比较简单,想找一个一分为二的清晰。
一些团队人员能在成长中随着经历而变得成熟,越过偏激和固执己见,越过黑白分明,越过与政府对立的简单思维,随社会环境复杂性来认识问题,包容多方不同的看法。后来那个认为不应该给政府发奖的项目志愿者离开了。
项目主管——专业从业者
独立执行了几个项目后,有经验的项目官员就可能升任项目主管,他的任务包括协调项目点工作,督促项目官员和监测进度,指导志愿者、项目干事和项目官员。各个项目点进展不一致,工作头绪多,项目主管要在几个项目点之间奔波,做支持项目的工作。
过程与相关群体
项目官员是自己做一个村一个点的项目。项目主管要注重整个过程。“做项目是个过程,两三天就得下去,要盯着发展的进度才能协调几方的配合,平常要定期地下去,检查项目的阶段性的进展过程。”在工作中超越孤立的工作任务,视野朝着未来的成效并为其努力,而非听任上级主管的指令,这是一个专业管理人员的标准。
一个女项目主管说:“我住在下面两三个月都行,尤其社区,我不想回北京,起码目前这几年,因为我觉得在北京做不了想做的事情,就想回巴彦浩特待会,洗个头洗个澡。我挺喜欢现在这些社区工作的,我觉得这是可以长期发展的一个行业。基层工作的这些经验是一定要有的,至少得要有三年,要把整个项目的流程过程都要经历一遍,而且是要完整的,起码是一年期的一个过程,不是蜻蜓点水的那种。而且我跟村民承诺过的,我说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管理项目中最难的是几方有不同意见:“了解流程比较有把握,但具体推动(几方)这块还没有把握,不好说……每个项目里头实际也是一个更小的管理循环嘛,但在这里头可能就要和涉及的各个利益方沟通。这块我觉得是我需要锻炼的,就是利益方之间的协调。
“要了解不同体系那个话语的方式,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是最重要的。例如,我换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就知道那个问题出在哪了,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哪儿入手。对这个群体(村民)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个项目推不下去的话,我就从他们那个角度想,问题出在哪呢,我这边怎么帮他解决。”
做节水也好,减少羊只也好,节水灌溉也好,村两委会、大小管委会、村民、政府各个部门、市场上的各种机构等等,政府往往是最棘手的一块。但“政府职能人员也有自己的苦衷嘛,以前打交道较少,不了解。然后,慢慢去了解和认识嘛。如果你不能了解到他们内部的一个循环的状态,你是根本没法去做沟通和协调的。我也会让他们去了解我这边是怎么想法的”。
如果做项目官员时功夫扎实,协调会比较容易一些。但如果是空降兵来的专家,落到村子也难以施展。这个功夫要社会场景知识,而非专业知识就能搞定。专家来了常常犯的毛病是,用空降专业知识画一个模式,结果是不了了之。建立几方可以接受的解释语言是推动几方协调的必要条件。
项目主管的社会架构又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