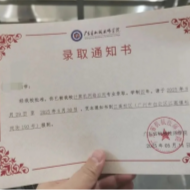2023-03-21
2023-03-21
 962
9622月6日,土耳其发生两次7.8级强烈地震,受灾人数超过1350万。这意味着在土耳其的6个人中就有1人受到了地震的影响。
3月13日,土耳其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卢表示,大地震已造成土耳其至少4.8万人遇难。这场地震及余震让土耳其境内有超过11.5万人受伤,5万栋建筑倒塌受损,数百万人不得不转移到其他城市,或是选择在帐篷里蜗居。

▲图片来源于《三联生活周刊》 黄宇/摄
地震发生后,近100个国家响应了土耳其的国际援助呼吁,其中84个国家派出了大约1万多名救援队员,为灾区输送了物资和专业救援力量。其中,官方派出的中国救援队哈塔伊省开展搜救,圆满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国际上的赞誉。
值得关注的是,来自中国社会应急力量的救援队也获得了广泛报道:公羊救援队、蓝天救援队、平澜救援队等深入一线开展生命救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北京新阳光基金会等基金会也开展了救灾响应、灾后重建等各类支持工作……
中国民间救援队如何有效参与国际救援?如何更好开展协作?本文为发展简报与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成都授渔”)王海波的对话。供读者参考。
01 土耳其救援一路“畅通”,依然困难重重
2月9日,中国应急管理部下发通知并指导成立“中国社会力量参与土耳其地震响应协调大本营”。
来自成都授渔的王海波和同事程明理在接到通知和任务后,在第一时间就赶往土耳其灾区,协助应急部筹备大本营,“大本营的工作,包括救援队的报备与登记、现场作业协调与开展,以及后勤对接等各类工作”。

▲中国社会力量参与土耳其地震响应协调大本营合影
实际上,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中国民间社会应急力量不断发展。数据显示,目前在民政等部门注册登记的社会应急力量约3000余支,全国乡镇街道建有基层综合应急救援队伍3.6万余支。
成都授渔就是在驰援汶川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组织,王海波介绍,“当时汶川灾区几乎所有的应急饮用水净化,都是我们做的,大概有100个工作站,每个站点能满足2000多人的饮用水需求”。此后,他们参与到了青海玉树地震、河南水灾等灾区救助和灾后重建的工作中。
“授人以鱼、授人以渔”,成都授渔也广泛参与行业能力建设,尤其重视全球范围内已经被广泛参考的《环球计划手册》,这也是他们此次驰援土耳其,参与国际救援的能力体现。
CDB:灾害之下,救援队首先需要具备哪些基本能力?
王海波:救援队要有“快速预判、快速动员、快速出发”的紧急响应能力。第一时间对灾情作出研判,决定是否有赶往现场的必要。
首先要评估灾情严重程度。例如,2022年9月四川甘孜泸定6.8级地震暴发,现场的受灾面积并不大,通过消防力量和周边救援力量就能够覆盖,当过多的救援队涌入现场就会适得其反:最为关键的生命通道可能被拥堵、当地政府将承担更大的救援压力、现场秩序很容易混乱……所以救援队对灾情的研判很关键。
其次,要分析灾区周边救援力量分布以及自身队伍的专业对口问题。在决定出发后,第一时间响应的机动能力很关键,如果救援队准备时间过长,甚至都已错过了“黄金72小时”,那么到现场的必要性就大大减少了。
CDB:在第一时间响应后,你们是如何进入土耳其灾区现场的?
王海波:国内队伍到土耳其参与国际救援还是面临不少挑战的,包括出国前的准备、资金筹措等。这一次的旅途舟车劳顿,到土耳其都需要20多个小时左右,基本没有直飞航班。
很多队伍对于国外情况了解不够深入,但这次土耳其当局在国际救援衔接工作方面做得很好,非常流畅,值得中国和全世界学习。
土耳其灾害管理局(AFAD)管理体系和工作系统很成熟。我们的航班在伊斯坦布尔落地,他们只要看到身着救援队服装的队伍,就会上前引导。这样一来,救援队办理出机场、走海关的手续所费时间就大大缩减了,直接由警察带领,配备一名翻译人员协助,还会安排专机运送到震中地带。
到了国际救援的大本营,救援队就可以安营扎寨了,每天的工作量、交通、撤离等问题都会有专门的安排。可见,对接沟通、翻译以及后勤的工作都被土耳其当局解决了很大一部分。
CDB:在土耳其灾区救援,面临了哪些难点?
王海波:土耳其地震的灾情非常严重,破坏力极强。我经过了一个震中的城市,它的惨状就像2008年汶川地震中的北川县城,其城市规模要更大。所以在现场能看到很多建筑是粉碎性倒塌,甚至是“叠汉堡”式的倒塌,个别仍伫立的建筑也是在根基出现了裂缝,摇摇欲坠。

▲图片来源于《三联生活周刊》 于楚众/摄
在这种世所罕见的大灾下,中国救援队会碰到各类难点。首先是语言不同的问题,虽然土耳其方配备了翻译人员,但在救灾现场的话语体系不匹配、翻译不精准打折扣的情况时有出现。语言背后也有文化差异,比方说中国救援队会通过“拍照”记录救灾过程,用以存档和结项等,然而穆斯林会难以接受摄影机拍到遗体或者遇难人员,甚至认为这挑战了他们的文化信仰。
其次是物资装备和保障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不少中国救援队属于长途跋涉、轻装上阵,有的重型装备带不上,也导致了现场救援很受限。像破拆这类装备,能带上的都是少数。另一方面,后勤保障常常会短缺。灾区是很混乱的,甚至是“兵荒马乱”的,一些中国救援队在到达后的三四天都吃不上热饭。
CDB:如何应对救援现场物资装备短缺的问题?
王海波:“合作”是国际救援的关键词,能够有效应对物资等问题。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参与土耳其救援的社会力量。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突破了重重阻碍,在协调、资质申请、物资保障等方面为中国民间应急力量提供了很多支持。此外,2月9日应急管理部指导成立的大本营也以“政社协同”的模式助力国际救援。
在“物资保障”层面,我这次去的主要工作也是协助大本营的工作,在赶到土耳其后,从阿达纳购买物资,找车开往灾区,为中国救援队做好保障补给,为他们准备了热饭。经过一段时间的物资紧缺后,中国大使馆、当地的华人以及商会也都来支援、捐赠。因此,救援最初面临的紧缺问题很快也被多方合力基本解决了。
在“装备短缺”这个层面,多数中国民间救援队也是采取了“合作”的模式。比如说,我们的很多救援队都携带了生命探测仪,会跟有重型破拆装备的队伍合作。
另外,在这次土耳其地震中,三一基金会在安塔基亚灾区投入了40台挖掘机、10台起重机等,在整个土耳其的设备投入超过100辆,这相当于十多个重型救援队的力量。徐工集团在土耳其也保障了中国国家救援队的挖掘工作。
这让我看到了未来中国民间救援队和中国驻外企业之间协同合作的可能性。今后,民间力量可以预先与这些企业沟通,形成对接机制,提高国际救援效率。
02 “政府+社会力量”大本营首次跨出国门
土耳其-叙利亚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国应急管理部就特别联合了国内多家基金会、救援队成立大本营,为前线队伍登记报备、对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土耳其灾害管理局(AFAD),还专门开展了当地文化习俗禁忌、相关风险等方面的培训。
“有中国官方组织协调社会力量参与国际救援,这应该是第一次”,王海波介绍,大本营的这种机制能让让中国的社会力量安全、有序、有效参与国际人道主义响应。
据统计,“中国社会力量参与土耳其地震响应协调大本营”从2月9日建立到2月16日关闭,累计作业面积约20万平方米,搜寻和救援23位幸存者、181位罹难者,得到土方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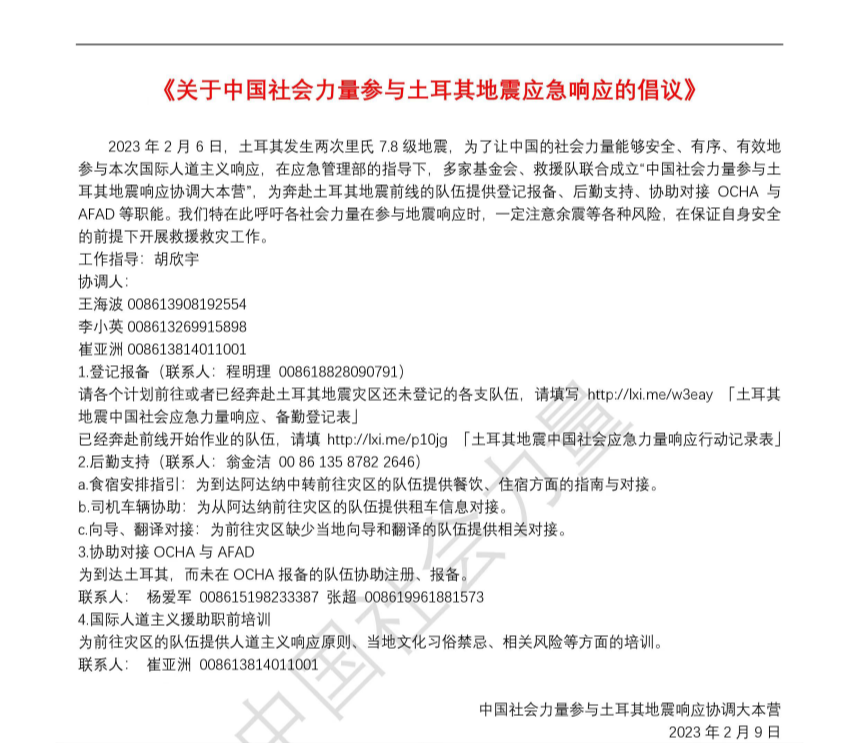
▲图片为《关于中国社会力量参与土耳其地震应急响应的倡议》通知截图
CDB:在面对应急灾害之下,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有哪些经验?
王海波:“政府+社会力量”协同的应急救灾模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多次的碰撞与磨合。
2008年,中国社会力量意识到汶川地震的无序与混乱让救灾效率低下,需要从零散的状态走上合作。而后,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抱团取暖”,在救援中互通有无,形成合力。
2013年,雅安地震中有超过700家社会组织、1.8万名志愿者先后参与救灾。大量外地组织和志愿者对实地情况了解不多,热情高涨与专业匮乏形成的冲突亟需高度统筹。于是,四川省负责救灾的指挥部成立了社会管理组,有效指导、衔接、开展各类工作。
后来,“政社协同”的救灾模式越来越成熟。2020年安徽水灾现场,政府成立了协调中心,并主动对社会救援队伍调用,还安排了食宿后勤保障,这次协同堪称完美。
2021年河南水灾中,在极端暴雨的第二天,应急管理部救灾协调局就直接下发公告,请拟前往参与应急救援的社会应急力量先与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取得联系,经同意后再开赴现场展开救援。当时,我就作为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一员,姓名和电话都被写进了公告中。
CDB:在国际救援场景下搭建政社协同的大本营,有哪些不同点,遇到了哪些问题?
王海波:目前来看,中国“政社协同”的救灾模式已经具备一定经验,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我印象中,中国官方协调社会力量应对国际特大灾害而成立大本营,这应该是第一次。
在国内,我们与多数救援队都很熟悉,对于登记报备、对接流程之类的业务,大家也都很清楚,所以,国内大本营成立得快,统筹效率也比较高。
在国外,大本营的协调难度成倍增长,要向联合国、土耳其等相关部门报备,要与灾区营地对接,要统筹好各个队伍的工作,还要对当地风土人情和宗教信仰的情况了解。
面对陌生的体系和非常态的流程,我们这次协调的大本营在部分前瞻性的事务上处理得不到位。因为当时很多参与筹备的人也都在路上,国际救援协调的经验不足,大家对于协调的整体框架也还不够健全。
后续,我们会制作国际救援的协调手册,不断完善网络的搭建,也对于中国救援队的能力进行评估,给予相应的配套支持。

03 不能只顾埋头干活国际救援需要找“痛点”
3月12日,全国多支社会救援力量代表齐聚湖北省随州市,参加“社会力量参与国际人道救援及灾后重建”研讨会。
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司原副司长、中国国际救援队原领队尹光辉在研讨会上介绍,此次土耳其地震,中国社会应急力量共17支队伍,超441人赴土耳其、叙利亚参与地震救援行动。“我们的社会应急力量,逐渐在成为一股国家的有生力量。此次救援相比尼泊尔地震,中国社会应急力量有了很明显的提高。”
随着中国社会组织不断发展,“走出去”成为了很多人关心的重点。人道主义危机之下,国际救援更是至关重要的课题,如何发挥好社会组织优势、找准对外援助的痛点,也成为了共同面对的问题。
CDB:您认为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救援有哪些必要性?
王海波:首先,全球各国会评估灾害的等级和严重程度。这次土-叙地震,其威力和伤害都很大。受灾国本就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很难再要求当地人民再承担全部救援任务,其他国家基于人道主义很难袖手旁观。在此次地震发生当天,土耳其内政部长索伊卢就表示,该国救灾应急响应等级已提升至最高等级,同时呼吁国际援助。
其次,土耳其的受灾人数超过1350万,总人口超过8000万,全国有接近1/6的人处于灾难的混乱状态中。可想而知,土耳其当地的救援力量也会极其有限,亟待国际救援力量进入。我这次去了现场后,发现每个人都处于忙乱的状态,对于救援和物资的需求是海量的,供给的缺口很大。
大灾难面前,非常“耗”人。当地救援队需要挖掘、清障、排险、安置遇难者、转移灾民等等……我们经历过5·12大地震,当时大量救援力量都扑在了各类繁杂工作中,“搜救”这类更耗时的工作就需要国际救援力量帮忙分担。
最后就是受灾国缺乏搜救装备的问题,就比如专业的搜救犬数量,这对于生命救援很关键,只有汇聚全球的力量,才能说勉强够用。其他的各类装备也是如此。
因此,中国民间应急力量要按照国际救援的标准和要求历练能力,不断“充电”“升级”。
CDB:在土叙地震救灾过程中,中国民间救援队有哪些优势和问题?
王海波:“生命搜索”,是中国民间救援力量在土耳其发挥的最关键的作用。
大地震让很多楼房坍塌,救援队就用生命探测仪第一时间搜索20-30米的范围,定位受困者,再配合具有较强破拆能力的队伍开展营救工作。
其实,很多救援队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等问题,没有带上重型装备,甚至有些装备还在转机托运过程中丢失了。但不少救援队都配备了生命探测仪,价值几十万元,这从侧面也说明了近年来中国民间力量快速发展的势头。
我们需要不断提高能力,也要面对现实:在无法携带重型装备的条件下,中国民间救援队如何发挥优势?
这次我们有接近500人奔赴土耳其现场,数量相比其他国家并不少。我认为救援队走出国门后不能只停留在“埋头干活”的阶段,要根据自身能力和特长,更有效地参与到国际救援体系中。
“生命探测仪”就给了很好的启示。中国民间救援队可以聚焦在高精尖设备支持和使用上,让定位更清晰:一个3人小方队带上生命探测仪就能工作了,5人队伍也可以再带上切割机等破拆装备。甚至也可以将这样的小方队统编到具备挖掘破拆的大队伍中,精准负责单一领域,提高搜救效率。
CDB:在土耳其救灾过程中,您有哪些感触?
王海波:在这次救灾中,我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参与国际援助的主力国家有60多个,所有救援队员在与生死赛跑面前,都不分彼此、协同作业。
我还看到了志愿者的力量,到了土耳其后采购物资的过程中,遇到了一对当地的夫妇,他们得知我们身份后非常热情帮助。这也让我思考:参与国际救援的中国社会组织也需要充分发挥当地力量,发挥更多人主观能动性,共同应对灾难。
我也看到国际救援体系搭建的价值和必要性。从装备存储、专业能力、协调对接,再到大本营搭建、国际救援协作,都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学习,最终形成行之有效的体系。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