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27
2022-09-27
 328
328幼儿园虐童、养老院老人受虐……公共服务领域问题频发,公共服务领域为何会出现上述问题?
互联网众筹平台”水滴筹“再登热搜,95中华慈善日,99公益日,众多公益组织筹款进行的如火如荼,两者究竟有何区别,在筹款领域“水滴筹”是公益还是商业?
“教培行业”深陷困境,资本为何迅速降温,到底什么是非营利?哪些事情必须依靠非营利办法?非营利与商业的边界如何界定?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社会创新50人第6期“如何划分公益与商业的边界?”,邀请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所副所长金锦萍教授,为我们解读“如何划分公益与商业边界以及热点事件中反映出的非营利性缺位问题”这一重要的社会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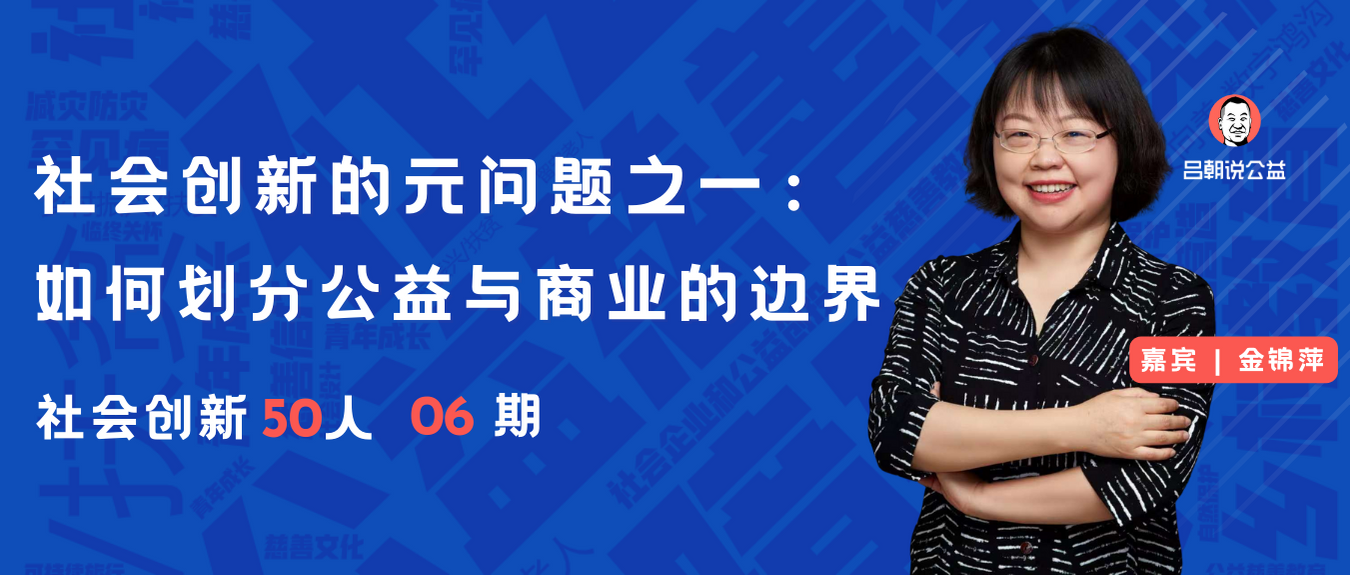
*本文精选自:「社会创新50人 」直播节目第六期——如何划分公益与商业的边界
01 什么是合约失灵理论?
吕朝:我们经常在短视频中看到幼儿园虐童、养老院虐老等让人触目惊心镜头——在幼儿园老师对孩子实施暴力,养老院工作人员虐待失能老人。这种问题并不是近两年才出现,我们进行过统计,大概在十几年以前甚至更长的时间就存在这样的案件。
这些组织很多都是营利性的组织 ,比如说幼儿园,它是企业型的幼儿园,养老机构也是企业型的养老机构。那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如果它是非营利的就不会有问题了。或者说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让他们都变成非营利、完全由政府来提供服务?
金锦萍: 从这个问题出发,比如说我们讲公益事业的时候有人会说科教文卫体都属于公益事业,认为公益事业是一个领域,一个事业的表述。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社会事业领域,它都有可能采取商业的模式或者采取非营利的模式,甚至是公益模式。近两年来,我们看到在教育领域大量的民办的教育机构选择非营利模式,甚至我们会看到这种方式,有可能还会延伸到卫生领域、文化领域等。那将会产生一个问题,社会创新者在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他首先要选择的是基础组织形式,是成立一个公司、还是成立一个社会服务机构或者基金会等。各种基础组织形式代表着它的定位、 它的法律性质是什么?
我们在分析该如何解决虐童、虐老时, 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媒体还是政府部门和大量专家,他们给的药方基本上都是加强监管——装摄像头、成立家委会、加强子女的探访等,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为其实社会事业、服务领域的问题在经济上我们称之为合约失灵。什么叫合约失灵呢?首先一件事情能通过市场规则解决,那它必须是合约是有效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市场上找到足够多的服务提供商,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选择跟谁去缔约合作。
第二个,我们去找缔约合作时,我们需要去考虑究竟选择哪一家?所以就需要我们有判断信息和依据,也就是信息对称,判断在众多的服务提供商那里,我找哪一家是最好?
第三,我们如何去判断订签合同之后其按照约定的情况履行了。它的条件依然还是足够的信息对称,使得我们能够获得这方面的信息并做出判断,进而启动违约追究责任的程序。根据一般情况,在市场中合约如果能够正常发挥作用,那我们会发现这三方面都是符合的。
但像科教文卫体等事业方面,尤其像幼儿托养所或者是失能老人的养老,存在许多问题。第一,我们在市场上,在社会上找不到足够多的选择,尤其是现在养老机构都特别难选择。
第二,即便有机构可供选择,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不知道该怎么判断哪家机构更好,因为我们缔结合同的和接受服务的人是两拨人。所以在社会事业服务领域里,我们会看到大量合约失灵问题,这就意味着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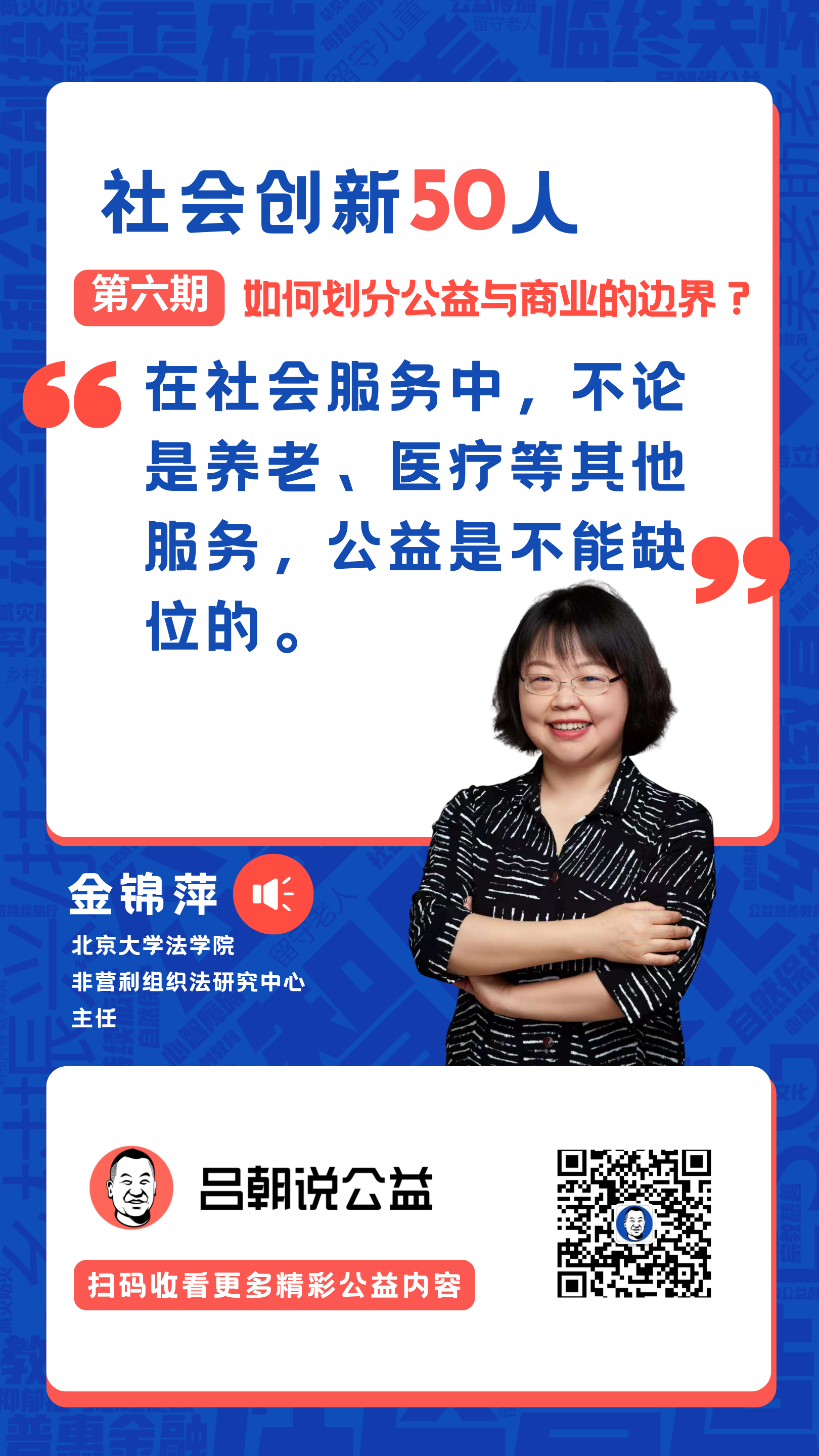
为什么要从合约失灵理论来讲,这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如果服务中真的有两类组织都在提供服务,一种是商业组织,另一种是非营利组织,我们在寻找服务机构的过程中,要怎么选择呢?
如果价格是一致的,我们就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非营利组织会胜出。为什么呢?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机构创办人不以盈利为目的,机构则没有克扣成本的必要,对一个非营利组织来说,利润并无太大意义。
然而,由商业机制进行运作,如果合约失灵,其肯定会压低成本、增加收入。其成本恰恰是压低在那些信息不够对称的地方。例如在护理师、师生比、软件等方面大量压缩,从而一定程度上导致服务质量的下降。
在一些社会服务领域,尤其是合约失灵的场合,资本过度逐利将会构成对整个行业的颠覆性的打击,因为这个行业本身的特性会导致它不断去压缩那些看不见的成本。
02 走进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真不能盈利吗?
吕朝:非营利并不是意味着没有收入。一个组织不管是营性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其都可以有收入。非营利实际上它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例如,我们假设一个非营利组织经营了一年盈余了一百万,但是它并不能将其盈余进行分红。但如果是企业,其股东就会将其盈余进行分红,股东为了赚得更多,就会要求经营机构不断地强化它的盈利能力。
金锦萍:民法典第87条,对非营利法人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定。
第一,举办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
第二,以公益或其他非营利为目的的组织中的成员不允许从组织中获得利润分配。所以组织本身是可以按照一定的运营机制去经营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大量民非也在经营并且有收入。其区别在于创始人设立组织有明确的目标,之所以没有选择公司,而选择民非是因为其并不希望通过组织进行资本的增值。
第三,即使作为创始人都不能从已经设立的组织的收益中进行分红。

在国家层面会大量倡导一些社会事业的服务提供商选择非营利模式,不允许资本过度的逐利化。比如,有段时间如果要上市的话,会要求把幼儿园、养老院中资产全部从上市资产里面剥离。
这是因为如果不把它剥离资本的实际控制,他们之间又存在产权关系,实际上就意味着一个非营利性的机构就出现在上市公司资产中。尽管它恪守了利益分配规则,但是其内部还会有大量的契约安排,还是可以有大量的利益输送。
如果我们现在选择社会事业领域创业,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服务提供商。比如,专门为养老院、幼儿园或者教育机构去提供一些基础服务、科技服务都没问题,但是属于在商业领域。但是我们一旦直接向社会提供社会服务,比如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等,可能在以后的政策变化时,政府会倾向于让我们选择非营利模式。
像教育、医疗,包括比如个人求助等,如果一旦我们在这些领域创业时用的是商业逻辑,我们考虑的是商业目标的实现,我们会发现我们与这个事业本身要达到的价值理性之间出现了极大的偏差,这个偏差最后将会给我们带来极大反噬。
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纯反商业论,我认为一个非营利组织要发展需要懂得商业机制。但是在根本的逻辑上,并不是任何领域的事业都可以采用商业模式,这也是我想提醒各位社会创新者的一点。
03 慧眼识"股东”——公益人股东VS公司股东
金锦萍: 公益人股东一词近期出现在市场体系中,但公益人股东属于概念的借用,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 。真正意义上的股东,享有两种权利。一种就是经营管理权,还有一种就是社会利益索取权。社会利益索取权又包括了分红权以及组织终止时的剩余财产的归属权,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
公益人股东实际上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公益捐赠或者志愿服务者,我们对这个组织是有贡献的。但这些贡献并不能换来股权,并不能因此在组织里占有财产权。那我们怎么还要提公益人股东呢?实际上当分红权、利益索取权被禁止时,还存在另一种权利——参与权。
这个权利实际上就是公益人股东得以立足的根本所在。比如我们现在倡导的参与式的捐赠和参与式的志愿服务,我们不仅仅是单纯的提供资金、经验和时间等,更重要是在这过程中,我们也参与组织本身的治理。
其实当我们用公益人股东这个词汇的时候,还是要跟真正意义上的股东要有所区分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保留组织经营管理权,但是并没有剩余利益索取权。
04 公益与商业的边界——走进水滴筹事件
吕朝: 在社会创新领域我们确实也看到一些所谓的“聪明人”,他在社会创新时,跨了不同的组织形式。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整体的论述 ,但是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水滴筹,这个例子特别典型的反映了许多问题。比如,不同的组织形式造成组织内部外部的组织行为特征 、机构内部不同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等。
金锦萍:如果将个人求助做成个独立板块,那在独立板块中须说明投入,例如人员投入等。因为人员本身是有成本的,如果是将其做成独立板块,就属于有一个独立于捐赠的第三方来进行支付,那无可厚非就变成纯粹的非营利组织了。
但是如果非营利组织本身又去为另外一个商业组织去引流,这个板块我们现在不鉴定它是否盈利,但这个板块要为另外一个商业板块去提供一种营销服务,并且这个服务本身是有商业价值的,两者之间相对于一种公益营销或者一个商业合作关系是可行的。
但是必须得把这个服务进行市场定价 ,并通过市场定价进行给付。从逻辑上来讲,通过这个例子我们能更好地理清这其中的关系。个人求助板块是有成本的,但是成本全部由机构支付,然后把所筹得的钱给求助人,这无可厚非,似乎通过其他的方法来实现了商业模式。
但是问题在于当平台有一天无以为继的时候,机构想要从求助款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平台的成本或者管理费用支出的时候,质疑也将蜂拥而至。
从本质上分析,个人求助业务、社会救助业务本身是有极强的公益性质或者社会属性。一旦用商业机制介入时,商业机制跟它之间的关系要界定清楚。想浑水摸鱼或者故意把关系给混淆,既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获得道德美誉,又想通过此模式给商业引流实现商业目标,最后会发现这两个目标之间会“打架”。
对水滴筹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先抛开道德层面评判的色彩,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个人求助的社会需求非常大。在目前公益所提供的救助还不够充分,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也不能全覆盖的时候,我们可能还需要此类个体求助。问题是当我们以平台的方式去给众多的个体提供个人求助服务时, 我们这个平台的定位是什么?只要平台不误导公众,就不会有法律上和道德上的风险。
05 社会创新的另一种方式——社会企业
吕朝:像之前我们谈到的非营利问题,尤其是利润不能分配的问题。有一些社会企业他们的利益是介于完全不分配和完全分配之间的,比如分配一半利润或三分之一的利润,这样是否可行呢?从法律工作者的角度您认为社会企业这条路是否能走得通?
金锦萍:当我们讲社会企业的时候,其特点就是在一个组织体里面融入了很多目标既有商业的目标、经济目标也有社会目标等,那它现在前景会怎样呢?
我记得大概四年前我在宁波参加了尤努斯举办的一个小型论坛论坛,我当时问了他一个问题,我问他你知不知道社会企业到中国之后有个非常核心的焦点责任就是它能不能分红。他非常无奈的看着我,很不解的说这怎么会成了一个关键问题呢?
“它到底分多少合适呢?99%合适,还是1%合适?”他在回答的时候我马上就get到他的点。你不管是分1%,还是99%,你是否将分红作为了你的首要目标?
我们会发现好多公司其实也不分红,我曾看到一个公司成立13年没有分过一次红,很奇怪的是那些投资者不仅没有撤,还一直坚持。我就很好奇问那些投资者,我说你们怎么这么有耐心啊,那简直是我见过的最有耐心的资本。他们回答说我们看好它的发展前景,他们知道这十多年的忍耐是有价值。那我们能称其为非营利组织吗?他们并未进行过分红。
所以当社会企业把分红作为主要问题讨论的时候 ,就已经背离了社会企业的目标,应不应该分红不应当成为社会企业讨论的问题。概括地说,当我们设立一个社会企业时,优先目标永远是社会目标。
近期我组织我的学生们一起将世界各国已经就社会企业立法的法律文本进行翻译,在梳理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在不同的国家对社会企业的界定的确不太一样。在不同的法律框架下,我们会发现它对基本问题的判断也有所差异。
比如英国我们都把它看成作是社会企业的鼻祖,在英国关于社会企业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资产锁定。其允许社会组织进行分红,那分红到哪里去了呢?分红到另外一个非营利组织,也就是社会企业的股东本身它有可能就是个慈善组织。所以在英国,大量的社会组织进行分红,这些利益并没有归私人所有,而是进入了慈善组织,那我们能说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分红吗?

因此,我们回归到对中国目前的社会企业或者选择社会企业进行创业的人士的一个提醒,就是不要滥用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本身是非常美的一个概念。不要以社会目标作为自己的幌子,也不要把它变成贬低非营利组织的一个理由,那些纯粹的恪守价值观的组织值得我们尊敬。并不是他们固步自封没有跟上潮流,社会组织体的多元化才是我们的正常现象。
社会目标优先是社会企业的核心因素,社会目标为体,经济目标为用。我们只有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才能使社会企业这样的组织体走得更远。刚开始处于小型阶段的时,我们也许会认为坚守目标很简单。
但是我们要知道万物瞬息万变,一旦企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当投资者追着我们跑的时候,那时我们还能坚持社会目标优先吗?如果我们在整个组织结构治理时,还能将组织创立之初的价值观体现在整个机构文化中,体现在各项制度规章之中,那肯定是个成功的社会企业家。
但如果我们相信自己人性的不完美经不起诱惑,那我们就不要在组织形式上给自己太自由的选择空间,这其实是对自我的保护。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