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7-14
2022-07-14
 221
221
何道峰: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历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第五组副组长、副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等。著有《乡村变革——当代中国农村政策问题探析》《就业·增长·现代化: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历史与未来研究》等,主编《中国社会扶贫研究丛书》等。
这是一个最激动人心的时代,也是一个最令人无奈的时代;这是一个凭感官就能感觉到眼前充满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认真沉思便能意识到人类面临难题无解与绝望的时代。
移动互联网中全球化信息的快速交流和摩尔定律主导的信息计算能力快速迭代这两种力量的相互推动,促进着信息加工与传输实用技术的快速进步;光传输和量子计算技术的最新突破,更为人工智能产业带来更为高远的想象。
另外,基因复制、阻断和测序技术的进步,正在开创生物微观技术领域的革命性进步。加上人际、组织间和国家间市场竞争制度的压力,人类技术创新行为被棘轮式地推入前所未有的快速轨道,人类没有时间和精力停下来思考。

因此一种不加深思的新技术赞美、期盼与崇拜,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时代潮流,主导着人类的舆论与群体行为,给人类带来期盼中的无奈和快速前进中的不安。人类焦虑、抑郁,群组性冲突、国家间冲突正在成为新时代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并未因技术发展而减少,反而因技术发展而迅速增加。
因此,深入思考并寻求新时代人类精神追求与物质追逐之间的平衡,不仅是理论与信心来源的解释学的需要,而且是人类减缓冲突、断裂,从而减少焦虑、增加福祉的需要。
人类文明史展示出人在历史中的两大优势,就是组织化与文字信息记录和传播;人在历史中最容易犯的两大错误就是骄傲和健忘。通过人类自身的组织化,人类放大了个体的有限能力;通过文字信息记录与传播,人类获得了群体性的学习与创新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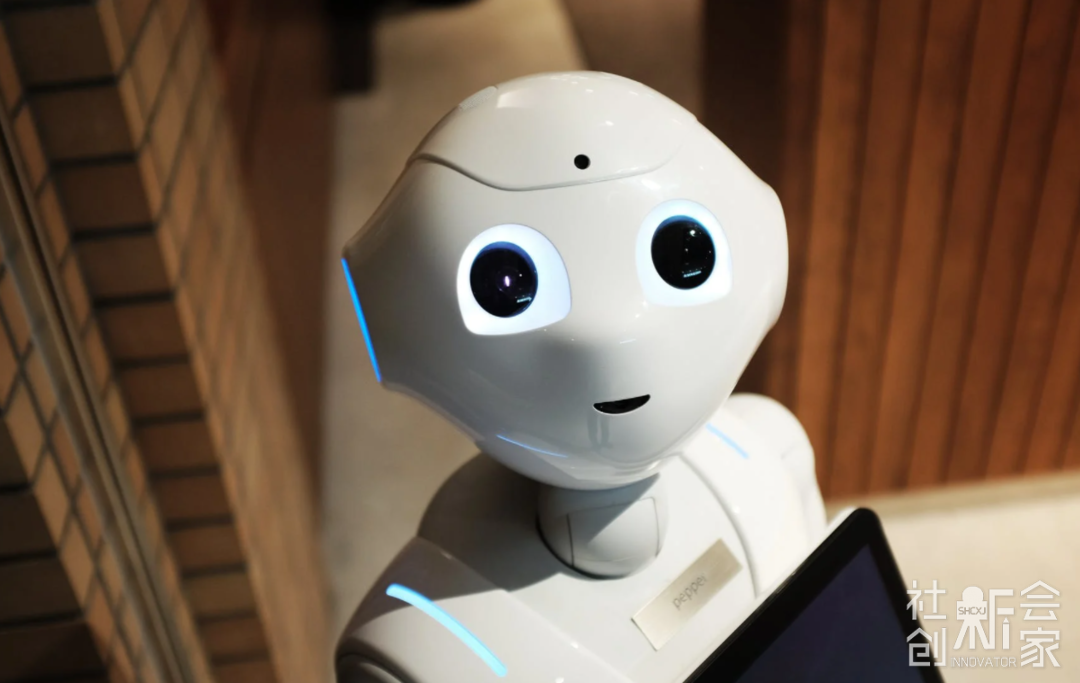
今天,我们回望整个人类文明史,它无非是这两大优势的群体性积累在征服自然过程中所形成“人的能够”的探索与扩张而已。始于自然哲学并通过人的经验累积的技术,与超验的想象力和逻辑推导能力相结合而形成的现代科学的跃升,及其科学技术的互动与合流,借助人类的组织化和信息传播与教育,让“人的能够”这种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可是人类在每一个历史进程中,总是为眼下所取得的“人的能够”之成就感到盲目自信与骄傲,总是堕入新技术、新工具崇拜的深崖,以为借助这种新技术、新工具就能够用组织化的方式去控制和奴役他人,而被奴役者也总迷醉于新技术、新工具,在奴役者所制造的潮流中盲目举杯,彻夜狂欢。
因为这种盲目自信与骄傲,人总是犯健忘症——不断犯那些人类历史中相同的错误,不断陷入奴役风潮、暴力冲突与自相残杀的绝境。直至问题走到极端,那些中流砥柱式人类智者的深思逻辑与醒世恒言,才会穿透人类骄傲健忘的寓于当下流行风潮中的重重迷雾,唤醒人因群体信仰而深藏的“人的应当”的神圣呼召,矫正那骄傲健忘的本性,小心翼翼地从历史记录的偏差和教训中学习,医治骄傲和健忘所带来的创伤,从而推动人类历史的健康前行。
可是,创伤的医治和向前发展又会在时间的流变中孕育出新工具崇拜的风潮,诱发人骄傲与健忘的本性。因此,组织化与信息化引领的技术创新便是“人的能够”借以扩张的工具;而人骄傲健忘的本性,就是人类如何处置自己的生命以获得神圣意义的“人的应当”问题。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无论多么复杂,都可以概括为人类关于“人的能够”与“人的应当”之间矛盾、冲突并相互推动的历史。

人类有文字记录的可考历史,可追溯至六七千年前苏美尔人的楔形象形文字,五六千年前埃及的象形文字,3000年前埃塞俄比亚的象形文字,以及华夏文明三四千年前的古汉语象形文字。而由字母组合的结构功能化文字发端则要晚一些,大约在3000年前,主要文字有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印度梵文等,阿拉伯文的出现则要晚很多,迄今回望,其只有大约1500年的历史。
但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化,特别是贸易和战争的影响,发轫古老的象形文字在运用上逐渐消失了,整全性的运用只剩下汉语语系,其他地区的文字则主要由字母组合的文字所替代。汉语语系在东方文明中守住了象形文字的历史根脉,并通过近现代的白话文运动,推倒了横亘在这两大语言系统之间难以逾越的墙体,使西语中以英语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化影响力迅速扩展到新的汉语结构中,从而使汉语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这些有文字记载的可靠历史中,文字的记录与传播犹如一个金字塔结构,从神学哲学思考的顶端往下,纵跨文学艺术启示,政治治理结构与战争,经济发展与贸易往来,社会自治与风俗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不一而足。而这种分层、分类的纵向结构之间,存在着文明内部的某种终极性深刻的逻辑一致性。

因此,如果从思想史的深层角度去观察和比较,我们就能够找到一种东西方文明比较的独特视角,窥见东西方文明演进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窥见被我们今天称颂为“现代化”文明的深层定义,以及不同文明系统内部思想与历史互动的神圣源头与权威源头之差别。我们由此找到一种辨析人类当下所面临问题的深层思想观和历史观,使问题的辨析找到一种可比性辨析的出发点,这便是本书想去探索的研究与分析路径。
如此大胆的想法对我而言,似乎过于狂妄和不自量力,因此我一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阅读相关文献并思考。奇妙的是,50岁生日之后,由于更年期的深度失眠,我能清晰感知到“死亡”的迫近感和距离感。自此开始,除了历史、哲学和神学思想者的著作之外,我无法阅读其他著作。经过10多年的阅读与思考的准备,我在4年前提前退休,于两年前开始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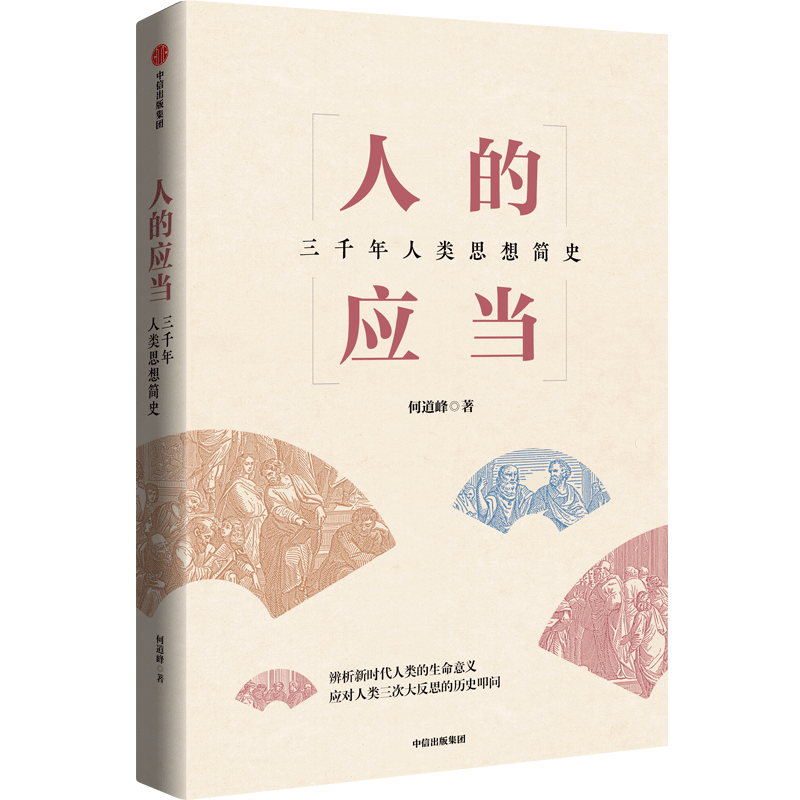
我尝试着将历史与思想史之间的逻辑联系建构起来,去勾勒现代化文明起源与孕育成形的历史脉络。我尝试着将人类在3500~1700年前形成的有文字记载的思考与思想,概括为人类第一次大反思。这与思想史界的第一轴心时代的思想不同。我认为人类第一次大反思应当包含古希伯来信仰思考,印度古老而深邃的吠檀多哲学与信仰思考。
当然,古希腊哲学思考、中国春秋战国哲学思考、佛陀哲学思考以及基督信仰引发的哲学思考,是这一时期人类思想的重要部分。这一次人类大反思是一次人类对所面临终极问题和绝对真理问题的发问与反思,讨论了自然哲学与人文哲学的种种命题,重点设问并回答了人从何处来并向何处去,以及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此生生命的“人的应当”与“人的能够”相矛盾的种种问题。其所涉及问题的深度与高度,迄今为止的人类从未超越过。

我尝试着将公元1200-1800年的核心思考,概括为人类经历的第二次大反思。这包括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再研究传播及其与基督信仰的整合,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佛陀信仰的东亚移植与南亚吸化,宋明理学与儒学儒教化,现代公益的发育与科学的跃升,人类理性自主与启蒙运动,现代化政治经济、社会市场化制度的构建与现代法治化建设,等等。
这次大反思以“人的应当成为公共精神”为假设,解放人的个体平等自由权,构建人际公平竞争及公正裁决体系,从而使人作为个体的平等自由权得到最为充分的保障,这种保障便是基于公平、公正的公共信仰基石所创建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市场竞争制度,以及基于公义的慈善公益精神与社会组织构建。
这种建构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的想象与创新能力,将人类群体性“人的能够”充分发挥、展示与极致挖掘,将人类群体性“人的应当”的悲悯与博爱推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一致,从而创造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文明。具有现代性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信仰基石,是在这一次大反思中形成的。它为现代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构建夯实了神圣而权威的根基,并创造了人类历史繁荣与发展的崭新高度。
可是,自人类第二次大反思末期开始的启蒙运动,将人类独一理性自主的“左倾”思潮在19世纪推到了另一极端化,特别是这种极端化给20世纪的社会大实验造成了一些国家骄傲和健忘的巨大历史创伤。而在另一些国家中,这种人类依靠科技独一理性自主的极端化浪潮,也推动着实用主义世俗化的浪潮无度演进。

科技越发达,新工具崇拜就越盛行。商业化对政治与社会的渗透越深,人就越在海量的碎片化信息中迷失方向。广告业越发达,人就越因被潮流席卷而失去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的能力。而这种状态下的人会骄傲和健忘。没有人能摆脱一生的压迫感和无度忙乱,心中只有货币计量的财富和用掌声或点击率计算的名声,恰如末路狂奔而不知航向。
因此,人类面临着第三次大反思的大事因缘和历史叩问,如何响应人类第三次大反思的历史呼召,深入思考与辨析生命的意义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人的应当”,已经成为人类最大的也是最紧迫的问题。因为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环境恶化、恐怖主义、核武威胁,每一项人类自以为傲的“人的能够”的群体性技术创新积累都可能终结人类。所以,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人类发出了忠告——人工智能或将终结人类文明,这的确意味深长且发人深省。
当然,本书的尝试也许是肤浅的或被认为离经叛道的,也许因写作风格是写意式而非经典考据式而受人诟病,也许很多论点未经严谨的文献引用和论证为人所不喜欢。但在今天这个社会科学分工细致和过度企图自然科学化即数学化的时代,为了学术的比较和赢得学术地位,人们习惯于在每片树叶乃至每片树叶的一条叶脉上精雕细琢,而忽视整棵树乃至整片森林之间的多维空间逻辑和历史逻辑。
也许这是一本闲书,但如果它能提醒人们去关注人类思想史和人类群体行为之间的互动对于人类文明的演进存在怎样深刻的逻辑联系,能启迪人们面对日益碎片化的信息如何保持整全性思考和精神信仰,我也就因此而心满意足了,正如一位老者将其毕生经验教训促成的思考转化成滋养来者思考的肥料般满足。
(本文系《人的应当:三千年人类思想简史》的序言)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