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30
2022-05-30
 265
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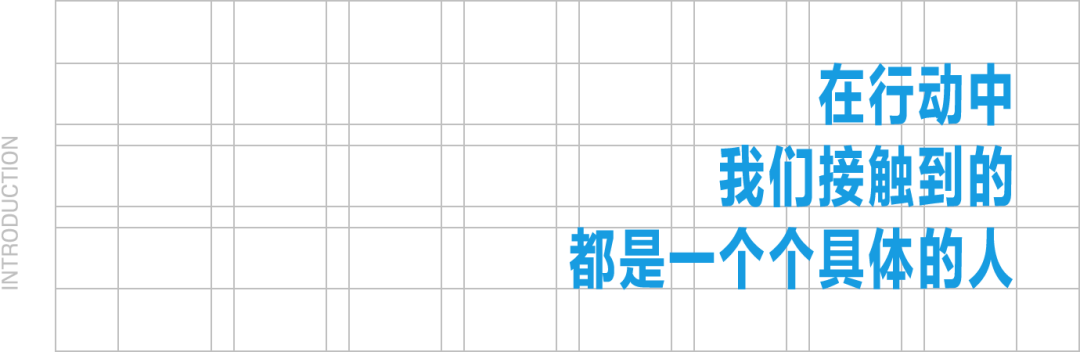
2022 年,上海。两个月的封控生活,让许多人知道了「自治」的概念,也让人开始更多地关注「社区」。社区,不仅是一个小区、楼盘的名字,它事关居民利益、街区生态,具体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今天,我们邀请有着 7 年「社区营造」经验的建筑师何嘉,分享他关于社区营造的经验。
以下是何嘉的自述:
4 月 10 日,我在(上海)新华街区街坊群里发起了「新华志愿车队」行动。这应该是我已知的上海唯一一个由民间发起的,覆盖整个街区生活圈,并实现街道保障政策和各社区志愿力量「真正携手」的志愿者车队。
当时,街道在封控期间收到大量个体家庭的就医需求:定期进行化疗、血透、孕检、精神治疗的,定期配药的,以及紧急就医的。根据这些需求,我设计了一套流程,在街坊群里发起招募,陆陆续续得到了 120 多位志愿者司机的响应,我也是其中一员。生死就在我们的身边,在行动中,我们接触到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车队在一个多月,帮助了近 200 人。
01 做志愿者对我而言,也是一种治愈
做志愿者对我而言,也是一种治愈,虽然这段时日,我和所有上海居民一样,情况并不好。比如,我也遇到过家庭内部矛盾:我们一家三代人时时刻刻相处,会因养育孩子方式的不同爆发代际矛盾;还遇到过楼上的水管泄露(可能是使用了消毒片)只能自己动手修补 …… 经常,一地鸡毛。状态最糟糕时,会被无力感笼罩,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发起车队的工作之后,反而感到了平和:因为看到大家都在一起努力地行动。行动是最好的一种疗愈方式。
「大鱼营造」(以下简称「大鱼」)呢,是一个关注社区更新、社区营造的公益机构。
很多人在这次封闭前,从来没和居委会打过交道,甚至连街道和居委会都分不清。因为从事社区营造,我们此前的工作与社区多方相关,比如参与式设计社区的公共空间,支持街坊共创社区刊物、社区节日,需要和街道、居委会打交道,(所以我们)比较了解他们的工作机制、方式。相对于遇到矛盾,「指责」乃至「对立」,我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尽量地去理解发生了什么,然后试着和街坊们一起,与政府的、民间的、正式的、临时的 …… 各个相关方一起,促成一个对话机制,让大家联手行动。越是在这样的时期,行动越是要联合。民间协作、民间互助的用武之地,就是让大量的「孤岛人群」能够通过邻里(间)守望相助的方式,渡过难关。
02 为什么建筑设计离真实的人这么远
到底谁在为多数人设计?
很多人对我性格的评价是温和、稳定。但是成长过程中我是一路叛逆才选择了现在从事「社区营造」这份事业。在我做职业建筑师的前几年,整个建筑行业都在为中国 2000 年至 2010 年之间取得的城市建设成果而亢奋,而我却时常困惑:为什么建筑设计离真实的人这么远,到底谁在为多数人做设计?
我的职业起步于国企的大型设计院,6 年工作经历中,参与的项目造价都是几亿、几十亿元的城市标志性建筑,也因此作为专业负责人获得过官方认可的行业最高奖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优秀(公共)建筑设计」一等奖。但我意识到这与生活本身相去甚远,建筑设计这份职业也失去了「这是我此生最想做的」的使命感。
03 我们做设计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身为设计师的“自我”
而是为了更多人的设计
2016 年从设计院离职,我一直在摸索把「参与式设计」和社区营造相结合,并经常以志愿者的身份试图帮助社区做设计。2018 年,因为大鱼的合伙人尤扬发起的「城事设计节」,我们有机会正式开始从身边行动。我们几位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将「大鱼」这个兴趣社群正式注册为了一个社会组织,并推动了新华路 7 个社区点位的改造和一场城市论坛活动。当时得到的反馈很热烈,于是我们就一直顺势向前探索。「大鱼」的成员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做设计不是为满足自己身为设计师的「自我」,而是为了更多人的设计。
城市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公共设施,只有更多人去参与决定,才能够让设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如果城市建设、更新的目的是想做一个「景观式」的存在,那使用社区营造的方法,会被认为「效率太慢了」。我很难想象那些在展示时只有「改造前」和「改造后」照片做对比,而不在乎中间过程的街区,在面对巨大公共事件的不确定时能否展现出韧性。
04 “社区营造”是对社区进行一种“关系设计”
「社区营造」是对社区进行一种「关系设计」。这些年的社区营造实践中,「大鱼」建立了一套方法论。往往,进入社区后的第一步是「认识街区」:找到当地具有代表性的、不同领域的人,再通过走街、研讨会等活动让大家一起重新定义附近、定义当下 —— 知道社区现在是什么情况,有哪些问题、住在这里的人共同的愿景是什么。从认识社区到建立关系、凝聚共识、聚焦需求、共同提案、落地工程或者开展行动,再到持续激发在地的参与者共同运营等,各个环节都让利益相关方能够获取信息,有参与的机会,形成持续参与的机制 —— 这就是「参与式」的过程。

这几年上海出台了针对「老破小」的改造政策,按照每平(方)米 500(元)的标准进行拨款。比如,这个小区有 3000 户居民,总体的改造费用可能有 9000 万左右。很多工程是标准化的「规定动作」:比如屋顶翻修、墙面涂刷、管道改造等 —— 很少能深入到改造会给居民带来怎样的「公共性」,居民的获得感也很低。当然,「定制化部分」就需要面对更多公共协商,比如把小区的零碎绿地「化零为整」成一个公共广场,居民都很关注,也会导致引发巨大的讨论或者争议。如果能够通过好的组织和好的过程,让大家一起做成这样一件事,那社区就有可能迎来更好的关系。
05 任何时期,设计都不该放弃对“美”的追求
理想的社区设计,可以让人感受美、温情、活着。海德格尔谈「诗意地栖居」的时候说,我相信好的社区,应该是去保护更多人的「本真」(「本真」是海德格尔哲学里的概念,亦称「原真性」),让人们感受到存在、并主动表达。每个居民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愿景(vision),然后我们设计师去找其中的共同点,将其转译成设计。我想,任何时期,设计都不该放弃对「美」的追求。这种美,不光是形式感,更多的是关系。城市社区应该提供更多美的体验。
2021 年上海城事空间艺术季期间,新华街区发起了一平米行动,每个居民都可以申请在街区内利用好一平米的空间艺术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认识社区到为社区提案、再到亲手创造,居民在社区的主体性可以更强。
今年上海涌现出非常多的民间互助形式。有人提出讨论:今年有没有可能成为「上海社区自治」元年?的确,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很多人都在这两个月的封控生活中知道了「自治」的概念。但是具体什么是自治、怎么自治、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仍然有很多问题存在。在信息不够透明、信任缺失的情况下,作为核心主体的社区居民很容易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公地悲剧」「电车问题」等博弈论的处境。在这段时间,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人用自己的方式呼喊,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这是好事;不过与此同时,如果谁的声音更大谁就优先被满足,那反而可能导致更弱势群体的利益进一步受损。
所以,我认为社区自治可能在今年朝两个方向发展,其中,糟糕的方向是 —— 很多人还没理解「自治」是什么,就丧失信心了。

4 月 10 日,何嘉在新华街区街坊群里发起「新华志愿车队」行动,并也担任了志愿者
我们国家,特别是在上海,已经推行了七八年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国家提出了「共建、共治、共享」「人民城市人民建」这些理念。2019 至 2021 年,上海也大力推行「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的概念,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参与、协商、对话。但很可惜,在疫情的冲击下,我们的城市进入了一种应激的「战时」生活状态,治理并没有完全发挥出作用,良性的社会互动没有遍地开花,甚至受到了损害。
社区营造的愿景是让社会上的每个主体都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主体性。如果一个社区培育了互信互惠的土壤,那么在危机时刻,就能够快速组织互助行动。疫情之下,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志愿者队伍,有官方的、半官方的和完全草根的团队。大家的思维习惯或者经验相差甚远,政府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相信民间的草根组织,而民间对强硬的管控也带有抵触的情绪,并转嫁到针对行政、决策体系的不满上。我感受到每个社区都需要有一个对话、协作的机制。我将「大鱼」努力扮演的角色形容为「握手平台」,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一方面希望可以试着帮人们去理解目前自上而下发布的政策;另一方面,也希望可以收集到更多(由)民间的行动、民间的声音汇聚而成的共性需求,用服务设计能力和组织能力,帮助更多人的找到积极行动的途径。
06 大家的思维习惯或者经验相差甚远
政府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相信民间的草根组织
而民间对强硬的管控也带有抵触的情绪
虽然「大鱼」所做的事情在这几年里得到很多关注,但是我也必须承认,实际效果非常有限。我今年 39 岁了,依然认为保持反思和批判性很重要,也会试着理解、包容更多。我们每个人都有局限性,同样,社会上的各种主体,不管是行政还是市场,乃至公益部门,也各有局限性。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政府、企业、公益等多元主体都有各自的位置、(履行)各自的责任,能够在一个好的互信的土壤中实现互惠互利。作为一个坚定的「共益主义者」,我相信美好生活是由多元主体共同定义的。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