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11
2022-04-11
 714
714欢迎你来到益盒对话笔记。我们在这里呈现原汁原味的研究对话,让你身临其境,旁听我们与业内专家的对话,看到公益的内情,成为更理性的公益人。
本期对话我们邀请到了李一诺。她几乎不需要什么介绍:一诺一土教育的创始人、“奴隶社会”公众号的主理人。她身上的标签很多——保送考进清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盖茨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教育创新领域的开拓者。在我们以为她已经安顿下来的时候,她总会不断跳出“舒适圈”,继续追问价值、创造改变。
在对话的开始,一诺和我们分享了早年成长和求学的经历里那些“高光时刻”带给她的影响。因为在学界、业界和公益界都有过深度的工作经历,在谈及公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公益行业与商业世界的关系等颇具争议的问题时,我们也得到了来自一诺的独到见解。最后,回顾创建一土学校的初衷,一诺认为,教育不应拘泥于所谓的“高大上”,要回归本质,关注更底层的需求。
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听听她的故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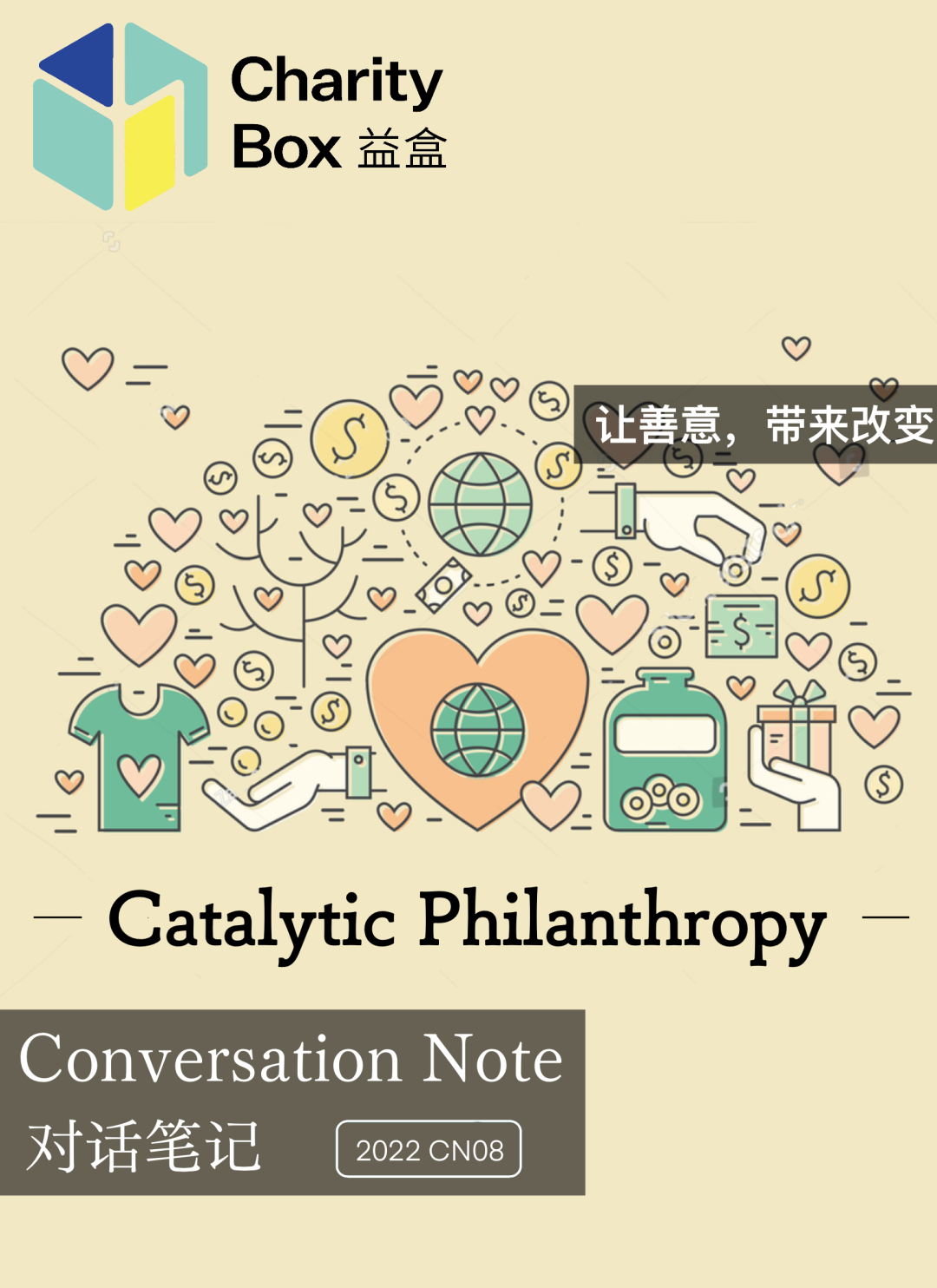
TIME
时间
2022年1月22日
METHOD
方式
线上采访
INTERVIEWEE
受访者
李一诺,一土教育创始人
INTERVIEWER
采访者
何流,公益盒子CEO
李治霖,公益盒子研究总监
农雨笛,公益盒子COO
范思怡,公益盒子研究志愿者
TOPIC
主题
中国公益 有效性 商业与公益
三十岁之前的经历
Q:大家对你的认识,一般是从清华“学霸”和麦肯锡开始的。在那之前发生了什么?我们想听听你更早的成长经历。
A: 我是比较典型的“70后”,经历了计划经济阶段的结束。我小时候住在父母单位的房子里,周末会用粮票、酱油票去买食物。当时的教育是比较平常的:就近上小学、划片区上初中,都是普通的学校,没有现在孩子所面临的教育压力,只是自己的学习成绩比较好。初中毕业时,我因为成绩排在第一名,被保送到山东省实验中学,是当时济南市最好的高中之一,另一所是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现在回想高中生活,使我受益良多的是很多年轻老师。他们是改革开放后上大学比较早的一批年轻人,普遍都只有二十三四岁,思想开放,很有自己的想法。
我的经历代表了典型中型城市普通家庭孩子的经历。我小学毕业时父母离异,对我管教很少,但从小我就知道学习是自己的事情。在我的印象里,中学时的排名系统是相对公平的体系,不存在“跑关系”之类的情况,老师只是通知我妈妈我被保送了。不过后来,老师曾经询问我妈妈是否让我放弃保送名额,因为即使不保送我也能考上。但母亲坚决要求保送,老师也就没有再坚持。整个过程比较透明和公平。我们高中人很多,有14个班级,将近1000人。每次考试都会张榜公布前面的排名,它的好处是透明,但是现在想想也是比较“残忍”的制度。高中毕业我的总成绩是年级第一名,获得了保送清华的机会。
我想我是比较典型的“好学生”,当过各种学生干部,也参加很多竞赛、“帮扶”其他“差生”等。我当时最好的朋友之一,就是我的“差生”同桌,我们经常一起上课不听讲,他现在在澳大利亚开旅游公司,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系。现在回想,当时学校的评价指标非常单一,就是考试分数。但我那位最好的朋友就是典型的分数不高却很优秀且富有创造力的人,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从幼儿园开始就通过把玩具租给别人的方式赚钱,之后还盘了一个小店,以会员制的形式租借音乐磁带给别人,1993年的时候就赚了不少钱,买了一个摩托罗拉的BP机。某种意义上,他当时就在尝试类似于Netflix的商业模式了。他虽然大学考得不好,但却做了不少生意,人也见多识广。当时我们高考结束后,他跟我约定,虽然不能考去清华,但他可以开着奔驰来清华看我,结果他真的开奔驰来清华看我了,虽然那辆车是借的,哈哈。一个如此有创造性、有意思的人,却被所谓“正统”的体系评价为不成功,在我看来很可惜。和他做同桌,虽然只有一年不到,是我高中记忆中的一个亮点。
Q:去在清华的时候,你想以后做什么?
A: 当时想的并不多。选专业的过程其实很糊涂。清华当时有两个系不招保送生:生物和经管,前者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的未来产业,后者则似乎是可以赚钱。我在高中参加过生物竞赛,所以招生办看到简历后,告知我可以考虑读生物系。清华的生物系一年只招一个班,30人左右,在山东每年只招两个人。当时知道这个机会难得,觉得自己上了不错的学校、读了不错的专业,却没想过自己要做什么。
上大学后,前两年都是基础课程,高年级才会学到生物专业课程,但我们很快发现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上课“魂不守舍”,每天翻着很厚的新东方“红宝书”。一开始我不知道她们在做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在准备出国读书。初入大学,我和好友颜宁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在高年级时学好生物专业知识,所以决定提前考完托福和GRE考试。于是我们开始去北大化学楼上新东方的英语课。说个好玩的插曲,当时是我爸骑车去帮我们排队报名,但他的拼音不是很好,把颜宁的英文名弄错了,写成了“NIENG”。这是典型的拼音拼读错误。不过直到现在,颜宁的英文名依旧没有改,论文发表的署名也是。

颜宁和李一诺
图片来源自奴隶社会公众号
我们在大学都不是成绩最好的,是“中不溜”,最后毕业的时候, 我记得颜宁在我们班排名第四,我排名第七。大三之前,我们就考完了托福和GRE,其实挺悬的,因为有效期只有两年,而且考试费用和上课费用很贵。考完后我们就一起上专业课,之后申请奖学金一起出国。
和那时候很多读博士的学生一样,我在UCLA生物系的学习不仅因为有奖学金而免学费,还有生活费。我母亲当时挣一个月2000元的工资,我一年2万美金、合16万人民币的奖学金。那时候感觉是一笔巨款,似乎特别有钱。
颜宁去了施一公的实验室。他比我们大10岁,当时刚做完博士后、成为助理教授。在清华时,他就回来做过演讲,谈起他的两份博士后工作以及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经历,非常激励人心。
Q:你是如何进入麦肯锡的呢?
A:我很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他从一开始,就告诉我读博只有三条路径:“发论文”,“发论文”,还是“发论文”。我博士一共读了4年,第一年是实验室轮岗,修读基础课之余,每个学期需要在实验室做三个月。博士结束时,我一共发了8篇论文,有一篇作为第一作者登上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的封面,还有一篇第一作者的论文同样发表在PNAS上,此外还有两篇第一作者的论文以及四篇第二作者的论文发表在比较好的期刊上,对于博士生来说,这算比较高产的。我那时的职业理想是读完博士后去做教授。
但在上完一门课程后我的梦被打碎了。美国的职业教育设置比较完善,我们学校有一位教授,用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的专项基金设立了一门大学职业教育课程,目的是让研究生和博士生全面了解大学教职工作,包括如何通过检索各类研究机构相关信息找工作,找到工作后如何申请补助资金、怎么招博士后、怎么管理研究生和博士生团队等。我曾经跟这个老师一起上过写作课程,也非常喜欢她,所以听说她开设新课时就报名了。我很感激这堂课,虽然我怀着很大的热情去了解教职工作的情况,最后发现,这份工作和我想要的不一样。但这也是这样课程的价值所在。
这门课程曾邀请了助理教授作为嘉宾分享感受。听完后我的感受就是他们的生活看上去很糟糕,跟我想象中的“高光时刻”非常不同。这堂课并没有尝试掩盖不好之处,而是真实地呈现了大学教职工作中的疲惫和痛苦。这样坦诚的分享在美国大学中很常见,比如新生入学时,就有一个博士生分享说:他已经读了9年PhD了,很感谢学校一直支持他,我一听吓坏了,觉得太长了30多岁了还在读书。当时UCLA的系主任还补充,不是所有人都这么久,博士生的平均毕业时间是6.5年,但在我看来也很久。所以我在博士阶段非常拼。我觉得这是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有趣的一面:不会尝试去美化这些不够美好的部分,而是比较透明地沟通预期。向未进入这个领域的学生展示真实的工作状态,而不是一味强调光鲜亮丽的表象,这是职业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
虽然我知道自己不想做教职,但具体想做什么却没有更好的想法。摆脱这一状态的契机,还要感谢我先生华章。他当时在加州理工大学,麦肯锡等大公司都会去做招聘。华章跟我说,你应该去尝试麦肯锡。那年正好赶上麦肯锡扩招卫生健康方面的人才,所以很罕见地来UCLA做校内招聘。之所以说“罕见”,是因为麦肯锡给人的第一印象非常“精英”,网站上展示的履历都是“鑲着金边”的,一个个不是毕业于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名校,就是拿过奥林匹克金牌的;当然进去后发现,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后来当我离开麦肯锡,也有人拿我的履历来宣讲,我才发现自己也变成了这些“金光闪闪”履历的一员。
为了应聘麦肯锡,我参加了UCLA安德森商学院的咨询社团。这个社团跟我当时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实验室的生活每天都是黑白颠倒的,有时候中午才醒,然后去实验室呆到深夜,穿着也很随意。在社团,我会觉得自己与他人格格不入,别人都西装革履,但之前西装对我而言是一个完全没必要的物件。
在盖茨基金会的工作
Q:盖茨基金会如何制定在中国的战略?
A:我要先声明一下,我已经离开盖茨基金会了,所以这些都是我在的时候的情况。现在很可能有变化。
制定战略就是回答3个问题: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每年基金会会有一个系统的战略研究会议,确定目标,列举支持目标的资金,分析从哪些方面推进,同时综合考虑它们之前的表现,再作出相应的调整。
在中国的部分战略制定是从基金会全球大目标分解而来的。盖茨基金会希望促进全球发展,加强全球健康投入。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研究确定抓手和策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确定所需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协同中国的资源与全球卫生健康发展的目标。
药物监管是基金会在中国的另一个工作重点。监管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角色不能高效运转,新药上市、定价和市场可及性都会受到限制。因此,如何支持药监体系的改革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重点支持中国药监局开展改革,让中国的药品审评系统尽可能地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审评系统接轨,让审评过程和卷宗得到国际标准的认可,以便中国的医药产品更好地服务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
Q:盖茨基金会每年花巨资支持各种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在公益慈善中有什么意义?
A:当我们想推进某种改变,就好像一架机器的齿轮,都需要转起来才行。
在盖茨基金会,这被称为“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框架,其主要作用是定义改变如何发生。这个框架的逻辑非常直接;如果推动改变需要证据,就去研究证据;有了证据后,需要媒体报道和传播的话,就去推动传播;如果发现需要做公众教育,基金会就支持宣传活动;如果需要支持政策决策,就通过智库做相关研究,为决策提供参考;如果这些都有了,还需要召集人员开会,那就组织开会、做决议。
Q:盖茨基金会十分关注成本效益,为什么?
A:慈善中的成本效益是很重要的。资源是有限的,要解决大规模人口所面临的问题,需要寻找影响力高的路径。此外,慈善和商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明确的方法论。商业创业会有各种商学院和项目教你怎么做;但慈善方面很少有这样的形式,尤其是国内的慈善行业,很少会衡量慈善的效果。
慈善不像创业有很多可衡量的指标,比如股东回报、股价等。慈善的回报更综合,不是纯粹的科学和数据分析能够完全衡量的,而是多维度的,认知的提升、社会共识的形成等都包含在这个维度里。
Q:您如何评价自己在盖茨基金会的工作?
A:这段经历显著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我很感激。
之前在麦肯锡的工作其实我也很感激,虽然很辛苦,但工作回报非常高,这个回报不仅是经济回报,也是学习处理问题的方法,它让我能从更多层面去理解这个世界,包括各行各业的情况、企业的问题、人的问题等。
但基金会的语境让我理解了麦肯锡的工作方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商业市场的规律无法运行的地方,麦肯锡式方法是受局限的。
从项目角度,基金会做的许多工作的过程和影响都是长线的,现阶段的成败都是暂时的,不一定代表全局。在规模比较大的跨国组织工作,很重要的工作是做倡导。为业务寻求认可、理解以及争取更多的资源。虽然内部的运营工作和资源难以从外部观察到,但却是外部工作的基础。
Q:您为什么离开盖茨基金会?
A:加入的时候就希望差不多做五年,2020年我在基金会已经工作6年,可以开始下一段探索了。
对中国公益的思考
Q:第三次分配的语境下,公益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定位是什么?
A:我觉得公益在中国很难,如果有定位,那就是:在细节里寻找可以努力的方向。
Q:公益需要从商业中借鉴什么、警惕什么吗?
A:我认为所谓的“学”,应该更多是向商业学市场。商业市场成功的原因是开放、自由、竞争。慈善世界中只有出现了有效的竞争,才会产生更好的方法论。比如公益盒子选择去衡量捐款的有效性,这样的衡量方式只有在自由的竞争环境中才有其必要性;在封闭、不透明、不自由的竞争环境中,公益组织可以自己通过媒体端阐述其有效性,而不需要第三方评估体系。
人才和思维方式也可以从商业中借鉴经验。比如企业做产品时,有一个漏斗式的获客模式,可以统计:多少人看了广告;看后多少人产生购买动机;有动机的人是否有渠道;渠道的价格是多少;客户群体可否细分;不同客户群的购买体验如何、售后怎么样;是否可带来更多用户;是否可能重复购买等等。这个思维模式和公益行业非常像,也是公益行业可以学的。同时,商业世界里,有很多公司会做市场教育。产品刚推出时没有人要,但可以通过教育逐渐培养市场。最显著的例子就是iPhone,它就是培育了一个从前没有的市场。这种思维方法、逻辑、推理和问题解决方法没有行业之分,同样地,领导力和组织形式也可以在不同行业间融会贯通。
衡量结果很难从商业里学习。社会问题的因果链条非常复杂,而且投入产出的结果不直观。比如,建立智库和开研讨会方面的投入,很难在短期内看到结果,但假如第五年才看到结果,难道就可以说前四年的投入是无意义的吗?不能。所以我觉得很难在慈善中用统计表简单衡量结果。
Q:一土学校希望培养“内心充盈的乐天行动者、理性创新的高效学习者”。这背后的思考是什么?一土学校看重什么教育指标?
A:我们希望做一个儿童友好的社区学校。大家平常给教育赋予了太多教育之外的虚荣心需求,追求一些很虚妄的东西。现今社会,教育的问题导致成人内心焦躁,会在不知不觉中也向孩子传递这样的焦躁。
所以我创办一土学校,说到底,是希望创建一个儿童友好的社区学校。社区学校简单来说就是社区的中心,因为教育是一个社区行为,它是家长和教师共同建立的社区。
在一土,我们有一套评估指标“螺旋图”,从“认识自我、追求美好、沟通协作、学会学习、敢想敢做”五个方面进行讨论。这个评估指标在不同年龄有不同指数,衡量5岁孩子和10岁孩子的指数肯定不一样。同时,5个一级指标下还有20个二级指标,贯穿孩子的成长全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学会学习”这个指标虽然和学习有关,但更多的关注的是如何去学习,引导孩子们去学习“学习的习惯”。
如果一定要把教育说成“产品”,教育与其他产品的区别在于它带来的是一个人的整体体验,很难简单地进行指标化。比如如何设计学生主导的家长会,这个设计本身,就是评估的过程,也是教育的过程。
Q:一土学校现在发展的情况如何?
A: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每天把事情做对、做好。一土希望能覆盖更全面的教学阶段,现在有幼儿园也有中学部。现在也在招生,可以看一土教育公众号。
Q:一土是一次相对精英化的尝试吗?在社会层面的定位是什么样的呢?
A:如果将“精英”定义为,未来可以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群体、心怀天下的人,那么大方地说,精英化没有什么不好的。但在中国有很多语言陷阱,很多时候即使精英的定义是不明确的,大家给你扣上这个帽子,就可以否定你的很多努力。
在任何国家,大众教育一定是公立教育,即便是美国,私立学校也只有4%。但不能因为学校小众,就认为它是给有钱人办的。在一个社会体系里,改变总是从非常小的前沿开始的。美国有很多私立学校,他们有更多创新的空间,这些变化会慢慢倒推社会整体的变化。

图源:搜狐教育智见
看到自己的全貌
Q: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你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
A: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在当下做最好的选择。每个人在每个阶段的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但是最重要的是对当下的环境作出最好的反应。
我们的教育里比较缺失的一点是只培养大家如何工作,却没有培养大家如何生活。我认为,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会更全面地认识自己的生活,看你的社交圈子里有谁、看你的家庭有谁、谁需要你的关照。我们需要把生活、工作、家庭责任视为一个整体,很多事情自然有答案。

被访者介绍
李一诺
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子生物学博士,现为一土教育、“奴隶社会”联合创始人,她从2011年起任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2015年至2020年担任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负责领导盖茨基金会中国团队,与中国的公共、私营及非营利部门合作,致力于解决中国及全球的健康、发展与政策领域的重要问题。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