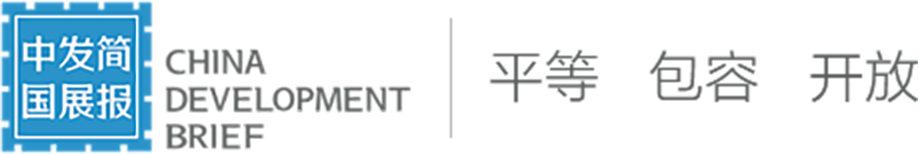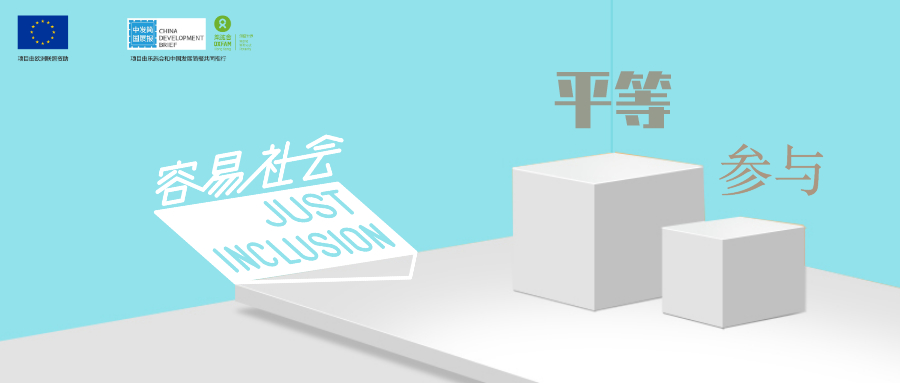2025-10-10
2025-10-10
 40
40口述:花姨(化名)/辽宁籍在京务工者
整理: 潘愉/协作者社会工作者
编者按:
花姨,70岁,辽宁大石桥人,1999年来到北京,经历两段婚姻,现独自抚养患抑郁症的女儿和有癫痫病史的外孙小金。作为隔代抚养者,她每月依靠3030元退休金支撑一家三口的生活,在病痛、住房压力与照料责任中艰难前行。这个七旬老人的故事,藏着无数隔代抚养家庭的缩影——用衰老的肩膀,扛起下一代的人生。
我是花姨,1955年生在辽宁大石桥,营口县那会儿还属大石桥管。家里兄妹五个,我排老二。父亲是八级钳工。在我18岁那年,父亲得胰腺癌走了,他一走,家里经济各方面都不行了。母亲身体也不好,肝硬化。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受不住打击,没几年也跟着去了。那时候我哥哥刚参加工作,一个月30块钱工资要养六口人,日子过得像被水泡透的棉袄,沉得喘不过气。
在父亲活着的时候,家里氛围特别快乐。我父亲特别喜欢小孩,我的同学会经常来我家里来玩。那段日子真的是无忧无虑,也让我感觉到家特别温暖,但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之后,我就觉得没有家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生活没有乐趣,后来慢慢才熬了过来。
从售票员到北漂:被命运推着走的半生
1975年,我高中还没有毕业,正赶上文革后期,学工学农的日子刚过,父亲单位照顾我们家庭的情况,让我接了他的班。我妈说:“如果我去高考,家里怎么办?”考虑到家里生活太困难了,我就没有参加高考,直接参加工作了。1977年,我成了汽车运输公司的售票员,在厂矿和市区间跑通勤,每天收票、报站,车厢里的煤烟味混着乘客的汗味,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那时候的婚姻,像搭伙过日子的工棚。25岁,我和高中同学结婚了,原以为知根知底能安稳,没想到碰上个喝大酒撒酒疯的。他在外边花天酒地,工资一分不给我。我每月挣得30块钱既要养家,还得给他还赌债。有次他喝醉了,在车厢里当着满车乘客扇我耳光,青肿的脸让我半个月不敢抬头见人。我想要离婚,他就又哭又闹,没到三天又恢复原样,就是“滚刀肉”。但没想到那个年代离婚比登天还难,需要单位街道都给开证明,但单位、街道都不给开,我被逼得精神崩溃,住进疗养院两年。后来,恢复身心之后,我就到法院起诉分居,直到分居满半年,法院才判离。
那时候女儿刚5、6岁,判给了前夫,我就一个人工作生活。后来,1999年单位效益不行,我办了买断工龄,先去大连可口可乐厂流水线上干活,也在中医诊所打过零工,也做过做饭钟点工等等……后来我妹妹在北京站稳脚跟,喊我过来帮忙带孩子。她是口腔医院的专家,忙得脚不沾地,我在她家一做就是好几年,接送孩子、做饭、打扫,成了家里的“保姆”。

社会工作者跟小金的姥姥在访谈
暖过也冷过的日子
第一段婚姻的结束虽然暂时让自己脱离了困局,但女儿跟着前夫却一直在受罪。前夫整天不务正业出去喝大酒,也不管她,心情一不好就回家打她。他去外出开货车的时候,就把女儿一个人锁家里,让她在家里吃凉饭,后来女儿憋出了抑郁症。女儿在学校混了七八年,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在家里待着了。后来,2003年左右,前夫亲戚给女儿介绍了表弟,我寻思女儿这个状况,只要找一个老实巴交、不欺负她的就可以了。但结婚了之后,她的丈夫把钱都交给了他妈,老太太整体东走西颠打麻将,女儿怀孕之后在家吃喝没人照顾,也跟不上营养。她有时候给我打电话,说自己什么都吃不着,我就给她打点钱支持她……后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就离婚了。现在状态也不是很好,有时候会自言自语,患有糖尿病,要每天打胰岛素,还有胆囊结石、鼻炎等一身病……
我自己在2010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北京的老伴,他比我大10岁,是水泥公司的站长。在和他结婚之后,没多久我就把女儿和外孙小金带过来北京一起照顾了。过去的这13年是我这辈子最安稳的日子,虽然每天就是柴米油盐——他买菜做饭,我收拾家,外孙小金来北京后,他也特别宠着小外孙。

儿童小金在写作业
但小金这孩子也是命苦。一岁多在奶奶家,从高床上摔下来磕了头,开始抽羊角风,一晚上能抽10次,脸憋得发黑。接过来北京之后,我和老伴带着他到北京很多家医院看病,现在吃药基本控制住了,每月药钱1050元,一分不能少。后面才知道是癫痫,小金的大脑损伤比较严重,影响了他的智力,三年级了还数不清5以上的数,语文课本上的字认不全,说话也磕磕巴巴。在学校被同学推搡,他只会拿铅笔扎人,说不出来。有次把小女孩推倒在草坪上,人家家长不依不饶,我带着去朝阳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蹦跳自如,没事”,可我还是赔了500块钱。
除了我女儿和外孙小金的情况,老伴的儿子从一开始就反对我们在一起,为了财产闹到打官司,老头被气得血压飙到200。2023年11月,老头突然脑梗昏迷,抢救了一个礼拜才醒,之后小脑萎缩得厉害,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很多时候他吃完饭就忘,总说我们饿着他。没办法,我会在饭桌上放个本子,他吃完就画个勾,就这样糊涂着过了半年,去年还是走了。
关于明天:不敢想的心愿
我自己身体也不太好,去年3月在医院做了手术,嗓子里的囊肿已经癌变,切下来的组织装了小半盘。大夫说再晚点就麻烦了,可我哪有时间顾自己?之前老头住院,小金疫情期间阳了发烧,我白天跑医院,晚上给孩子物理降温,熬得眼睛都糊了。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心口窝堵得慌,恶心反酸。胃里还有息肉,三年没敢复查,就怕查出问题来,这一大一小没人管。小金的癫痫药、女儿的胰岛素、我的降压药,堆在窗台像座小山,每个月买药就得两千多。水电费燃气费加起来近500,吃饭省着花也得1000,这些账我记在着,越算心越沉。我现在这点退休金,养家根本不够……妹妹偶尔接济我,塞个三百五百的,可她脾气急,说两句就拌嘴。社区街道我也没找过,不知道还可以找到谁。

社会工作者跟小金在访谈
有时候坐着发呆,会想起辽宁老家,现在老家房子早没了,哥哥得了脑血栓,自顾不暇。我想过回老家,可我的医保在北京,半年得查一次嗓子。回去也没有可以营生的事情,但不回去,这房租就快交不起了。我自己这个岁数也没什么想法了,但是我女儿和孙子,如果我走了,他们可怎么办?女儿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小金癫痫一犯,谁给喂药?
什么是幸福?我觉得就是能看着小金好好吃饭,女儿能多说句话。要是哪天我不在了,希望有人能多照拂他们一把。我最想就是把这两个孩子安排好,将来我不在了,怎么能让他们能生活下去,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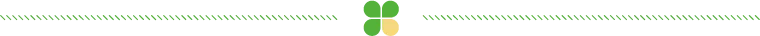
协作者始终将目光聚焦于困境流动人口,深切关注他们的发展状况与多元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群体的故事丰富而深刻:有人背井离乡,在陌生的城市中努力打拼,只为给家人更好的生活;有人遭遇挫折困境,却凭借顽强的毅力,一次次重新站起。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淋过雨,所以愿意为他人撑把伞”,他们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从受助者成为助人者,用自身的经历传递温暖与力量。基于此,协作者将用文字和影像记录、分享这些故事。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