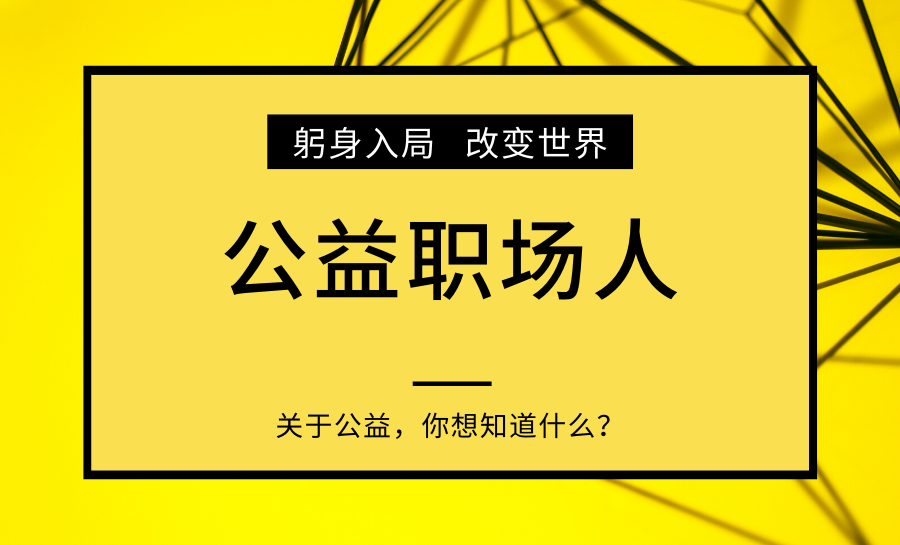2025-08-05
2025-08-05
 202
202“女性在摩梭人的心里面作为母亲,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存在,因为没有母亲就没有自己。”摩梭博物馆的尔青馆长说道。
摩梭人的母系大家庭,是一种以女性血缘为纽带、财产与权力沿母系传承的家庭结构。这种制度深刻重塑了女性的心理状态与价值观。
一项2020年的研究显示,生活在母系摩梭社群的女性,比生活在父系社群的女性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在父系社群中,女性的慢性炎症发病率是男性的两倍多,而这一模式在母系社群则恰恰相反;高血压的患病率也呈现同样的趋势,即在父系社群,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而在母系社群则相反。慢性炎症的发生率通常是衡量个体长期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这或许与母系大家庭中,女性拥有更多生活自主权有关。
另一方面,生活在母系社群的男性,其健康状况并未因此恶化。“男性在母系社群中,同样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权以及获取资源的机会,”研究者们如此解读。
摩梭母系家庭的结构特征
摩梭大家庭以母系血缘为核心,子女皆归属母系家族,姓氏与财产也随母系血脉传承。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舅舅承担重要的社会礼仪职能,而女性,尤其是达布(女家长),则负责管理家屋内务和家庭经济,所有成员的劳动所得都会集中到家屋中统一使用和分配。这种以集体为单位的资源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体陷入贫困的风险。
在母系摩梭家庭中,能够担任大家长或成为达布的,通常是家族中最具责任感、最有能力的人,而非单纯依据年长与否来决定。同时,家族的主要财产并不会直接由大家长独自掌控,而是根据家庭内部是否有年幼、体弱或需要照顾的成员进行相应配置。这种权力与资源分配机制,不仅强化了家庭内部的照顾责任,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资源过度集中于某一权力个体,确保了家庭成员的基本保障与公平。
对摩梭女性而言,这种母系家庭结构还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熟悉的成长与生活环境。她们通常与母亲、姐妹、外祖母及自幼相识的亲人共同生活,形成强韧的社交网络和情感支持系统。当她们的走婚伴侣前来探望时,女性始终处于一个熟悉且充满家人支持的空间之中。这种空间安排也天然具备对家庭暴力的结构性约束作用——伴侣的任何不当行为都可能被家人察觉并干预,从而形成有效的集体监督机制,进一步增强女性的安全感与主体性。

传统的摩梭家庭院落|图源:远行客
母系大家庭对女性心理的积极影响
在摩梭大家庭中,由于女性在经济事务上拥有参与权以及管理权,她们普遍展现出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对许多摩梭女性而言,所谓的“年龄焦虑”几乎不存在。即便到了三十多岁尚未走婚或结婚,她们并不会担心自己“嫁不出去”,也不会面临外界催促她们尽快成家的压力。在这里,是否成家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选择,而非社会的期待。
对摩梭女性而言,与其依附于他人,她们更倾向于通过认识自我来实现个人价值。正如纪录片《三个摩梭女子的故事》所呈现,其中一位受访者坦言,她不喜欢别人第一时间用“某某的妻子”来称呼她。因为在她看来,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需要与他人捆绑在一起,才能使自己完整。
在我们的采访中,一位名叫尔车拉姆的摩梭女子也分享了她的经历。她曾外出打工,但由于事业发展不顺,最终决定回家照顾孩子。然而,她强调,这一选择完全出于自愿;如果她愿意,仍然可以随时离开村子,去探索外面的世界——没有人能替她做决定。
此外,摩梭女性并不需要依靠“妻子”或“母亲”的角色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她们的身份认同更多来自于家族本身的归属感。这种结构性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她们的生存焦虑,让她们能够以更从容的姿态面对人生的选择。
由于财产归整个家族集体所有,摩梭女性在生活保障方面拥有较强的安全感。尔车拉姆提到,在她们的生活中,土地、房屋以及牲畜都属于家族共同拥有,即便某个成员暂时没有稳定收入,也可以依靠家族田地的收成,或者分享家中饲养的猪、鸡等基本食物。在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资源共享模式下,即使遭遇经济困难,家人之间的互助与支持也能有效缓解生活压力。正因如此,当地女性很少会因为生计问题而感到焦虑,整体生活状态也更为稳定。
在育儿方面,大家庭内部普遍实行共同抚养,育儿责任由多个家庭成员分担。这种集体育儿的模式不仅有效减轻了女性的育儿压力,更构筑了一套完善的家庭支持系统。以拉姆的家庭为例,三个孩子中有两个是姐姐的子女。由于姐姐常年在烟地劳作,孩子的日常照料便自然由拉姆、母亲和舅舅共同承担。
这种家庭成员间的育儿分工,一方面显著减轻了单一照顾者的负担,降低了产后抑郁等心理健康风险;另一方面,也为女性创造了更灵活的生活空间——她们可以选择阶段性外出工作,又能在需要时回归家庭,而不必担心孩子无人照料。正是这种富有弹性的育儿协作体系,使摩梭女性得以在育儿责任与个人发展之间找到平衡,从而拥有更自主的人生选择权。

拉姆的母亲正在织布|图源:远行客
母系大家庭对女性心理的潜在挑战
然而,母系大家庭的结构,也为女性成员带来了一些潜在的心理挑战。
首先,摩梭社会以家族利益为优先,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限制女性在职业和情感上的自由选择,进而带来相应的心理压力。在纪录片《三个摩梭女子的故事》中,达史拉措的经历便颇具代表性——当她深爱的汉族男友邀请她一起前往昆明生活时,她最终选择了放弃这段感情。对达史拉措而言,她与大家庭紧密相连,离开母系大家庭不仅意味着地理上的分离,更是一种文化认同的割裂。
在我们的采访中,一位摩梭阿妈扎西卓玛也提到,大家庭通常更倾向于她们选择本族男性作为伴侣。这种文化规训虽然有助于维系母系家庭的延续,却也在无形中限制了女性在情感上的自主权。
其次,在摩梭母系家庭里,尽管孩子由大家庭成员共同抚养,但这并不意味着母亲可以完全卸下对孩子的照顾责任。而对她们的伴侣而言,无论是兄弟姐妹的孩子,还是自己的孩子,男性往往无需承担主要的养育义务——是否参与抚养,更多取决于他们个人的意愿。
2017年,在一项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生西沃恩·麦迪森与波士顿大学社会科学学者沈颂怡合作开展的调查中,沈颂怡指出:“如今,在泸沽湖的旅游区,有越来越多的男性沉迷酗酒。因为他们可以依靠祖传房屋从事旅游业赚钱,不必像过去那样在土地里劳作以维持家庭生计。而生孩子、做饭这些事情,本来就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传统角色几乎消失了。”
虽然近年来这一情况已有所缓解,然而,与此同时,女性对家庭的传统责任依然延续。尽管她们在育儿与工作的选择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但许多女性依旧需要将从旅游业赚取的收入,投入到家庭和孩子身上。
在采访中,扎西卓玛坦言,虽然家庭的经济压力不大,但如今生活中最让她感到焦虑的,是教育孩子。作为家中有威望的女性,家里的孩子谁淘气了、学习不好了,都是她来处理。她既要为孙辈们准备饭菜,又要监督他们的功课,还常常扮演“调解矛盾”的角色。扎西卓玛苦笑着说:“他们不听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气得不行。”

摩梭小女孩在玩耍|图源:远行客
总而言之,摩梭族的母系制度通过财产继承、育儿合作网络和去婚姻化的社会结构,确实为女性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安全空间,显著提升了她们的心理韧性。然而,当我们深入观察这些制度的背后,也会发现,那些被赋予神圣意义的“母亲”角色,有时也承载着难以言说的情感压力与个人发展空间的牺牲。比如,“达史拉措们”为了守护家屋不得不放弃跨族通婚的自由,“拉姆们”在照料家人中逐渐被推向家庭内部的角色定位,这些现象为摩梭女性带来了某种形式下的新压力与边界。
这些现实提醒我们:制度本身并非终点,无论其形式如何,真正的性别平等仍需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同时,持续关注个体的选择权与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3434334
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4191521592075232&wfr=spider&for=pc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