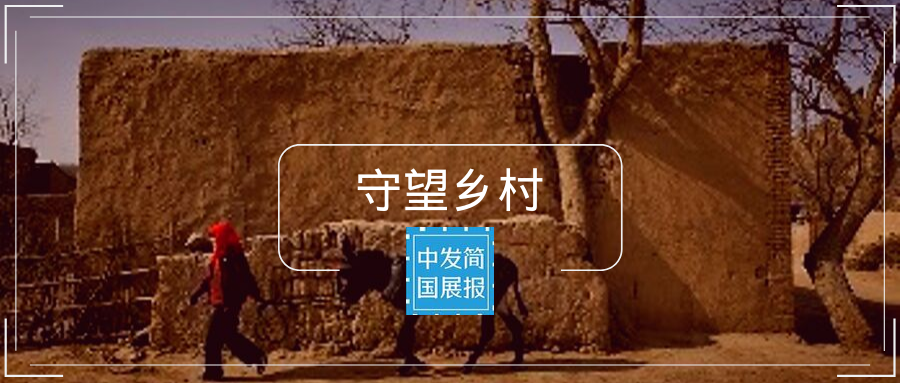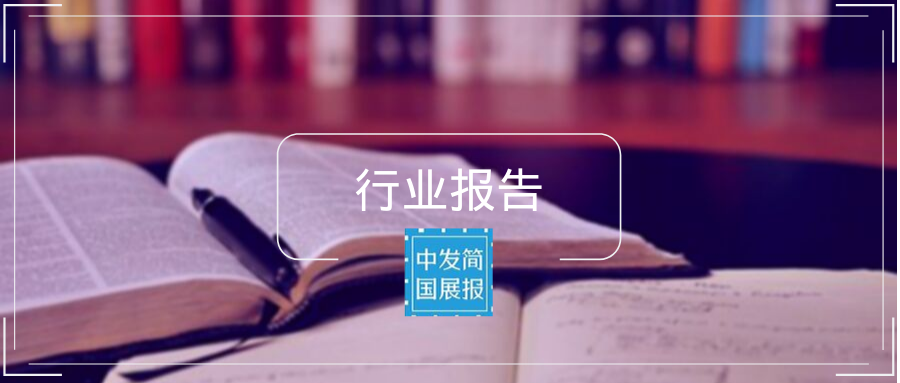2025-07-18
2025-07-18
 14
14口述者:李大哥(化名)/某平台转送骑手
整理者:李慕菲/协作者实习生
何慧慧/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者
李大哥,山西临汾洪洞县人,1984 年出生,初中毕业后便开启了北漂生涯,先后干过餐饮、保安的工作,2015 年起成为一名外卖骑手,至今已在这个行业奋斗了10年。李大哥常说:“幸福嘛,就是说不要一味地只挣钱,老人健健康康的,孩子也学业有成,一家人什么都挺好。”

童年:爷爷奶奶都对我很好,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的人
我是山西临汾洪洞县人,1984年出生,我们家一共哥俩,我是老大,下边还有个弟弟。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和我的舅舅、姨,他们四个人合伙去北京租摊位卖水果了,记得小时候,爸妈偶尔回来,我连一声“爸”都叫不出口,感觉他们就像陌生人一样。现在看来,我也是“留守儿童”,只是那时候没有这种说法。
我们这一辈的孩子全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冬天家里没有取暖设备,全靠土炕。奶奶会提前把被子“咔咔咔”铺在烟道经过的地方,炕烧得温热,我们躺进去就不那么冷了。我们早上上学,被子一扔就走,都是爷爷奶奶叠好摞起来。我爷爷在他那个年代学历算是挺高的,在乡里教过书,我爷爷的字写得也不错,过春节的时候还写毛笔字春联贴在门上。
后来慢慢长大了,我陪他们的时间也变短了,一年也就两三次。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媳妇都结婚了,回北京正好是晚上的火车,奶奶非得要让爷爷送我去火车站,可是这一来一回折腾半天,没有回村里的客车了,爷爷要走很远的路。我不想让他们遭罪。为这事,我还说了一顿我奶奶,觉得我都这么大了,还让我爷爷送,万一出事了,可不好。但这件事,我永远都会记得。

北漂:有人说北京生活压力大,我觉得这里什么都挺方便
2001年,初中毕业之后我就没继续上学,跟着三叔来到北京。第一份工作是在胡同口的小饭馆传菜,一个月三百块钱,那会也是刚出来,社会经验很少,我记得干了不到一个月,人家给了两百块钱的工资,还是四个人头的那种纸币,我高兴得不得了,只花了几块钱买了牙膏,剩下的都攒了起来。待了有半年多,我叔又给我讲,电视村那边有个单位,工资能拿七八百,还发洗头水什么的生活物资;日常穿的工服,铺的床单、盖的被罩都不用洗,把脏的放洗衣房里,再领一套干净的,那个也挺好,我就去那边也干了一段时间。
后来我又干了阵保安,就成家了。成家之后,我和媳妇都在北京的同一家饭馆干活,我在后厨,她在前厅当服务员。在那个饭馆待了一年多,因为我干得好,老板给我调到分店,我媳妇跟着过去了,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我媳妇就怀孕回老家了,我还在饭馆继续干。干了一年多,老板又在三元桥开了一家分店,说是要给我涨工资,第二个月从八百涨到一千二的时候,我特别高兴。我就想我一个月花两百块还能攒一千块。三元桥的店面有点偏,生意不是很好,原来的店又缺一个人,老板又把我调了回来,又涨了工资。后来工资发得不那么及时了,好多老员工都走了,我和媳妇也离职了。之后,我和我媳妇就在王府井小吃街给人家干,那个地方生意很好——国庆节的时候,每天早上六点钟上班,到晚上十一点下班,中午不能休息,那人都乌泱乌泱的,好累的。
2015年,我开始送外卖,那时候某外卖平台刚起来,有社保、保底工资,一个月三千块钱。王府井那一片一共就十几个人在跑,工服、头盔、箱子都是免费的;现在不同了,满大街都是骑手,大家在路上都是慌慌张张的。本来为了方便骑手,平台再不让进去的写字楼下面设置了一大排外卖柜,结果一个柜收五毛钱,都得骑手自己出钱。虽然钱不多,但是这个东西让人很反感,而且工服、头盔、箱子所有的设备都要花钱。有些骑手遇到收钱的外卖柜,即使柜子是空的,也会打电话说“外卖柜满了,给你放外卖柜旁边”,拍个照片就走了。其实免费使用,给客人的体验也很好——放柜子里边干干净净的,又丢不了餐。后面和协作者反映了这件事,不知是什么影响的,反正现在外卖柜免费了,不收我们钱了。再就是社保,我媳妇已经交了六年,她的那个公司年底也要退出中国了,还得再找工作。看着别的平台给骑手交社保,我也得赶紧交上,在这个平台也干了挺久的,要是补上也有小十年了。现在就是想找个有社保的工作,这样有保障一些。

家庭:现在这样平平淡淡的也挺好,心里踏实
我们老家那边一过二十岁,家里边就开始张罗结婚了,当时我妈打电话让我回家跟女孩见见面。流程大概是,人家介绍,我就去女孩家里边见一面,两人聊聊天感觉差不多,就去城里边逛一圈,给人家买个东西。那时候,我见了好多女孩呢。
当时我跟我媳妇也是一样的流程,好像是去城里边买了一条裤子,就打车回来了。我跟她说我妈在家里边准备好了饭,让她去我们家吃饭。现在想,那时候我真是傻呵呵的,我媳妇说:“不用去了,我就直接回了。”我在出租车上就和她说“走吧,没事,咱俩不成,吃顿饭也没关系”。最后,我媳妇还是去我家吃了顿饭,我妈给了几百块钱,然后我就把她送回家了。
2003年,我们结婚了,她比我大一岁,脾气特别好,很会过日子,该抠得抠、该花得花,我挺知足的,有什么事我们都是商量着来。结婚后,我们俩就来北京打工。我们在云湖宫那边租的房子三百块一个月,我记得有时候下班我俩饿了,外边的炒饼卖三块钱一份,我们就买一份要两双筷子,把那个饭盒撕开,一人一半。
2005年,我们的儿子在老家出生了。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回去了一趟。等到儿子稍微大点,我再回去看他,临走的时候他就扭着头不看我。孩子一周岁以后就是我爸妈带,我的儿子也成了“留守儿童”。我们一年回个一两次,多了就三次。
儿子从小就在老家上寄宿学校,二年级起开始独立生活。平常周末放假,我爸骑电动车来回接送他。后来,在小升初的时候,他考上了重点中学。那天,我还在送外卖,班主任在微信群里发——“有没有人接到某某中学的电话”,正看着这条消息,我就接到了电话,这是真高兴啊。中考的时候,孩子就差一点考到全市最好的高中,这个还是有点遗憾,后面去了另外一所高中。我和媳妇心里都希望孩子在高考的时候分数在600分以上,来北京——我们能离得更近点。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他想去哈工大,报志愿的时候我们说,既然他想去就冲一冲哈工大;最后,孩子高考603分,来北京上的大学,开学典礼上,当时他们学校的校长说来这里上学的基本都是全省排名的前5%,这是让我最骄傲的事情。
未来就希望儿子能找个稳定的好工作。我们也挺尊重他的想法的:如果需要,我们就去他工作的城市打工,这样我媳妇以后还能帮他带孩子;不需要就离得远一点,反正孩子们都有自己的生活。

遇见协作者:要是以后有需要我的,我也愿意来做志愿者
第一次走进东四小院是在元宵节,我站在小院里,心里觉得不行——总不能免费吃饭,干点活才踏实。协作者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我感觉挺好的。我和协作者的社会工作者提了外卖柜的事情,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的作用,外卖柜子真的免费了,原来普通人的声音真的能被听见。后来,我也参加了人际交往小组,慢慢也学到了沟通的技巧,这个真挺好的。未来,协作者开展的活动,我都会参与,只要时间允许。说实话,骑手的工作还是挺枯燥无味的,而且压力很大,在高峰期,神经都是紧绷的,和大家在一起唠嗑,学知识,就可以缓解压力,心情也会更舒畅一些。
新就业群体关爱行动
2025年,中央社会工作部在全国各省市试点开展新就业群体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委托社会组织具体执行。北京协作者负责承接实施北京地区试点项目,该项目将由中央社会工作部总体指导,北京市委社会工作部负责执行指导和支持工作。一直以来,北京协作者始终聚焦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与多元需求,用专业与温情守护城市奋斗者的梦想。如今,随着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骑手群体成为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穿梭街巷的身影背后,同样蕴藏着无数关于奋斗、坚持与善意的故事。因此,北京协作者采用文字记录骑手口述史,记录时代浪潮下平凡奋斗者的不平凡人生,让更多人看见他们的价值与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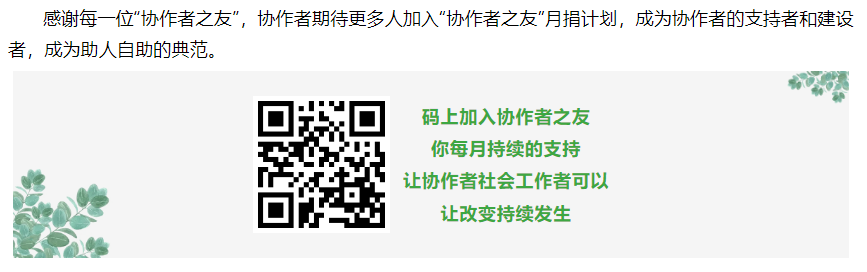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