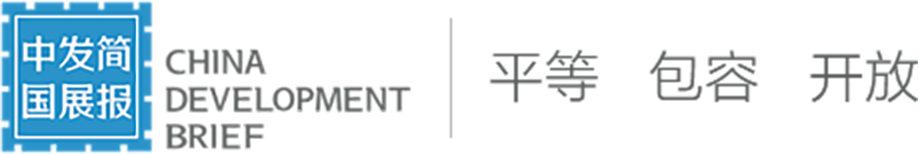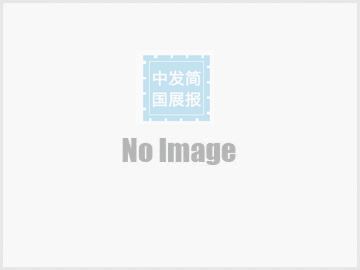2013-03-25
2013-03-25
 654
6542月份我去了趟新西兰出差。在葡萄酒节还没开始的时候,我溜达到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公园,看新西兰的“国宝”。不同于中国人民币上印着人,新西兰的纸币上几乎都是各种各样受保护的鸟。这个国家以自然风光和动物出名,所到之处所见之事,无不映照着人们心底对大自然的崇尚之意。
一到野生公园,我便忙乎了半天,喂羊吃谷物,碰碰这只马的头、和满地的鸡赛跑,玩得不亦乐乎。要知道,城市里都没动物给我近距离接触,机会如此难得,怎能不把握亲近?忽地听说下午五点有个观鸟的导航,辅导员会花一个小时时间讲解每种不同的鸟,还会在黑暗中找奇异鸟。好学如我必定不会错过,于是我报了名,不到五点就早早大堂里侯着辅导员。
辅导员是个阳光的新西兰大姐们儿,一看她眼睛就知道她对这里一草一木都充满着爱,而她那种简单又朴实的气质也让我留下深深的好感。她语带激动地跟我们介绍了这鸟那鸟,甚至同种鸟哪根羽毛色块不一样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同行的游客虽然也听得振奋,但他们都盼着看完最著名的奇异鸟就赶紧打道回府,当然,姐们儿也在不一会儿后察觉到了这一点。
我们走到了奇异鸟房跟前,辅导员在准备手电筒和一切所需物品。我们等着她的地方,有一个隔离网,网后有几只不知名的“生物”。而我之所以用“生物”两个字来形容,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都是会飞的、小小的、色彩斑斓的鸟,而在这远处的草丛中,虽然我并没有看得特别清楚,但体积分明是大的。那红红的嘴、翅膀扑通起来,加上那刺耳尖锐的叫声,更像只大型的“鸡”。我拍了拍辅导员的肩膀,指了指那堆草丛,问,这只鸟叫什么?
辅导员对我对它的兴趣似乎吃了一惊。她顿了顿,悄悄在我耳边讲道:这是我园子里最喜欢的鸟,她背后有个故事。要是有机会,我待会儿讲给你听。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转过身来大声地呼喊大家进奇异鸟房。我回头再看了那吵人的在地上跳动的“鸡”一眼,只好信步跟着大队走了。
看奇异鸟是重头戏,花费时间比较长,而看完,这次行程也基本上结束了。辅导员在送走大家后,只见我带着满腹的疑问,双手交叉在胸前向她走来。她摆了摆手,做出一副无奈的表情,说:“几乎没人问到过它。”继而拍了下手掌,又兴高采烈提起精神,“Well,你要听故事是吧,那你仔细听好了。”
原来这只鸟全世界只有225只。他的名字叫Takahe,不会飞,叫声还很吵,1898年的时候因为不知名的原因灭绝了,整个新西兰都没有了他的踪影,大家都相信不可能再见到它。而Takahe灭绝的十年后,有个叫Geoffrey Orbell的人出生了,长大后成为了一个医生,他一直相信这只鸟没有死。他找了很久,做了很多调研,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路。十几二十年,坊间总有传闻,说在哪里貌似见过那鸟一次。他就跟随着这些线索,终于有一天在风景秀美的蒂阿瑙湖旁边的一座山里找到了一串不熟悉的脚印,随后重新发现了全世界仅剩的两只Takahe。
跟我快速地讲完故事后,辅导员就去带下一波人了,留下了我在原地深思。Orbell医生找到Takahe的时候是1948年,当年他40岁。而往后的60多年至今,别人继承了他的工作、繁殖这只小东西,到今天整个新西兰才有了两百只。
我到了纪念商品店,尝试找这只“不死鸟”的纪念品,翻遍了所有本子、吸铁石,硬是没找到相关的产品。问店员,一个女孩儿挠着头,想了良久,把我领到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从一堆玩偶中抽出了一只Takahe,再找了找,又抽出了一只。我问店员,没有其他的了吗?我实在很想买这只鸟的纪念品,但玩偶好像不怎么适合我的年龄。店员再皱着眉头想了会儿,回答道,实在没有,玩偶也就这两只。你要就要,不要拉倒。
Takahe长得实在不怎么讨人喜欢,难怪硕大的店里,也只有这么两只玩偶的纪念品。我看了看价钱,狠了狠心,把两只都拥入怀里买走了。在回酒店的路上,我忍不住想,医生为什么要找这只鸟?这只鸟有什么重要的?它在整个宇宙之中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不是吗?
我把这事儿拿去跟朋友讨论,他说,那医生找到鸟,起码在人类动物史上留名了呀。我说,留名是留名了,但你想想他做的所有努力,所有坚持,所有不被看好,也就是在历史的洪流里留下小小一笔。你认为找到鸟在历史上留名会是他的目的吗?这是一单回报率能持平的买卖吗?有多少人在乎这鸟从灭绝到现在有了两百只,它甚至不为人知、不为人重视,以至于在纪念品商店里都没有什么商品!
朋友词穷。我继续说,也许这只鸟的传说之所以动人,是因为我们被医生心底的“信念”和他“不死的梦想”打动了吧。为一个梦想能坚持半生,难道不是平凡人里最伟大的举动了吗?
说罢,我突然想起四个字:“信者得爱”。耳边朋友幽幽地说道,所有的事情,你信,就会实现;不信,就没有办法了。
人间的精髓,大抵都如此吧。
后记:
谨以此故事送给我身边那些“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整天做着“不切实际”的梦,所以路比谁都难走。但别人未必理解的了的、时代未必能理解的了的,只要自己继续坚持不放弃,终有一天,他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不死鸟”。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