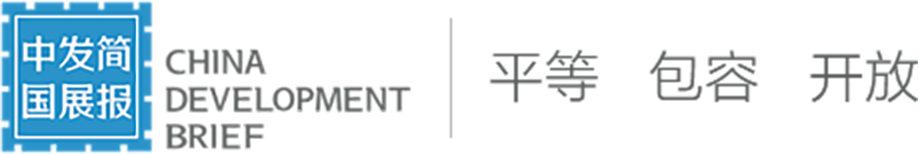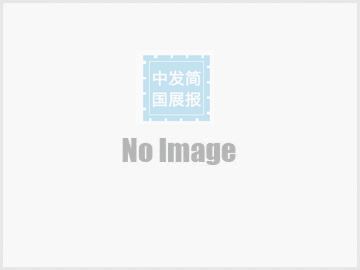2024-11-05
2024-11-05
 1498
1498
2022年9月起,云南协力公益支持中心、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和梦南舍可持续发展中心共同发起和气学堂·气候变化应对系列共学活动,邀请各领域专家、从业者结合自身领域与气候变化展开分享。至今,已举办线上线下活动20余场,主题包括气候变化与建筑、气候变化与农食系统、社会组织的气候故事等等。
即日起,和气行动项目组将整理过往分享内容,重温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不同领域从业者的探索与实践。本次分享回顾的主题为“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嘉宾是卓明志愿者团队、NCP生命支援的创始人郝南和绿色潇湘发起人、北京守望者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刘盛。
*本文由嘉宾审定后发布,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其所在机构或本平台立场。
近年来,气象灾害明显增多
郝南:
分类型理解气象灾害
郝南:

对的。其实近几年洪灾造成的伤亡,遇难人数中超过70%都是山洪造成的,洪涝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与上个世纪的伤亡情况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仙台减灾框架
主持人:
编者注:
2015年03月18日,第三届世界减灾大会在日本仙台召开,会议最终通过《2015-2030年仙台减灾框架》,该框架预期了未来15年全球减灾工作的成果和目标,明确了7项具体目标、13项原则和4项优先行动事项。其中4个优先行动事项为:
1. 了解灾害风险(Understanding disaster risk)
2. 加强灾害风险治理以管理灾害风险(Strengthening disaster risk governance to manage disaster risk)
3. 投资于减少灾害风险,提高抗灾能力(Investing i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for resilience)
4. 加强备灾以作出有效反应,在恢复、善后和重建方面“再建设得更好”。(Enhancing disaster preparedness for effective response, and to “Build Back Better” in recovery, rehabili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郝南:
仙台减灾框架是2015年提出的,到现在,对于气象灾害的应对,还是有很强的现实性指导作用。
仙台减灾框架提出了四个优先行动事项。第一个是了解灾害风险。这一点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更好地理解气候灾害风险的变化趋势。
我认为首先应该知道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在给每个人都带来影响。比尔·盖茨2022年说过,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最终一定会超过新冠给社会造成的影响。新冠疫情对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造成了影响,它改变了全球经济和社会的面貌,气候变化接下来也会对全人类社会造成这样深刻的影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们所面临的长期的局面。
极端天气越来越多,会变成一种新的常态;增长的趋势会越来越快,现在就能感觉到灾害一年比一年多,而未来几年感受会更加明显,气象灾害增多的趋势会继续加剧。每个人都会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气象灾害的极端性增加对生活造成的影响。
另一个优先事项是投资于减少灾害风险,提高抗灾能力。所有的准备都是要花钱的,有关方面需要花更多的钱去减少灾害风险。作为社会组织,我们要考虑如何提高自己的执行能力。要比公众掌握更多知识,同时要掌握一些社区内的适应性工作方法。这些方法需要专业知识作支撑,也需要去研发和学习。我们需要发出一些可靠的、能落到实处、能切实减少风险的方法和工具,而这些都是需要投资的。
还有一个优先事项是加强备灾以作出有效反应,在恢复、善后和重建方面“再建设得更好”。每个社区面临的风险及影响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更怕缺水,有些地方更怕水太多。每个地方的孕灾环境、承灾体、经济类型、脆弱性、韧性等都不一样,而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势,那么灾害风险应对的方式肯定也不一样。如何找到更适合每个社区的个性化的方案是尤为重要的。
此外,脆弱性是非常多元的,没有一套针对脆弱性的工具在全国所有社区都适用。每个社区的脆弱性的表现就像指纹一样,是不一样的。每个社区里也都有脆弱的人,有个体、也有群体。比如有些山区空心化特别严重,尤其留守老人多的情况特别突出,有的村子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占了40%,甚至更高。那么,这样的社区脆弱性就集中体现为说老年人过多,劳动人口过少。有的老人腿脚不好,跑的时候得有人背着,避险工作的组织就更难,这样的问题非常突出。
城市社区脆弱人群的类型就更多元了,那些我们平时在街上看不见的,不太出来遛弯的人,在水灾当中都是脆弱人群。灾害发生时,这些人需要每个人都有专门的对策,一人一策地去应对灾害,这是目前全社会相对来讲比较空白的一些方面。其实疫情的时候已经为解决这样的问题给出了很好的方案和模板,比如当时广州市就为八类脆弱人群,每个社区的每个人都建立一个档案,有专门的社工去负责每个人,定期巡查他的需求,不能说做的十全十美,但这个措施本身是有效的。这样的措施同样可以迁移在极端天气的应对中,这是可以行动的一些方向。
还有一个不在优先事项中,但我觉得也特别重要的,就是气象灾害的早期监测。气象灾害发生往往是个过程,从宏观的天气异常,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南方涛动(ENSO),到副热带高压异常这样的中观尺度的天气异常,再到微观尺度异常比如极端降水,它有个发展过程,那么就可以提前做一些预报。这种预报特别重要,包括实时降水量的监测。根据每小时降水量的异常,推断出不同地方承担的风险。那么在水涨起来、人被淹之前,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地方可能发生的灾害过程提前做一些应对的准备。这个工作可以极大提高我们在社区应对灾害的效果,尤其像山洪或泥石流这样突发的地质灾害,尽早采取措施,我们甚至可以把人员伤亡降到零。
社会力量参与灾害应对
刘盛:
把时间尺度拉长来看,气候变化是在过去的工业革命、工业文明起来以后才发生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随着人类变得越来越强,对环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才有可能人为地去干预气候变化。
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没有经历过特别大的灾害,就像没挨过饿就不能体会真正的饥饿,我们对灾害也没有体感。我们现在认为遇到灾害被人救是应该的、特别确定的,其实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以来,遇到灾害都是没人救,要靠自己的。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我总结了灾害的三个新特点,第一个是灾多,灾害变得越来越多;第二个是灾重;第三是灾变,灾害变化无穷,不可预测。当然我们的防灾抗灾能力也在增强,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风险也在变大。
在备灾抗灾和重建的过程中,要做到对高风险人群的一人一策,成本是很高的,但我认为有一点是可以做到,就是让每个人的生命都被尊重,可以从公众的视角出发,设计一些公众参与的、体感很强的项目。
例如,我们这两年在做长沙古井的调研。早年间长沙有一个职业,就是挑水工,他们在湘江挑水,卖给城里的人。当时有上万人,就像现在跑腿的人一样,你在网上叫个外卖就有人给你送,那时候也一样,你在路边喊一下“我们家没水了!”他就从湘江来挑一担水来给你们家。自来水是20世纪初才有的。
如果发生灾害,三天或者更长时间没有自来水,甚至自来水系统被冲毁了,那我们怎么过日子?可能真的要求助于遍布长沙的将近3000个水井。在城市郊区,很多古井还在,它们有没有可能被城里人看到,去保护起来?这有可能成为降低脆弱性、增强抵抗能力的一个因子。
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作为一个环保组织,如何去应对气候变化。比如现在很多地产公司到江边、湖边盖房,这些房子其实就是破坏了水边的湿地建造的,发生水灾的时候,这样的房子被淹的可能性更大,尤其地下车库是极有可能被淹的。当我们谈论应对气候变化时,与公众自己的财产安全、对生产生活的影响等发生关联,他们可能才有感觉。
郝南:
从社会力量参与的角度,有两个思路与刚性的、预防与为主的思路有所区分。
一个思路是“与灾害风险共存”。以前我们把灾害叫“洪水猛兽”,建更高的堤坝把洪水挡在我们生活的社区之外,洪水来了就赶紧跑。那么现在这个思路可能不能完全奏效,我们必须得学习与洪水、与干旱共存。
洪水来的时候与其防范被淹,不如把水直接蓄积起来,把洪水变成未来几年的水资源。很多地方已经提前做了蓄洪区,可以把水留下来,补充到低洼地区。另外,引入保险机制和政府补偿机制,没有灾害的时候,正常生产赚钱,发生灾害,也能拿到一些赔偿。
那么,如果房屋的选址、设计、建造,整体的农业生产规划、城乡布局规划等,都围绕这样的方式去做,就能适应风险了,来水也不怕被淹,这时候脆弱性就大大减少、韧性就大大增强了。
另一个思路是“传统智慧中有方法”。气候变化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事,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经历过好几次气候变化。比如,河南之所以简称“豫”,是因为以前河南有大象,它是温带季风气候,非常湿润,和现在不一样;又比如黄河的上游,以前也不是黄土高原,而是森林。有些地方对水灾的记忆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印记,融入到当地的社区环境中了。
很多人口集中的地方,都会有本土的宗教信仰,有各种庙,庙里的对联内容都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不要有水灾、不要淹我们家,或者即使有水灾,第二年的收成能够更好,其实在民间本土文化当中已经包括了气象灾害适应性的相关内容。所以,很多地方建立起与水有关的文化系统,其中就蕴含着应对极端性的水灾的策略,这些策略是现在我们可以去挖掘和依据的。
灾害与人类的生活环境本来就是相互适应,并不是分离的。从前,没有人的时候,灾害事件造就了我们现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当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后,孕育它的因素反过来成为了不利的因素。
我们现在应该有智慧地把我们的发展方式与致灾因子的始动因素联系起来去应对,而不是用决然对立的方式去应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灾害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它孕育了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也在告诉我们,现在有些事儿可能是我们人类做得不对了,我们的发展道路走得过于极端了,这其实是对我们的一种警示。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