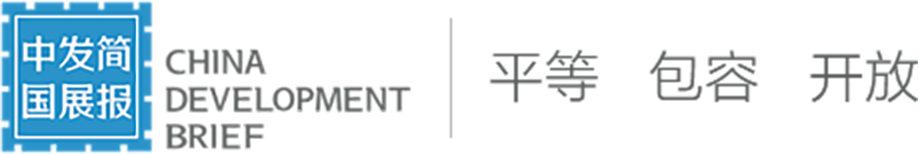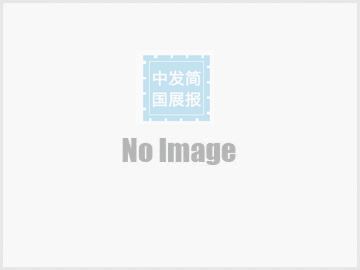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
“公信力是公益组织的生命线”这一观点早已成为行业的共识。但近十几年,因善款监管不力造成的公益丑闻频频发生,几起备受瞩目的行业丑闻令公众对公益信心降低。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公益组织里的种种行为到底该由谁来监管治理?
一般而言,治理包含“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对于公益组织,“外部治理”指的是政府、社会公众、媒体等的问责;而“理事会治理”相当于“内部治理”。公益组织的财产是社会财产,组织内部通常设有理事会,由理事会代表社会,监管社会财产,行使决策权,并监督组织接受财务审计,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度。公益丑闻频发能否说明我国的公益组织理事会治理失效?“理事不理事”是国内基金会的常见现象,这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是什么?如何从立法上突破理事会治理困境?围绕这些问题,《社会创新家》采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社会创新家》:备受关注的“儿慈会事件”,引发了公益行业诸多反思,其中一个是关于基金会理事会治理的问题。从儿慈会到公益行业,能否认为理事会治理是失效的?
贾西津:儿慈会的事情可讨论角度比较多,不完全是理事会治理的问题。“儿慈会9958项目”涉及个案打包筹款模式。这个模式不仅儿慈会在做,也有其他机构做,在中国当下捐赠文化和信任机制下,是一种相对容易获得捐赠的筹款模式。以个案发起群体筹款虽然不违法,但一直都存在公益伦理上的争议。因而这个模式本身,存在认知层面的问题。理监事会是基金会的决策和监督机构,有决策、监管和支持等职能,既有目标实现、扩展资源,又有合规监管、风险把控职责。对于有争议性的项目,理事会应当充分讨论,为机构把控方向,尤其是项目的公益属性,确保和机构的愿景、使命、价值观契合。个案筹款的模式要不要做,“加盟”筹款的快速扩展有否使命引领,地方站点负责人有什么风险,理事会有把握责任。但现实情况可能没有这么理想化。比如长期延续的筹款模式,或机构选择地方加盟站点,可能都不一定在理事会上讨论;还有地方站点参差不齐,负责人各有对项目理解的差异,背后动机很隐匿地加入进来;财务审计也是如此,审计报告在流程上是合规的,监事会通过审计报告,甚至很好做到向社会公开,但实际上捐赠收入和资助去途如何决策、对接,是否指向了特定受益人,未必被识别。所以,项目出现问题,问题可能有多种层次,要具体分别,不只是笼统说理事会治理失效。《社会创新家》:很多公益人戏称,他们的“理事不理事”。很多理事长都是从朋友圈里找理事,理事也是碍于情面答应。基于这层朋友关系,理事们也不愿讲真话,就起不到什么作用,更不会向监督部门如实报告。对于“理事不理事”的现象,您有哪些观察?贾西津:我没有专门做过理事会治理的实证调研,无法给到你具体的现实情况。但从一般意义上,理事会通常有两类,一类是咨询型理事会,另一类是决策型理事会。在咨询型理事会,理事们的角色主要是提供相应的咨询建议,帮助创始人实现愿景,这在第一代公益组织中比较常见,创始人有很强的公益发心,强大的行动力,理事们更多是基于对创始人的认同和支持参与进来,作用会比较虚化,还有企业基金会的理事会有些也是以执行企业决策为重;在决策型理事会,理事更实质参与机构的运行管理,在重大决策中的确行使决定权,这类理事参与治理的民主意识就会较强,在制度化运作的公益机构中,理事会应该是决策型,权责相应。但是形成规范的治理机制,是需要创始者或公益组织负责人本身,有意识、主动寻求制度约束的,理事会也需要有这样的价值共识,在文化和制度能力层面都是有挑战的事。现实中“理事”和“不理事”的情况均存在,各机构理事的参与情况有差异,做好并不容易。《社会创新家》:您提到民主意识淡薄,在理事会治理上存在一些问题。这背后更深层的文化原因是什么?贾西津:有一定的关系。在公民素养比较高的地方,人们愿意在公众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知道如何与人沟通交流,那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在社团里,他们依然可以延续这种的沟通方式,实现民主决策。显然,这不是我们的日常交流方式,而公益机构又需要理事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即便与机构领袖的观念不一致,理事们还是必须讲。那在我们的社团中,大家能不能谈起来?有些组织的理事是企业家,他本身不断经历决策过程,这些人坐在一起,想实现什么公益理念会表达出来,也愿意坚持自己的想法。若是这样的讨论氛围,对理事会治理是有益的。但很多时候,理事们平时也缺少民主实践,对于意见表达、民主决策,也没有什么意识和经验,像你说的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深究,或对机构了解不深,没有时间投入和参与,这就难以起到治理的效果了。《社会创新家》:“情”和“理”构成了社会心智的一体两面。中国人注重“情”,而忽视“理”,因为“情”更适合人际关系的稳定发展。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治理”这个词是否就不适合中国的土壤?贾西津:我认为,“情”和“理”不是对立的关系,放到理事这个角色上,也不冲突。以法官为例,一个好的法官,他一定是有理又有情,面对一个案件,在最深透处实现的不只是纸面法条,而是法目的。理事也是,他要对公益的使命与价值有十足的理解,同“情”共感,才能在决策中引导组织选择正确的方向。治理这个词本身没问题,它表达了组织的有效管理,这种管理不是某个人发号施令,而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实现组织使命。在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人情世故方面的问题,甚至是违法问题,但不是说治理这个概念就不适合;人情世故跟中国的土壤也没有必然联系,它在人群中或多或少都存在。多元主体之间的平等自主交往,我们确实比较缺乏经验,需要学习和实践中练习。《社会创新家》:理事会对于公益组织,相当于董事会对于上市公司,企业里董事治理的效果相对好。理事治理为何如此艰难?这背后存在哪些结构性的矛盾?贾西津:理事和董事在本质上不同。企业的董事是股东,是公司的所有权人,但公益的资产具有公共属性,不归理事,因此也就造成治理上的困难,理事并不会像董事那样具有明晰的产权和利益激励。因此,公益组织找理事,更多依赖声望信任,也就是理事已经有自己谋生的手段,来公益组织当理事不是为了谋利,而且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使得他非常珍惜自己的名声,社会信任度较高,他愿意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来寻求公共价值、公益价值,在公益机构中是代公众进行监督,为公益目的负责。《社会创新家》:您曾提到,在英美国家,每个理事要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在您看来,一个合格的理事应做到哪些方面?一个有效的理事会应起到哪些治理效果?贾西津:在理事会治理上,国际上有两种通行的做法,英美国家的理事叫独立理事。每个理事独立为自己的决策负责,不代表其他人,不代表集体,只代表自己,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签字权,个人责任感更强些。我们和欧陆一样,实行的是另一种模式,即理事会治理,或理事长代表制。这种制度强调集体决策,侧重将理事会视为一个整体,由理事会做出决策,最后理事长还有代表理事会的签署权。虽然理事个人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包括对理事会决定保留个人意见,在一定条件下起到免责保护作用,但总体上,都是集体决策,个人责任感偏弱一些。理事会条例明确规定了理事会的决策和监督职责。一个理事会只要做到法律上的不违法就是一个合规运作理事会,但合规离做得好还有很大距离。一个好的理事会是会自我约束的,提出更高的要求。基于对机构愿景、使命、价值观的认同,形成使命驱使的战略,才能把机构带向“对”的方向,向“好”公益发展。每个理事需要小心呵护组织使命,充分贡献自己的能力价值;治理层和执行层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理事会既不干预执行层自主性,又能足够保障公益目的;执行层也能够理解组织使命和战略方向,主动去推动其实现。这是一种好的治理关系。《社会创新家》:南都公益基金会、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自然之友这些机构一直是国内理事会治理的标杆。他们做到了什么?有哪些值得公益机构学习的地方?贾西津:以自然之友为例,机构历经了几次传承,从最初依靠创始人个人魅力治理,到慢慢形成自己的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机构的治理层和执行层不断探索,执行层主动考量请求约束自己的权力,决策层谨慎过度干预、有意识陪伴执行层的人员成长,最关键的是,彼此不断回到组织的初心、使命,深度沟通交流,识别细微的价值分歧,呵护愿景、使命、价值观的共识在组织内外生长,这是非常细致的工作,需要投入时间,慢慢探索。阿拉善SEE也是从创立之日就持续经历治理探索的过程,他们除了政府要求的规范章程,还有自己额外的、更细的治理机制、议事规则等;南都也是同样的方向,都是做了大量超越法律之外的自我的规则约束、伦理约束,理事们是共同探索、朝向共同守护公益目的而努力。同时,不仅需要考虑现有的人如何做事,还要建设组织制度,做好公益目的的传承。《社会创新家》:如何从立法上突破理事会治理困境,实现多元的理事会?贾西津:目前《慈善法》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具体的规则太多,限制太多,法条在各种不同维度约束机构的行为,但未和最终的公益目的相关联,甚至还没有对公益目的的定义。这样容易产生做好事的被管太多,想做坏事的仍然不足以被管住,反过来当问题出现,进一步导向更多限制的方向。其实英国的《慈善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它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慈善法。它的公益监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内在逻辑,就是保障公益目的。它的政府许可权并不复杂、也不多重,但各种慈善概念以公益目的来定义,所有对行为的法律监管原则,就仅限于公益目的不被滥用,只要在公益目的中,就享有相应公益权利—最重要的是免税;反之,任何对公益目的的侵害,谁的行为谁负法律责任、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如此一来,公益机构遵守法律,就是为公益的目的负责;它对法律规范的遵循,首先也是自律自觉的,是组织使命内在的需求。回到公益目的上,是法律监管和公益组织达成同向需求,突破治理困境,实现主体责任的落脚点。这样公益组织可用的手段是非常放开的,它的目的和责任主体则十分明晰。
 2024-09-25
2024-09-25
 1761
1761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