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6-09
2023-06-09
 601
601什么是社会影响力,什么是“善”?我们做的好事是可以或应该被量化衡量、比较的吗?
为什么公益事业需要与理性结合,科学精神将如何颠覆我们对于行善助人的想象?
我们应当关注远方的苦难吗?遥远的弱势群体和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有区别吗?
超出利己范围的行动(如捐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为什么可能是一种道德义务?
近日,由公益盒子研究总监李治霖作为主讲人的讲座顺利开展。讲座分享主题为“激进地共情”,下面是这场讲座的回顾。
讲座回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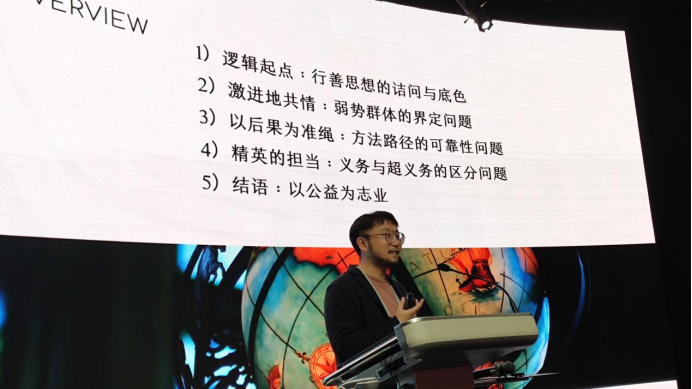
我一直觉得大家对公益有所误解,一想到公益可能还是停留在捐钱、建学校或者支教,好像公益行业非常边缘、在社会里也不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求职的时候也绝对不会考虑这个行业。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公共生活中获得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权利、有什么样的义务、怎么去跟大家交互、怎么过一种良好的生活,这都是公益问题。
逻辑起点:行善思想的诘问与底色
想象你正在去上学的路上,你路过了一个比较深的池塘、水井或者沼泽地等等,你发现路过的池塘里有一个小朋友正在奋力呼救,因为他快要被溺死了。请问在场的各位有多少会停下来去救他?
现在加点条件,如果你去救这个小朋友,你会弄脏你身上这套刚买的昂贵的衣服、需要洗衣服,你的期末考试会迟到。请问,如果有这样的代价,你还会不会去救他?
大多数同学还是会的。
这是在全球伦理学界备受争议的一位学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实验。他的思想实验想表达的和孟子有点类似,就是“人皆有恻隐之心”。当我们看到身边有人正在受苦,我们都会想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他在1971年写了《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这篇论文,这篇论文对我影响很大,在根本上重塑了我对公益这件事情的思考。
他写作这篇论文的时间是1971年, 那时,孟加拉地区正在经历战乱与饥荒,病痛与死亡随处可见。所以他在思考,对于那些远方的生命来说,我们究竟能不能有意义地做点什么呢?简单来说,如果远方有人正在受苦,但这件事不在你眼前发生;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小朋友因为生病过早地死亡、或者遇到灾难需要帮助。彼得·辛格想要讨论的是:这些远方的孩子跟我们近处看到的孩子有区别吗?
他推理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能够去防止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并且我们不需要牺牲自己同等道德权重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就有道德责任去做这件事情。简单而言,如果我们看到有人正在受苦,并且给予他帮助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应该去帮助他,如果没这么做才是有问题的。就好像大家在谴责小悦悦事件中无情的路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人是有问题的,而不会因为如果有某个路人救了小悦悦就给予他特别大的赞赏。这是他这篇论文里提出的非常重要的观念,之后在全球伦理学界引发了几十年的讨论。
我认为他提出了一个我们应该如何思考远方时时刻刻正在发生的苦难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关注?我们究竟能做什么?他给出了很好的结论、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
这个结论引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是弱势群体,谁需要我们的帮助。这是我们在做公益的时候,面临的第一个问题。谁是受助者?谁是弱势群体?是否只有弱势群体才需要帮助?当我们在考虑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帮助谁呢?
即使是家庭中也有一定权利地位财富的差别,有某个亲戚过的不好,那么他是家庭内的弱势群体。朋友同理。社区里也有经济条件不好的邻居、很多鳏寡孤独者。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做公益的起点,我们关心别人很多时候是从关心身边的人开始。但是世界上还有乡村里的孩子、难民(比如因为中东问题或者俄乌冲突流离失所的人)、战争的受害者。世界上有许多的弱势群体,在我们思考公益的时候,首先要问我们究竟想帮助谁。能帮助的人有非常多,但究竟怎么帮助下面这一行的人呢?我们之后也会简单提到一些方法。但当我们在考虑弱势群体是谁的时候,不应该局限于身边的人,你因为各种因缘际会认识的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社会上需要帮助的,需要我们投入力量去解决的问题非常多。
作为一个引子,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没有人会不同意“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吧。至少在自然状态下,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一个人无论出生在哪里,他都应该跟我们具有平等的地位,不会因为他出生在别的地方他就低人一等。这是我们现在社会的共识,人人生而平等也被写进了美国的《独立宣言》。
但是几个问题产生了。
如果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那远方的人和我们身边的人,谁更重要呢?远方的人离我们很远,我们看不到他,因此他就不值得我们帮助吗?这是第一个问题,是地理距离上的“远”。
第二个问题是人际关系的远近。亲戚,邻居,陌生人。这三个群体你认为他们平等吗?
第三个是,我们会不会倾向于帮助和我们相似的人呢?我们是黄种人,那么是帮助黄种人更重要,还是帮助白人黑人也一样重要呢?
在伸出援手缓解困难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做这个优先关系的排序呢?
假设我们已经认同了人人生而平等。但在做出任何一个选择的时候,同时就放弃了其他的所有选择,这在经济学上叫作机会成本。
我们先思考一些距离和关系远近的问题。
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左边是中国农村的孩子,我们做公益很多时候会先选择去农村小学、初中做支教,这是很多人公益之路、行善之路的起点,这是特别好的事情。但是中国农村的孩子,很多是留守儿童,他们长期缺乏父母的陪伴,导致了他们有些人早期发展不良。早期发育不良就是一个孩子如果在0~3岁大脑发育关键时期,没有足够多的养育刺激,缺少父母的陪伴的话,孩子大脑刺激神经突触之间的连接建立不够完整,就会导致他大脑发育迟缓。农村的孩子在早期得不到关键的照顾,导致他们大脑发育的程度就是比城市里的孩子要弱很多。这样的农村小孩数量极其庞大,中国早期发展不良的儿童有1743万,有将近40%的儿童都面临着早期发育不良的风险。这些孩子可能离我们很远,大家虽然可能有接触过,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持续发生的严重性,影响未来我国的人力资源和人才素质。
右边是一个更严重的世界性公共卫生问题,疟疾。青蒿素的发现为解决疟疾问题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尽管中国已经消灭了疟疾,但在非洲、南亚等地区,每年仍造成将近50万儿童的过早死亡。目前疟疾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但是因为它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用药水浸过的蚊帐能够给孩子们提供有效保护。整体来看,欠发达地区仍然受传染病的巨大的威胁,更发达地区的人们受慢性病如血压控制、血糖管理等影响较大。不过无需怀疑,在我们过着每一天的生活时,有非常多的弱势群体在远方不断经历着生命威胁。
举个例子,一个 2023年1月份的数据显示2021年约有190万婴儿死亡,500万儿童在五岁之前死亡,另外约有210万5至24岁的儿童和青年丧生。婴儿死亡大部分是因为早产、夭折和分娩过程中的并发症。而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主要是因为卫生条件不好、疫苗覆盖率过低等完全可避免的原因导致的。
500万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很大,但我们很难有非常直观的感受。让我们来进行一个换算,将500万孩子平均到365天之中,那么每天中有13700个孩子因为可避免的原因过早死亡。13700人是什么样的数字呢?想象一架民航客机,一架飞机上有300个五岁以下的儿童,那么每天有46架满载五岁以下儿童的飞机失事。这就是此时此刻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旦发生空难,我们都会有非常强烈的情感共鸣,但是这些沉默着的正在发生的死亡远比空难要糟糕的多。
难道不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就不重要吗?我们就可以不关注吗?
当我意识到每天有46架满载着五岁以下孩子的飞机坠毁的时候,我认为这应该占据全球所有新闻的头条,而不是只在有空档的时候才出现。为什么我们总对大的数字感到迷茫?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叫做规模钝感。这意味着人们对于特定群体的关注不会随着群体扩大而增加。曾经有心理学家问受访者,如果有2000只、2万只、20万只候鸟会淹死在油库里,他们愿意花多少钱来解救?得到大概是80美元、78美元 和88美元。死亡的数量呈指数级膨胀,但下面的捐赠数字就增加了十块,甚至还会减少。
右边这句话据说是斯大林说的,也符合斯大林的特点。(但是这是谣言,并不是斯大林说的。)“一个死亡是一场巨大的悲剧,而100万个死亡只是一个统计数据。”但100万个死亡实则应该是100万场悲剧,不只是一个统计的数字。
规模钝感这个词在公益领域中其实很常见,比如说,帮助一个人获得的关注有可能比帮助100个人还多,但为什么数字变大对人们公益投入的影响如此有限呢?
有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者提出了两种很有启发的理论。
一个叫“原型价值论”,我们往往关注的是问题的原型,比如一只候鸟,一个病人,一个孩子,我们关注是后面那个名词,我们关注的更多是性质层面的定位,而不是前面的数字。我们很多人逻辑上会有这样的潜意识,也是我们心理认知上的偏移。
第二个解释“道德满足论”,就是我们捐赠和帮助的动机,其实不是真正的帮别人解决多少问题、避免多少死亡,而是要获得一种尽到的责任的满足感。我捐了1个人,和捐10个人、100个人、100万个人,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样的。我做了一件好事并不会因为这个数字疯狂扩大,就好像感受到自己“积德”的量也成比例地扩大了。很多人想的是尽到这个责任就可以了。
当然这两种解释不是去支持规模钝感,规模钝感是一种认知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如果真的认为人人生而平等,那一个人和100万个人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他和我们一样有朋友、亲人、爱人,有自己的事业,有开心、快乐的时刻。这样一想,就不可能再把这些数字看成一个简单的统计数据。
我们刚刚讨论了距离远近的问题,现在让我们再看看我们是如何对待那些“看起来和我们不一样的”生命的,ta们对于我们来说是平等的生命吗?
第一个是性别歧视的问题。(左边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博客,大家如果有条件可以去看一看。)第二个是种族歧视的问题。第三个是物种歧视,比如我们都觉得柯基很可爱,但是小猪其实也挺可爱,只是我们可能中午就会吃了它。
我们可能会因为对方跟我们不一样而去歧视他们——比方说因为男性和女性不一样,男性(包括我自己)占据了这个社会绝大多数的资源和优势地位,就自然地去维护自己的共同体利益。(我今天在这里做讲座也是典型的mansplaining,我感到很抱歉)。
我们会因为柯基可爱、猫可爱,建立一些公益组织去保护流浪猫流浪狗。但你有见过关注农场里的猪的生存状态的公益组织吗?中国有一点、外国有一些,但整体的数量和关注动物和流浪动物的相比还是少很多。但一只猪和一只狗的差别是什么呢?它们一样都是脊椎动物,它们感受疼痛的方式跟我们一模一样,在智商上,甚至猪的智商在很多时候甚至比狗还高。我们不会说猪生来就是被吃的,但一直都是这样,从来便是如此,这是人类的物种歧视。
因为它跟我们不是一个物种,所以我们认为它就低我们一等,这和ta跟我们不是一个种族,所以ta就低我们一等,和ta跟我们不是一个性别,所以ta就低我们一等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至少我认为是这样。)
这背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谁应当成为我们道德关怀的对象呢?Moral Patient就是谁值得我们在道德上去关注。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也不能给出明确答案,但是我想说,这类问题背后的预设都是很明确的,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一点。
对于我们刚刚最后的一个问题,谁应该成为我们道德关怀的对象,边沁,一个非常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他提出了一个得到了非常多的人认可的观点。
The question is not,can they reason?Nor,can they talk?But,can they suffer?不是因为他们能否像我们一样说话、或者他们能否理性地思考,他们就值得我们的关注。而是因为他能否感受痛苦、和我们一样感受痛苦,才值得我们的关注。
我想举个例子:0-3岁的小朋友是没有人格(personhood)的,即他们尚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自我(self)的观念,也没有回忆及展望未来的能力。我们每个人在0-3岁左右都是这样,可能有些极端,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物种的区别,年幼的我们自己和一只宠物狗的理性思考的能力、能否跟其他人对话交流的能力、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很类似。同理,这个社会中有非常多的人,比如先天大脑发育迟缓、唐氏综合症患者,他们也是没办法和我们理智地沟通、没法成为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就去歧视他们,反而会认为他们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值得更多资源的投入,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先天遭受了某种不幸。如果我们这么去想的话,为什么动物仅仅因为它跟我们不是一个物种,它就一定比我们低等,而不是它们是弱势群体、值得更多的关注呢?
如果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在距离层面上,无论他是在哪里出生的,都值得我们平等的对待。那如果在时间距离上呢,无论他们是在何时出生的,都值得我们的平等的对待吗?
举个例子,这有一个陷阱,脚踩上去会非常痛,一个小女孩儿在今天踩到了,她感到非常痛,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事儿太糟糕了、我们应该帮助她。但如果她十年之后踩到了,我们会觉得这件事儿就变得不重要了吗?反正她都是踩到了,今天踩到明天踩到也类似。
这个例子会延伸出来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如果我们今天怎么做无所谓,那未来的孩子们就跟我们没关系吗?我相信如果我们谈到气候变化,大家不会这么想。因为气候变化就是一个我们今天的行动影响了未来人们的福祉的问题。还有一些别问题同样也会给我们的未来世代带来非常多的不公平。牺牲今天的环境、而不顾未来的人们去发展经济,这某种程度上也不符合人人生而平等的预设,或者所谓的道德理想的状态。这个在政治学上叫作“代际正义”问题,就是不同世代的人们是否得到了公平的对待。
但是我觉得这同样跟我们怎么定义弱势群体有关。未来的人对他们生活的世界是没有发言权的,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由之前的人决定。所以说某种程度上,未来的人是弱势群体,因为他们无法决定他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这种意义上关心未来的世界是否会变得好或者坏,也是一种公益。
这也是我们在进行公益、我们帮助别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想特别提出一点,就是我们关怀的对象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是在不断扩大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从道德圈层的扩展来说,在原始部落的时候,大家只关注自己、然后开始关注自己的亲人;到了形成稳定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开始关心同宗族、同社区内的人;慢慢地,我们废除了奴隶制,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对待另一批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慢慢地,我们开始反思种族主义,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对待跟我们肤色不一样的人。到了现在的社会,性别是一个非常明确并且热门的话题,我们开始反思,这个社会对女性是否安全、男性在这里占据了多少优势地位。
可以说人类的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个道德圈层不断扩展的历史。到了100年之后回望,我们会不会觉得现在对待动物的方法是不合适的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巨大的问题,只不过那个时代的人是不会意识到的。我们现在认为非常伟大的哲学家在2000年前很可能都是奴隶制的支持者。每个时代有它的局限性,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不应该假设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问题的,所有人都已经得到了平等对待。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还是在这个这个层面上不断取得进步的,我也期待我们未来能取得更多的进步。
那么第二个问题,也是彼得·辛格论文里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远方的人我们真的能帮助到他们吗?或者说我们通过利他的行为过程,究竟能对远方施加什么样的影响。很多人会说,远方的小朋友出事了或者是因为疟疾死亡了,我好像没法帮助他。我们在想帮助别人的时候,究竟能帮助得到别人吗? 举个例子,如果现在有一个科学家攻克了人类衰老的问题,那绝大多数疾病都会没有了,因为衰老被攻克了。但是衰老攻克不是一个公益导向的事情,因为太难了,这就是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远方的苦难和问题都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
接下来我想请大家简单看一下三个选择题,关于特定公益行为对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究竟有没有影响?它是有用还是没有用?每一个有用或者没有用的结论在此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和论证,结论是比较确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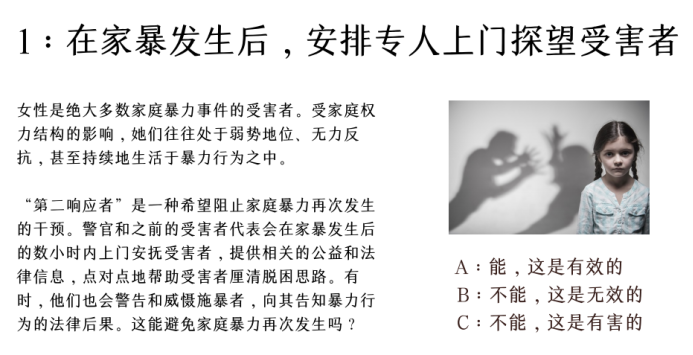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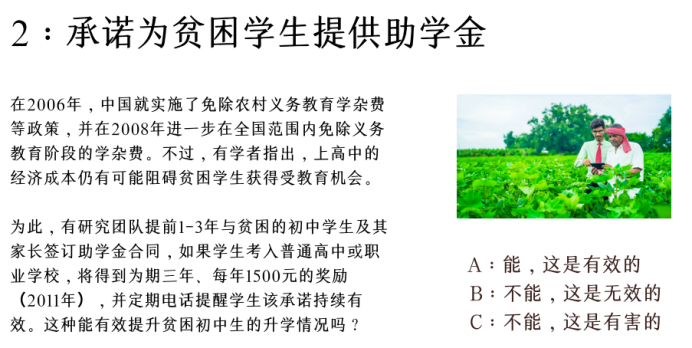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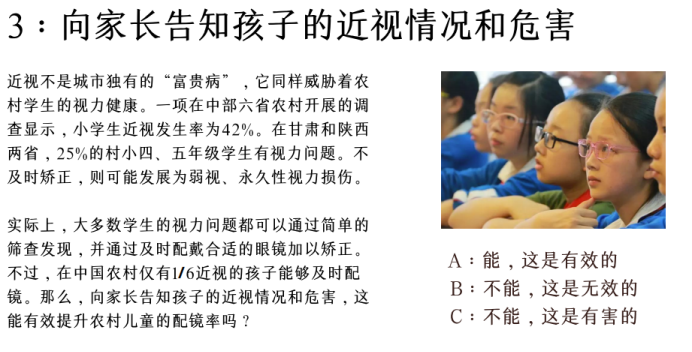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很遗憾的是,在家暴发生之后,安排专人上门探访,会持续造成家暴问题。但这个项目已经在美国和丹麦成为了国家推行的项目,结果发现这个项目不能降低家庭暴力行为的发生频率,但它确实增加了女性报警的频率。虽然报警频率高了,不代表每一次家暴的发生都被阻止了,而家暴的行为实际上变得更多。相对于对照组,参与该项目的女性再次被施暴的可能增加了1.7倍。这很可能是因为项目激怒了施暴者,有警察、志愿者代表去受害人家庭告诉施暴者这样做的后果,于是激怒了他、令他感到难堪,进一步恶化了家暴行为。
第二题,很遗憾,给贫困学生提供三年每年1500元的助学金,并没有显著改善他们的高中录取率。但它确实能增加贫困学生对上高中的期待,但对真实的学业表现没有任何影响。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点跟在国际上开展助学金有效性的研究实验是不符合的。
这背后有很多理论解释,比如说中国家庭对于孩子上学未来带来的财务回报的认识是非常清楚。大家都知道上学能改变命运、知识能改变命运,所以当你告诉他再多给你助学金,并不会形成有效的激励。这样的研究实验结论五年前可能就有了,但是在这之后还有多少个项目在这么做呢?如果这种项目最终确实没有帮助到贫困学生增加他们的高中学历,那其实这些钱很可能是被浪费了。
第三个问题,告诉家长孩子的近视危害是无效的。随机干预试验是我们研究一个真实的公益项目的有效性的非常好的标准。五个随机干预试验显示,告诉家长孩子的近视情况是并不能促成改变的,家长知道了之后,很可能因为不重视或者没有钱继续去忽视它。
但是什么是有效的呢?给孩子免费发眼镜,孩子可能会带个半个月就不带了。因为他们会觉得免费的东西不重要,或者认为看不清黑板也就那么回、家长也不会去持续督促。但是如果给家长发一折兑换券,他只要付10%的价格就能获得眼镜。他需要带着孩子去配镜店里配眼镜,家长会觉得这副眼镜是花了钱买的,是自己给我孩子配的,所以他不会不重视近视、会持续地去监督和激励他,因此能够增加孩子长期的眼镜佩戴率。
我们在设计这些项目的时候,需要考虑不同层面的激励。如果我们只是在项目设计上单纯地空想,那么也很难找到真正能够对远方的人产生影响的方式。只凭我们自己的直觉,我们很难知道什么东西有没有帮助到远方的人。
我刚刚举了非常多人类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认知上的缺陷和不够客观的地方。在生活、公益世界中也是一样,光靠想,不知道到底真的能对远方的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光凭直觉不行呢?这也是我们机构过去两年一直在倡导的。虽然说不能对中国公益的所有项目都有这么高的要求,但我觉得仍然值得讨论这个因果推断问题。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关于支教。支教了之后,孩子们的成绩提升了,那么孩子的成绩真的是支教带来的吗?有没有可能孩子这段时间家里营养变好了,有没有可能这段时间这个老师更认真负责,帮助他做的更好呢?我们实际无法把孩子成绩的提升归因到支教上。
第二个例子,假如我们在学校里办了一个诗歌社团、招收了很多学生来写诗。进行了长期的追踪,发现十年之后,这些学生非常有创造力、他们的收入翻了几番,似乎因为诗歌社团的培训,他们每个人未来都成为了在艺术上有更好的表现的人。但是这些孩子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当时在学校创办了一个非常好的诗歌社团,给大家赋予了充分的创造力吗?有没有可能当时愿意报名参加诗歌社团的孩子本身就是特别积极、特别开朗、特别愿意写诗、特别愿意创造的孩子呢?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归根到底到具体的某一件事情上。这在经济学上也非常有名叫survivorship bias,幸存者偏差。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在研究二战期间飞机被炮弹打到哪里最不容易坠毁时,研究者没有意识到坠毁的飞机根本没飞回来、没有办法被研究,这就是因果推断的问题。
幸存者偏差为什么在公益中重要?如果我们真的想对远方的生命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首先得确定我们真的能对他们产生影响。很有可能大部分的项目是没有对他们没有办法产生影响的。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经济学的工具,或者有更多监测、评估的意识。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先看看之前有没有相关研究去说明这件事的有效性,或者在整个项目的设计过程中要不断地去考虑是否需要试错、要不要随时根据我们现有的基础去做方法的调整。这都是非常现实的启示和建议。
但很显然,绝大多数中国公益项目都没有这么做,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我刚刚说了很多无效的东西。那什么东西是有效的呢?我简单举两个例子,是我们组织研究的一些成果,是我们觉得可以在中国公益界形成非常好效果的一些项目。这些很可能是一开始在考虑公益项目的时候你不会意识到,或者说不觉得这些事还需要我们公益人关注。做支教不就行了吗?
中国60岁至89岁人群的白内障发病率是80%。白内障是每个人老年都有可能会得的一种疾病,基本是年龄因素,和其它因素无关。白内障就是眼睛的晶状体变浑浊,手术非常简单,现在成熟的手术可能十分钟就能做好、把原本的晶状体换成人工的晶状体就好了。
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手术,在中国有多少人没有被矫正呢?中重度视力损失和失明的有1859万,理论患者更是过亿。但手术的成功率很高。公益组织资助一台手术成本1000元,算上筛查与来回路费两三千元。帮助一位失明患者重获光明,确实不是一个特别创新的公益机会,但它确实能够帮助有效地帮助远方的弱势群体,帮助一个失明的老人重新看见这个世界。
左边这张图,是中国白内障手术率的排名,我们是红色这条线、排在最下面,和发达国家差的很多,即便和印度、伊朗、巴西的差别都挺大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领域。
类似的问题在中国还有不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未必会想到吃盐过多是造成中国人死亡与残疾排名第三的原因。为什么呢?钠是人体必需的一种营养素,但钠摄入超标会增加一系列健康风险,尤其是高血压和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卒中等等。中国人的吃盐数量,在全世界也是很高的。我们每天可能要摄入11g盐左右,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盐的摄入量是5g,我们盐的摄入量是翻倍的,这也可能是因为大家还有“吃盐有力气”的传统认识。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办法,比如把家里的盐换成低钠盐,因为咸味不仅来自于钠,也来自于钾,可以把食盐中的钾的比例提高一点,平衡血液中的钠钾比,就可以显著地降低钠的摄入含量、极大地改善中国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钠摄入量过高的后果有多夸张呢?如果中国全部家庭都改成低钠盐,每年可以减少50万人死亡,这已经和全球每年疟疾造成的死亡可以相比。
我们看到也有许多有效的项目,但这些实验都是需要非常仔细地去做、去想,而不是觉得公益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我在这里就再开个脑洞。假设以下这两种情况,你有100%的几率挽救回500个早产儿的生命,或者有10%的几率挽回5000个早产儿的生命,你会选择哪个。
为什么我提这个问题呢?因为不是所有的慈善都是需要讲求证据的。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做这个事儿它是能够显著的改变世界,一旦成功了它就能够有非常好的成效。但是我们得接受它很高的失败比例。比如说,现在非常流行的给早产儿护理的一种方式叫袋鼠妈妈护理。早产儿出生之后,把ta放在母亲的身上、胸口前,给他提供温暖和轻抚。这个对于减少早产儿的死亡是非常有效。
第二种,我们假设就是你现在能够研制出一个神药,有百分之十的成功概率。很多药厂在这干这个事儿,比如说疟疾,青蒿素已经很有效了,但是如果研究出一款疟疾的疫苗,这个事儿就完全解决了。所以这两件事我们要怎么想?这也是我觉得对于慈善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要理性地考虑这个问题,就得考虑他的成果和几率。同样用一个在经济学上大家可能熟悉的概念叫expected value,预期价值是多少。比如说第一个可能就是100%×500,就是500。第二个是10%×5000,也等于500。并不是我们的所有决定都要这么去想,但是当我们面前真的摆着这样的问题,你需要选择投入的时候,很可能这就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而在这里产生了两种慈善的逻辑,一个叫循证慈善,一个叫打靶慈善。其实就是我们的方法论不同,这跟做投资也是一样的,你是想多投给这个b轮、c轮马上上市的稳定企业,还是做早期的风险投资。那为什么我们慈善不能这么想呢?我知道不是所有慈善都会这么做,但是慈善也可以很有意思,它也可以是很有创造性、很需要我们的思维逻辑的事情。我举两个例子。
比如左边这个金字塔,分析项目是否有效我们需要高等级的证据,而不是这个专家说有效这个事儿就有效。一个专家的观点基本上是最低等级的证据,谁说了什么一点用都没有,还是得有真实的证据,这也是循证慈善的思路。
右边有两个打靶式慈善非常好的例子,上面这个叫帕格沃什会议。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因为时刻有爆发核战争的风险,慈善家就资助了两国的核物理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每年在帕格沃什会面去讨论如何减少核战争的风险和毁灭全球人类的核战的发生。最终发现,帕格沃什会议在帮助两国政要在一些关键时刻减少误判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笔钱很可能就避免我们人类因为核战走向毁灭。这个世界仍然面临着这样的风险,包括气候变化,如果我们真的面临一些极端的气候变化的场景,我们有没有好的技术能够去避免全球极端升温的情况出现?这个不一定要捐赠,进行有效的投资也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它也是广义上的公益。
下面也是一个打靶式慈善的案例,叫绿色革命,是早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上世纪60年代左右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粮食增产。当然这里背后也有一些冷战的政治上的考虑,但至少从客观结论来看,它确实帮全球各个发展中国家显著提高了粮食产量,并且最后绿色革命被广泛认为避免了数亿人因为饥荒而死亡。所以我认为慈善家在一些关键时刻进行有远见的资助,很可能会在世界历史上发挥一些重大的作用,这些事未必我们都知道。所以不要小看慈善的力量。如果慈善做得很好,它不比投资要无聊,也可以发挥非常大的影响。
大家可以看到我都非常强调一件事的后果,这在伦理学上也是非常著名的,叫后果主义。我们主张一件事是好是坏的最好的判断标准,就是它带来的结果到底怎么样。比如说自然界中的美固然应该保护,但我可能认为使人类的生命变得更好是一件更有价值的事情。这也掺杂了福祉主义,就是在对于什么东西有价值上做了一个预判,即生命的福祉是最重要的。如果把后果主义跟福祉主义加起来就叫效用主义,很多人也听说叫功利主义,但我认为功利主义是一个不合适的翻译。功利这个词在中国有挺多负面的意义,一听到好像觉得这个人很功利、他就是一个不关心时事只想赚钱的人。所以现在很多人就从经济学、商业世界借用“效用”这个词,所以这可能是我认为更合适的搭配。那效用主义意味着判断我们一件事做得对或者错的核心标准是我们能否给别人生命带来好的影响。我认为效用主义和后果主义的思路在中国的伦理学界和日常道德生活中是被大大低估和污名化的。
为什么我认为后果是需要关心的事呢?尤其是在帮助他人这件事情上,它可能不仅仅关乎到你自己的选择。如果你觉得这个事只是你自己的选择,我可以选择优化后果、我可以选择不优化后果。这对于后果主义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挽救一个本可以被挽救的生命是一件不善的事情。同理就是,你路过一个池塘时没有救落水的孩童和你造成了他的死亡,在后果主义者看来是一致的。
这个理论肯定有很多问题,但它的重要性在公益这件事上尤其突出。如果我们的资源本可以被用来,比如说,改善中国农村孩子的进食情况、改善中国农村老年人吃盐过多的情况、做更多的白内障手术、减少更多的早产儿死亡、给远方的生命捐去更多的防疟疾的蚊帐。如果这些钱本可以发挥这个作用,那些可避免的死亡就真正可避免,而不是永远成为一个“可避免的死亡”被列在我们这种PPT上。我们在公益领域的钱跟政府、跟公司比起来是差得非常远的,如果在这件事上我们不去尝试让我们的钱花得更有效,其实我们可能是在辜负非常多的弱势群体。我们再回到机会成本这个概念,在此巨量的机会成本是由弱势群体去承担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把这笔钱花好,因而他们失去了被挽救和被帮助的机会。
最后,让我们来谈一谈,这些有关公益的玄思和我们自己的关系。尤其是,哪些事情是我们分内的事,哪些事情是分外的事?这就是所谓的义务和超义务的区别。分内,其实就是你应该做、你没做到我就要谴责你;分外,没做到那是你的本分、你做到了我会表扬你。这就是义务与超义务的问题。公益,或者说我们有一定的收入就去进行捐赠这件事,它究竟是一种义务还是超义务的行为呢?有两种可能的路径去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逻辑,也是彼得·辛格的观点,就是应救则救,因为你能救、所以你该救,这个是很简单的逻辑。第二个逻辑,我觉得还是要考虑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的情况,就是我们究竟占据了这个社会多少的资源。不仅是我自己,在座的各位能在复旦参与这个讲座,或许我们都应该想一下这个问题。你是精英吗?如果大家觉得你是这个社会上的精英,有同学愿意举手吗?很少,我特别理解。如果别人这么猛然问我,我也不承认,好像显得自己特别的自大。但是请大家扫这个码,这是在2020年99公益日的时候我们做的东西,叫“影响力计算器”。扫了之后,你可以输入你的收入、或者预计自己毕业之后令自己满意的薪资收入是多少?
扫出来之后的结果,至少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震撼的。我没有想到我做公益赚这么点钱就已经是全球全中国最有钱的那批人之一了。同理,我们看右边这张图,这个是Giving what we can,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公益组织网站。他们做了How rich a man is,在全球范围内你是多有钱的一个人。我来之前搜了一下复旦大学毕业生的年平均收入,每月是11000,那假设没有年终奖,就是132000元。数据显示,如果你一年赚人民币132000元,你就是全球最有钱的3%,你比全球97%的人都有钱。你的收入是全球中位数的13.2倍。
接下来,我们算一下随机出生在中国的青年考上一本的概率。这个是我们在最近发的教育报告里简单算的,我们找了每个阶段最靠谱的一个数据,最后算出来6.52%,意味着如果你在中国考上一本,你是同龄人中的百分之前6%、比94%的人的学历水平还要好。我知道我们现在就业中会有很多鄙视链,TOP3、C9、985、211,但是我们得意识到有沉默的大多数还在我们背后。我不是说一定要上名校才能有光明的未来。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在的社会,学历对于一个人未来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影响是非常相关,而收入又影响他的健康、他活得好不好、他能不能救得起病、吃得起药等等。教育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未来和我们自己生命的体验。
我们说了收入问题、教育问题。我们可能不想承认自己是精英,因为精英这个词有些被污名化了。但是如果我们回望那些在成长过程里被我们落下了、或者是由于没有我们所拥有的条件而被不平等伤害着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国家是广泛存在的。
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理论是反后果主义和效用主义的,他认为正义不应该是最大化的所有人的福祉,而是让我们相对来说达到公平。他提出了“无知之幕”原则,假设这个社会我们所有人在不知道自己会投胎到哪一个物种、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地方,你会希望社会制度怎么建立。他觉得除了我们基础的人权和自由需要得到保障之外,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被不平等伤害的人应该是整个社会资源投入最多的一个方向(“正义的两个原则”)。
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怪罪于这些人不努力、或者是他考试过程中没有用合适的方法学习。社会结构性不平等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不应该从弱势群体的身上再去找原因、去苛求一个完美的受害者,而是应该去想我们作为既得利益者能做什么。那如何让“运气”的成分在这个社会里被减少得更多?让每个人有效的付出和他最后达到的情况能有等比例的、相对的平衡,我觉得是每个处在优势地位的人应该考虑的事情。我也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去做公益的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不要在一个特别卷的社会里去往“人上人”的位置上去卷,而是去想你比你穷的95%的人、比你学历差的95%的人,他们怎么能过得更好一点?如果这么想,其实公益领域特别需要人才,这里一点都不卷,非常需要各位来卷一卷让我们把事情做的更好。
回到开头论述里,还有一件事儿没说。彼得·辛格说“不需要牺牲同等的道德权重”,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从后果主义的立场来说,彼得·辛格的意思是,只有当我们的损失重要到能够与其产生的收益相提并论时,捐赠的行为才能够停止。人话版本就是:当我们下一笔钱捐出去之后、我们和全世界最弱势的那个人的处境相类似了,我们的道德义务才结束。讲白了就是你得捐的倾家荡产,你得接受苦行的生活,你的道德义务才算完成、才算没有做坏事儿。
当然他这个要求太高了,但是我认为对待一个过高的要求的时候,我们能有两种态度:一个是想方设法去辩倒他。第二个逻辑就是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意识到我们尽到各自道德义务的世界是个特别美好的世界,但是由于我自己的软弱,我不敢去承担我该有的责任,从而去反思自己。
我现在每年大概捐出我收入的10%,捐了之后我也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类似的立场并不罕见。比如说基督教的十一税,教徒的10%的收入需要捐给教堂支持教会的运营。什叶派的穆斯林甚至要捐收入的25%去支持这个清真寺的和伊斯兰教会。就像拉丁教父圣安波罗修(Sanctus Ambrosius)说:“你扣留下来的面包是属于饥饿者的,你储藏的衣物是属于衣不蔽体者的。而你埋藏的钱财是用来救赎、解放身无分文者。”同样,在佛教里也有类似的说法,“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就是说你跟这个人没有缘分、你依然对他有非常强的慈悲心;“同体大悲”就是他发生了特别大的苦难,你能感受到他发生的苦难就像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一样。
虽然辛格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放眼全球其他宗教对教徒的要求、或者把它当成某种更高的道德理想,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情。
现在也有非常多的组织在做这样的事情。比如我提到了Giving what we can,他们在全球号召有钱的人去把至少10%的收入捐出来的组织。
最后,我想以我最近几年最喜欢的一篇博客文章来结束本次讲座。牛津大学有一个智库叫our world in data,他们用数据去追踪这个世界上所有关键的问题。他们的创始人Max Roser在一篇文章里陈述了三个结论,对我认识公益、认识这个世界非常有启发。
第一个,今天的世界还很糟糕。比如每年过早死亡的儿童数量是520万。第二个,今天的世界比过去更好。就全球儿童死亡率在19世纪大约是43%,至今已经下到3.8%,如果今天保持像过去一样的儿童死亡率,每会年有6000万儿童死亡,而现在是520万,已经有了巨量减少。由于我们的卫生医疗技术提高、经济的发展,这个社会已经显著地变得更加公平、我们有更多的能力去帮助远方的人。第三个,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我们知道降低儿童死亡率是可能的。如今欧盟地区的死亡率是0.4%,如果全球儿童健康率能够与欧盟相同,死亡人数就可以下降到54万,每年有将近500万的孩子就不会死了。他们能够有更长远的未来、有自己的快乐,他们的家庭也不用承担这种丧子之苦。
总而言之,世界仍然很糟糕;但已经比过去好得多;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这三个结论同时成立。但是往往我们在思考公益和世界时只看到其中一个结论,并且因为别人只说了一个结论就去攻击他们。但是意识到这三个结论同时成立特别重要,我们也就意识到这个世界仍然有非常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但过去也有非常多的人已经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尝试让它变得更好。未来这个担子可能在我们身上,需要我们继续接棒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因为我们自己做公益,我知道公益领域又是一个既缺钱又缺人的领域。疫情三年,无论是对我们组织、还是对整个中国公益来说都造成了挺大的负面影响。但是我还是想用马克思·韦伯在“以政治为志业”的演讲的末尾说的话来结尾。
他说:“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的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他们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然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说他担起了一份政治的‘使命’。”我认为政治这件事换到行善和公益上依旧成立,我们能在做的过程中感受到非常多的困难,但是只有能够自信地说着“等着瞧吧”,这个世界就依然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变得更好。无论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坚持担起一份行善和公益的使命,也就可以说是担起了一份精英的使命。
讨论&提问
01 主持人:我相信大家在这边肯定还会有很多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对之前接触已经有一些了,我可能我自己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就在这里先问治霖一个对我来说非常切身的问题来抛砖引玉一下。
我在读了治霖的文章、听了“脆弱世界”播客、了解了这个领域的公益之后,我发现一个应该说是特别难的问题,也可能是所有人都面对的问题。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从理论上质疑Peter Singer的前提,我去认真的阅读了他那篇论文、没有觉得他的论述里面有什么问题的地方,那么我理所应当的应该要接受他的结论。
但是每年捐出多少钱的收入、或者考虑动物福祉,我相信对每个人来说做出这样的选择,这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现在面临很多问题,我也经常跟大家会讨论我们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但是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大家可能普遍对这些问题反而没有以前关心了。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或许是意识到自己有责任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本身是件相当有痛苦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去做,但是告诉别人你应该怎么做,一方面既有道德上居高临下的嫌疑,另一方面就像鲁迅说的那样,如果告诉别人这些你做的还不够、你要多做一点,他们就会觉得非常痛苦。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治霖您作为有效利他主义的践行者,会怎么样面对这样的问题?
治霖:你说的话里,我觉得有两点对我自己特别有启发。
第一个就是我认为任何一种理论想做到知行合一都极其困难,但是做不到知行合一,不构成对这个理论本身的挑战。反而很可能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做的不够,或者让我们不断去反思。
第二个是对我自己特别重要的一点,比如说我认为我现在我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或者是我可以选择少食用动物性的产品,可能是比较正常的。我们得意识到比如说有非常多劳动者,他们不可能做到不食用。肉类很多时候是贫困地区人们主要消费的食品,但我们不应该去苛责他们。一个人能够拥有多高的道德标准,做出一些符合理论判断的事情本身也是一种优势,是一种你需要去反思的优势地位。
所以我认为我有这样的优势地位,但我不应该以此去抨击那些由于没有我这样的运气能认可这种理论的那些人。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这么做,他很可能完全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去这么做,而我也是极其幸运地有条件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不认为这一套理论在这个阶段适用于去提供除了律己之外非常强的一个律他的倾向。我自己也不是一步到位,如果我真的完全践行这些理论,我现在可能要把我的至少一半以上收入都全部捐出去,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过程,比如说Peter Singer,他也不会出去跟别人说你要把所有钱都捐出来,会说我们先捐10%。为什么呢?捐10%你比较可能接受,可以慢慢试,然后对你生活没有影响那么大、你会愿意慢慢捐得更多,这是理念层面和行动层面以后果为导向的一种策略。
02 提问人:假设我是一个要先为自己考虑生存发展需要的人,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以公益为志业,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到公益职业里面去。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事业、志业、职业在英文的表述里面,或者在我们中国的语境表达里面,它是完全一样的吗?它有什么不一样是可以带到今天这个话题里面来的?
治霖:我也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我也在自己寻找答案过程中,所以说不要把我的建议当成建议,我只能说我有一些非常粗浅的想法。
首先职业、志业、事业的区别中,志业是有点不接地气的表达,我觉得也是因为马克思·韦伯的三篇演讲,所以变得很火的,其实我们日常用的人不多。我们好像经常会说职业就是你不得不去做的谋生的事情,事业好像是你自己创了个业、或者你有一件特别想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人有自己的事业,但我觉得志业这件事情本身是有一定公共性的。
当我在说人以什么为志业的时候,无论是以学术、政治等等,我觉得是有一定公共性和公共取向的,因为这个事我需要创造一定的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而且志业很可能拢括了事业和职业。至少我看到很多人上现在社会上的精英,他可能是没有自己的志业,但有自己的事业和职业。
第二个我可能借这个机会说清楚,不一定非要进入公益界才是在做公益,公共利益在各个事情上都可以被实现。比如你去拼多多这样一家公司,你在里面帮他们的算法改进得稍微好一些、帮助他们增加社会伦理方面得考虑,这很可能就是非常具有公共利益的一件事情。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枪口抬高一寸也是一件非常具有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的事情。
更简单一点就是我认为公益作为一种职业在这个社会上很可能会持续作为一种小众的状态,大多数的资源还是在商业世界里、在政府的领域中,所以我认为其实可能真正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的时间还是需要在更有资源的地方,才能够真正去为我们想做的世界提供更多的改变。
我们在一些关键的政策岗位上去促进一项有利于民生的事业得到更多落实,这是一件公益事业。所以我并不认为一定要把选择公益行业作为职业,但是我不得不说在别的行业里做这些事会有非常多身不由己的选择,尤其是有额外的目标在驱使和指使着我们的时候,有时候就需要面临道德困境、需要做出一些选择,所以我在公益这个行业它压力小一点,能够更本真的去进行一些表达和创造,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留在这,我觉得这里有空间。但如果更多的大学生,像复旦这种学校的毕业生,大家能够多去想这些问题,我觉得很难说我们未来这个社会不会在根本上有所变化。
03 提问人:治霖你好,我想问一个比较贴近我们生活的问题。其实大家都是有意愿去做公益的行动,但其实真正的问题是缺少这个途径去让我们关注到这些项目,那么更看不见那些远方的人。我也刚才翻阅了一下益盒的公众号,里面说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是直接捐钱,但我们其实缺少一个有效的、透明的、值得我们信任的渠道去捐钱,或者说这种渠道已经存在,但是公众其实不太了解,这中间的一个断层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
同时我又联想到还有两件事情,首先是我们系里也在组织结对和宁夏的小朋友的书信活动,主要就是给他们写一些激励的话、然后我们也加了相互的联系方式,我在思考这样子的行为是不是真的能够鼓励到他们,或者说这种鼓励其实是无效的。然后我自己也在一个支教的社团里面,我们社团以前会写明信片给这些山区孩子们,但是我也在思考它的效果问题,它为了鼓励大家放出一些奖品作为激励,然后这些奖品的经济价值其实蛮大的,如果用给大家参与的激励上、然后大家写了一些也许其实并没有用的明信片给那些山区的孩子们,这样是不是一种自娱自乐的公益行为。
治霖:很感谢你的问题,我觉得能进行这样的反思,我觉得已经特别好,很感谢你坦诚的分享。
首先写信这个事你先别太悲观,你去看看有个广州叫“蓝信封”的公益组织,他们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评估研究,还有一个“广东日慈公益基金会”,这两个组织应该是做书信的教育陪伴,我印象里他们挺注重评估结论的。
然后对于你说的信息缺乏的问题,首先直接捐钱这个事儿,很遗憾说中国没有合适的渠道,但国际上有很多,我推荐一个组织叫give directly,如果你有国际的信用卡,需要给非洲捐钱,他们做得特别有效,可以直接给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户家庭转让,你每捐一美元应该有0.85美元就进对方的账了,因为0.15是有过程的手续费、组织运费等等一些很合理的费用,0.85这个比例是很高的。他们就专门去做全程披露,你甚至能在他的公众网站上看到每一个家庭谁申请这笔钱、用来做什么。
我觉得值得提一下的是直接的现金捐赠,在国际发展领域是被广受认可的、最有效的帮助别人脱贫的方式。这跟我们通常认识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完全不一样,所以还是那句话,你光凭想象很难知道什么有用、有什么没用,你总想着说是穷人会拿着钱去*的,那是个万里挑一的个例,大家只有自己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把它做成好事需要克服这样的认识。
但是你说的靠谱捐的渠道,国内还是有挺多靠谱的渠道可以捐,这也就是益盒在做的事情,我们希望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渠道和信息。
最后你问支教这件事是不是自娱自乐?我不觉得是这样的,当然我今天说了一些支教的“坏话”,但是我自己最开始也在大学做支教做了一年多,我觉得不应该否认的一点就是我们带去给孩子的东西很可能真的不比孩子带给我们的多,而我们应该为孩子给我们带来了好的东西而感到羞愧吗?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我觉得我们正是因此对利他有了更好的认识,并且不断反思到新的问题。
未来也许通过这样的经历,我们有更多的反思,我们能做更好的事情,这个善意通过孩子传达到我们自己身上,而我们借助自己的资源和能力把它放大、再去回馈给更多的人,其实不就是执教的一个重大意义吗?就像我知道很多朋友在联合国出来之后继续做公益,或者是在乡村教育行业做出了非常多的好事情,所以我认为它通过一种放大器的作用,让更多有资源有能力有想法的年轻人能在路上走更远、有更多的反思,这其实本身从结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04 提问人:我们的企业每年都会有一定固定的发展资金,可以去分配给不同的慈善公益项目,听了你刚才的发言以后,我在想如何去选择要去支持的议题。当你有有限的资源、有限的预算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主要是教育方面的支持工作,当比如说有疟疾的儿童还存在的时候、或者说还有儿童因为营养不良有各种健康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优先去选择健康、医疗方面的项目。
当我们选择好一个议题、一个方向之后,有没有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在看项目和在看公益基金会的时候,有哪些哪些公开渠道的信息是你会主要去用来衡量一个项目的可靠性,比如一些刚开始的项目可能不一定有长期的数据,你是怎么去看这种项目的reliability。
治霖:我们可以过会私下再交流一下,公开来说的话,因为益盒的立场是impartial(不偏不倚)地去选择一个议题,根据比如说后果主义立场,这个事能我额外的钱进去能够产生多大的价值,这个要求是挺高的。所以我认为可能在公司有一些大的金主、有自己比较强的兴趣的时候,我觉得贴合他们的兴趣去在兴趣范围内去增加他捐赠的有效性其实也很重要,因为要不然你要求说除了这些议题其他的就别捐、他就不捐了,你最后反而变成什么事都没做出来,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有效性和最后能够促成这笔钱怎么流动这个事情结合起来。
第二个我稍微提供一点,我们益盒在做筛选时的方法论,比如说议题问题,我们怎么做的。我们有三个原则:第一个,议题影响多少人,大规模地影响人的议题还存在就证明它仍然大有可为,非常值得投入;第二个是它有多被忽略,比如说政府、公司在这里投的钱有多少,投得越多,你额外创造价值的可能性越低,也是投资很著名的理论,你越早进入、带来的成效可能越大;第三个就是可解决性,这个事儿有多好解决,如果这是个无解的问题,尤其在公益资源这么有限的话,你不能当风投一样不断去投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找出明确的可解决方案的问题。这三者都满足,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合适的议题。
如果采用一个更中立的判断方式的话,在公益组织的方向上我们的框架是这样的:首先它需要有效性的证据,比如说有没有我刚刚说的那些学术干预去说明了这件事情的可靠程度。第二个是组织有没有好的监测评估的流程,如果没有、如果他们自己也不注重成果的改善, what is not measured cannot be improved,如果这个东西没有被测量就很难被提高了。第三个就是它的成本效益,当然我今天就着重说我们钱花的多有效才算有效。第四个,就是它的透明度,他有多愿意去跟公众、跟我们这样的评估团队去分享交流信息,它越公开越透明,对捐赠人对负责,对我们所有人负责,它很可能就把这笔钱花得更好.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