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5-06
2023-05-06
 728
728我在2015年写的短文中,曾经提到公益组织专业化的重要意义,公益行为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的自发性行为,是社会的自组织行为,比如自然灾难发生时,人们会自发组织去赈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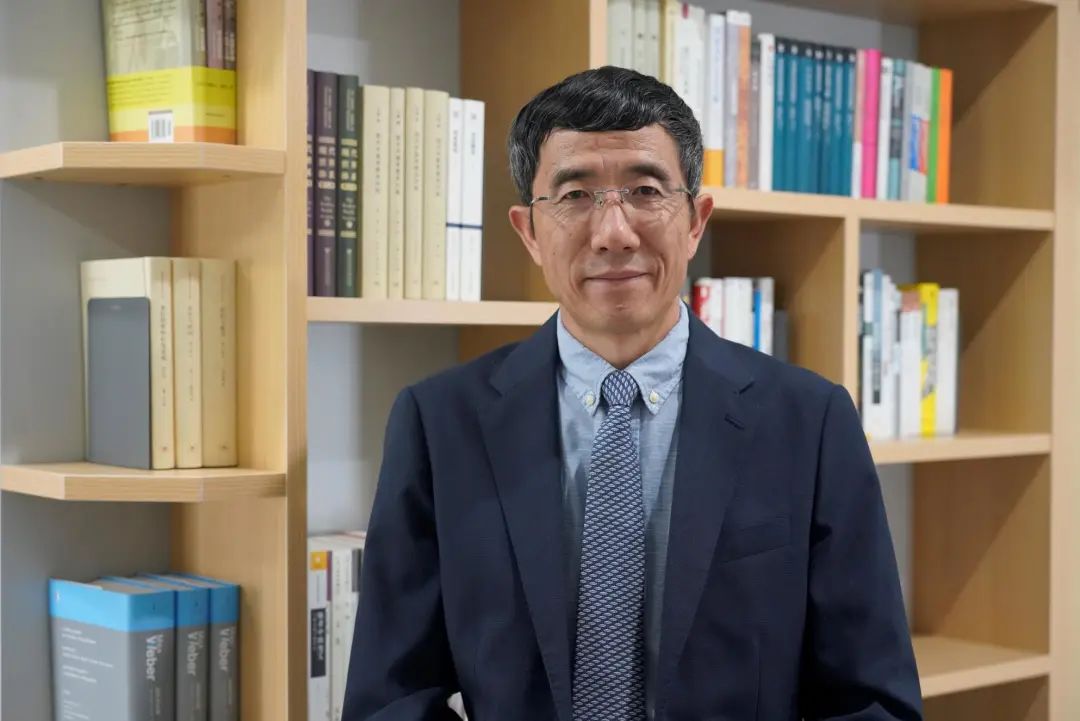
我曾经见到路边发生了车祸,很多人自发围拢过来,其中一个有领导力的人会指挥谁去打电话,谁来救助伤者,大家也都很听他的。虽然这样的行为也只持续了不到一小时,但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公益行为社会自组织的属性。
当公益行为规模变大并成为持久的行为,特别是涉及资助行为受资助行为的时候,就无法仅仅依靠短期的自组织行为来实现公益资源的统筹分配,当公益成为一个行业的时候,专业化的公益组织也就成为公益发展的必然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公益组织的专业化是无可非议的。
学者们对公益组织存在的价值、公益组织的管理等问题有众多的论述,在此不再赞述。我觉得,无论是传统的慈善还是现代的公益,它们的实质是“辅助性的社会正义与公平”(社会正义和公平不能会依靠公益来实现),核心是捐助者和被捐助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捐助者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当向社会无偿指助社会稀缺资源的时候,都会自然产生道德优越感。这种道德优越感也很容易演化成影响甚至操纵捐助议程的权力,这种权力有时候是直接的,有时候是间接的。而被捐助者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容易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在道德优越感和操纵性权力面前,容易产生弱势的屈辱感。“人穷志短”,弱者的选择一般都是接受,但是弱势下的无助和屈辱感会导致心理逆向反弹。这也就是很多人常常会遇到那些所谓“不感恩行为”的社会心理原因。
公益不同于市场行为,公益过程中流动的钱和物承载着情感、道德和权力等复杂的社会心理要素。当捐助者和被捐助者处于最近距离的时候,道德优越感和弱势的屈辱感之间就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张力,从而消解慈善公益的正能量。这也是我对陈光标慈善善举有所保留的主要原因。我绝不反对和质疑他的慈善动机和慈善精神,我主要是想说这种行为的慈善效果,我也不是特别赞赏带着很多旧衣服送到贫困地区的做法,因为捐助者觉得自己很辛苦还得花钱洗干净寄过去,而被捐助者可能觉得你把自己不用的东西处理给他们,怎么不把自己现在用的东西寄给他们呢?你希望他们感恩,而他们觉得替你处理了不要的东西,你应该感谢他们,所以慈善公益之间物化品的流动所引发的这些外部性的确值得思考。
慈善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这些都有过深入研究,我认为,在捐助者和被捐助者之间要有一个缓冲性的制度安排,这个缓冲性的制度安排就是公益组织。公益组织阻止了公益界捐助者和被捐助者的直接接触,打断了构建道德优越感和弱势屈辱感的信息链条。
一方面,严格意义上的公益组织作为一个中性的形态,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将捐助者的资源转化成各种各样的公益项目,在公益项目中并不能看到捐助者提供了多少钱,从而有效地稀释了捐助者的德优越感;另一方面,公益组织通过其专业化的过程,将被捐助者需求转化成所谓的公益项目,这样也就消除了产生屈辱感的社会心因素,被捐助者更多地被看作公益项目的参与方和受益者,而不是传统慈善行动中简单地接受援助方。由此可见,公益组织对于公益事业的发展是意义非常大的。
对公益组织的专业化,我一方面觉得非常的重要,另一方面也保持一定的警觉。这就是我讲的那种说不清的纠结或者是理不清的自相矛盾。为什么呢?公益界过去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乱象,大家都把这些归结于监管不严或者社会道德紊乱。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导致公益伦理紊乱的重要原因。但是,公益组织一旦专业化以后,就一定会涉及专门的人员;有了专门的人员,机构内部就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功能;有了功能后,公益组织就成了一个从事公益工作的机器。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机器不是一个机械的机器,而是一个社会的机器,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这些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技能和不同的预期,他们在公益的机器中不是一个“道德统一”的公益人。我们之所以常常对公益界出现的各种不道德行为表示惊讶,是因为我们把公益组织假设成了圣殿,可能把公益人也假设成了圣人。
事实上,公益组织比任何其他组织都更容易产生人格化的负面影响。由于我们都倾向于把公益视为一个神圣的事业,我们也容易把进入公益组织的人看作“好人”,所以我们也往往都不会在公益组织中对人和事保持那样高度的警觉。道德尺度在公益组织和市场公司中有所不同,这就是公益组织化和专业化产生人格化的潜在负外部性。
不仅如此,我对公益组织专业化所产生的公益异化的警惕,还来自公益组织专业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消化和吸收非道德的行为,很多人在公益行业中谋求私利就是很好的证明。公益组织的专业化势必需要数量庞大的人力资源,有时不得不容忍其中很多非道德的行为,如果这些行为逐渐沉淀成普遍现象,就会侵蚀公益的价值。这些都是公益社会道德失范的社会原因。公益组织的社会过滤器作用与公益组纽本身的异化使得我对公益组织专业化产生了很深的纠结心理。
公益的本质是辅助性的社会正义和公平,因此公益必然是道德取向的。但是,公益人无法绝对道德化,对于公益人的道德要求必须是相对的,否则无法维系公益的道德取向。
西方公益行业的工资不算高,有人问,为什么他们工资不高还很少有乱七八糟关于“钱”的事。首先,西方公益行业的工资处于平均水平之上,而且西方就业相当稀缺,也没有一夜致富的社会条件,因此,获得一份工作相当不容易。我们的情况是,就业还没那样的稀缺,很多人都通过各种渠道致富,人们就业的收入或福利预期都比较高,如果公益行业不能提供合理的福利,就无法获得满意的工作人员,另外也容易使公益组织的管理陷入复杂和高成本的境地。承认公益人是“人”,给予他们合理甚至高的福利恰恰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为公益服务,恰恰能有效地维护公益的道德取向。
这里我并非强调高薪养廉的老调,而是想说不能因为公益是神圣的事业,就要求从事公益的人是圣人。只有把公益人首先看成是普通的人,并予以相应的福利待遇时,才能要求他们做一个符合公益的“道德人”,我想这就是徐永光说的“去道德化”。我不认为公益应该去道德化,但我认为公益组织应该去道德化。公益组织的人格化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符合实际的福利制度,公益组织必将产生异化,这对于社会来说是一大悲剧。
当然,我也不认为一个合理的甚至高的福利待遇就能阻止公益组织的异化,社会的总体价值、职业道德和有效监管都是重要的条件,公益制度安排则是重要的基础。一个发育完善的公益制度不仅在于工资和福利,也在于公益文化,还在于公益人的就业安全感和幸福感等。公益组织化和专业化以后存在因人格化造成的潜在的道德风险,我们不能把公益组织看作圣殿,也不能把公益人视为圣人,除去伪道德的包装,正视组织化和专业化产生的潜在问题,公益事业的神圣才能得以维护。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