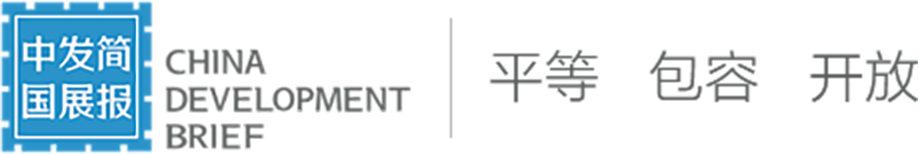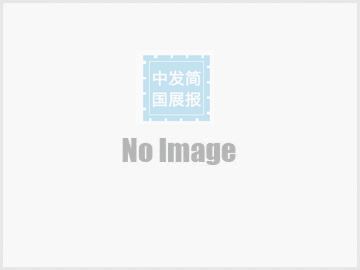2022-08-01
2022-08-01
 206
206前 言
欢迎各位来到第十期的益盒对话笔记。在这里,我们将呈现原汁原味的研究对话,让你身临其境,旁听我们与业内专家对话,看到公益内情,成为更理性的公益人。本期对话的受访者是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自然之友理事张伯驹。
自然之友成立于1993年,是中国成立最早的环保社会组织之一,致力于通过环境教育、生态社区、公众参与、法律行动以及政策倡导等方式促进中国的环境改善,支持更多的绿色公民真心实意、身体力行的行动。张伯驹在学生时代就参与自然之友的志愿活动,后逐渐成长为机构负责人。他从2006年开始在自然之友专职工作,在2013年8月到2021年7月担任自然之友总干事,任期届满后转任理事,并于2021年12月加入银杏担任秘书长。银杏成立于2015年,由数家基金会共同发起,希望通过支持具有社会创业家精神的青年行动者,积极回应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
在自然之友任职期间,伯驹参与了超过50部生态环境和气候能源相关议题公共政策的制定和修订,包括《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参与了长江经济带总体规划、环境保护与能源等领域的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等一系列规划和决策;推动提交数十份人大议案、建议及政协提案;并作为原告发起50宗环境公益诉讼。此外,他还是“中国零废弃公益联盟”的联合创始人以及《中国环境绿皮书》的编委之一。在本期对话中,我们系统性地回顾了他这些年来深度参与环境公益及政策倡导的得与失,并进一步探讨了他希望在新的岗位上探索中国公益协同行动的愿景。
在中国公益领域中,环境保护一直以来都是紧迫而困难的那块“硬骨头”。在探索中国环境问题解决之道的过程中,张伯驹及其在自然之友的同僚逐步建立了民间力量通过推动立法,撬动整体改变的工作方法。正如他在本次访谈中分享的那样,推动法律变化是路径,政策倡导的最终目的是“有效落实”。公益组织不应止步于政策倡导过程中的政策文本变化,也应持续参与、监督公共政策的落实,协同构建有效、透明的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公益行业生态。
时间
2022年3月10日
方式
线下采访
受访者
张伯驹
银杏基金会秘书长、自然之友理事
主题
政策倡导 动物保护 环境保护
从博物爱好者到环境公益从业者
益盒:您是如何参与到环境保护、动物保护的公益事业中来的?
张伯驹:“ 我小时候是比较典型的“植物人”,最开始只是单纯比较喜欢植物,对包括植物分类在内的整个领域都很感兴趣,但并没有“保护”意识。那时我会到各地去看喜欢的植物,比如听说京郊有一棵野生猕猴桃树,可能会爬很久的山去看,看完就很满足地走了。之后我因喜欢植物而进入自然领域,而该领域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或受到威胁,于是开始了解有关自然保护的相关议题。
热衷“自然”和热衷“自然保护”并不完全一样。有一些人可能是博物爱好者,但却不一定是环境保护者。我是一步步从喜欢植物,到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再往深处看到植物和动物的问题、生态和污染的问题,之后则进一步关注有关气候和能源的问题。这也是不少自然爱好者逐渐成为保护行动者的路径。”
益盒:目前您最关注的公共议题有哪些?
张伯驹:“ 在气候-环境领域中最关注的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一系列气候适应问题 [1] 。我从2007年开始关注此类问题,也和一些同行编写气候适应相关的案例和报告,当时“适应”在气候变化领域是一个不那么受重视的议题。但最近几年,特别是在一系列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发生后,我能明显感受到该议题变得更受重视。不过相比温室气体减排而言,全社会真实的投入和有效的行动还是比较少。气候适应是我关注的一个方向,我也在努力寻找更多有效行动的可能与空间。
[1]编者注:气候适应(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在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日益增长的背景下被提出,泛指适应当前或预期的气候变化影响的过程。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8/02/WGIIAR5-AnnexII_FINAL.pdf

图注:随着海洋变暖和过度捕捞的压力,基里巴斯的社区成员正在学习如何管理鱼类种群,使其保持稳定或得以再生。图源「联合国气候变化适应策略」
其次是环境法治的建设,包括中国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环境司法、原住民权利、野生动植物权利等等。此外,从公共政策的方向去考虑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在内)问题,也是我关注的方向。
在现在银杏的工作中,我投入较多的是支持公益人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探索公益机构协同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我希望能够有机会支持公益行动者找到基于真实且持久的社会问题的协同出发点,并且不断提升协同行动的有效性。”
益盒:我们了解到您曾创建过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在您的观察中,环境领域内不同行动者进行协同,各自的角色定位应该是什么?
张伯驹:“ 自然之友作为一家专注于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的组织,有比较专注的行动领域,核心是力争通过行动影响公共政策,通过一手材料并结合专题研究对公共政策和立法工作产生影响,并以此扩大和保障公众参与的空间。所以必须有一线工作为核心支撑。
刚刚说到的“协同”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应对气候变化,很多人会认为这是环保组织的责任,但从国际层面看,多年前就专门提出过“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的概念,这一视角能让大家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一个渗透多领域、广泛影响包含弱势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的问题。
在面临气候变化问题时,可能女性受到更多的生计和生活压力、老人外出不便的情况会更严重、残障人士得到工作机会的权利会受限。因此某种程度上,关注乡村建设、城市社区发展、女性权益、残障或老人扶助的组织,恰恰更需要具备气候正义意识和气候适应的能力,这就是很重要的协同。

图注:25岁的瓦妮莎·纳卡特是非洲当地“崛起运动” 的创始人,她就气候危机及其与性别、种族之间的交叉关系发表了看法,特别是对非洲的妇女和女童的极大影响。图源「联合国-非洲振兴」
正如只靠做助老扶老组织根本无法回应所有的社会老龄化问题一样,单靠环保组织根本无法全面回应气候问题。尽管这里的“组织”并不单纯指环保公益组织,还包括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自然资源部等政府相关部门,但依然无法回应所有气候变化问题。
因此,我所认同的“协同”应该是更大格局的“协同”,其落脚点可能是民间组织,不必区分是社会企业还是其他公益组织,只要是使命驱动的行动者及其团队就行。大家尝试超越单个组织的利益格局,在共同努力下,找到各自的“生态位”,形成协同和策应,目标是长期、有效解决社会真问题。
益盒:比如在面对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时,我们可以共同描绘一幅路线图:银杏基金会在什么“生态位”?公益盒子又在什么“生态位”?如果还有一家做老龄服务的社会企业,它又在哪里?描绘出路线图后可以看到更多可能性。
张伯驹:就协同的过程来说,首先,这群人眼中有了一幅路线图,将能更清晰地看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其次,需要注意的是,有了图之后各个组织应进一步考虑能否实现各自“生态位”的有效发展,而不只是混在一起做事。正确的做法是分别提升益盒和银杏的能力,比如提升益盒在专业研究报告、影响大额捐赠人、资金导向等方面的能力,银杏提升串联社会创业家们的能力,而不是让益盒和银杏开展一个合资项目,那就把这个策略窄化了,不是协同而是直接合作;第三,这些社会力量需要不断回顾和复盘,看路线图的进展对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价值在哪里?是否缺少其他“生态位”?如果现阶段能找到,就去做动员和倡导,如果没有,那或许应该搜寻、培育或者孵化?这是我所理解的协同过程。”
益盒:您可以给我们举一个公益行业内已形成路线图、带来较好协同的例子吗?
张伯驹:“ 现阶段国内类似的情况比较少。比如壹基金的“救灾联盟”,但其更多是由很强的“骨干”(backbone)组织领头促成的。我参与组建的“中国零废弃联盟”,由几家领头的NGO制定路线图,相对而言更像协同案例。不过目前仍然是以环保组织为主导力量,多元化程度仍不够。

图注:2022年7月11-12日,济南市章丘区遭遇大暴雨。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伙伴潍坊市领航社会工作事务所、寒亭社区志愿者救援队,联合济南当地伙伴章丘区城际救援队共同开展行动。图源「壹基金」
我们在做研究和翻译工作时发现欧洲有一些可参照的案例。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欧洲不仅有环境组织的参与,也有人权类组织、发展型组织、法律类机构和一系列智库的支持,以及司法系统的引入,此外还包括宜家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不同机构和部门的加入,最终推动改变的发生。
如果不是今年欧洲发生了战争,荷兰应该是近期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明星国家”。一系列的气候诉讼在荷兰发生,虽然是司法领域主要发力,但各类组织都在其中各司其职,大家共享“图景”式的目标,这是理想化的状态。目前在国内首先需要组织大家彼此找到、共同练习,一步达成目标是不可能的。”
气候问题与中国公益视角下的动物保护
益盒:您提到气候灾难或气候适应,这不仅关于弱势群体,也关于生活在户外的动物们。在您看来,目前气候和环境领域的行动者们对动物议题有何关切?
张伯驹:“ 气候变化对动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想举一个例子,是关于野生动物的。2021年,自然之友和三江源地区的公益机构合作一个项目,是关于青藏高原雪线升高后、动物活动范围改变而引起的人兽冲突等问题的研究。从这个例子中看到的气候变化对野生动物的一种影响是生存范围的缩小或扩大。如果缩小,野生动物的生存机会就会变小,或适应时间不够。适应需要很长时间,在面临短期剧烈变化而适应不够时,种群可能会出问题。如果扩大,就可能产生人兽冲突问题。”
益盒:考虑到目前我国立法上没有将动物视作权利主体,在人兽冲突中,现实中的各方是怎么认识动物的地位与价值的?
张伯驹:“ 这个问题需要从社会整体环境加以把握,在我看来我国现在还处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阶段。
十几年前的北京动物园里,有些动物的介绍标牌上还写着:“肉可食用、毛可做衣服”等内容。当时我在读大学,为此当时的大学生们还做过更换标牌的倡导。
2003年的非典是重要的时间节点。非典(SARS)之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启动,2004年进行了第一次修订,此后又进行了三次修订。当年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时,很多人的思维还是将野生动物作为一种可食用、利用的资源,某种程度上来说,整体思路是打造一部“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以利用”的法律。这样一部以野生动物为代表的动物保护法的核心立法思想,肯定是在当时逐渐建立起来,能代表从国民到政府、立法体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此后,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有了长足的进展,方向是“打断”使用和利用野生动物的思路,因为它们不是商品。我们希望它们有更大的主体性,但不得不说,在目前这个阶段,谈动物福利、权利还差的很远。野生动物需要首先回归“不是资源/商品”,然后再确保人与野生动物“你有你的地,我有我的地,我们之间还有交界的地”。现在各地已出台了一些比较积极的政策,比如在一些自然保护地及其周边,狼吃了村民的羊,由国家提供补偿;村民攻击狼或受保护的动物还可能入刑,虽然量刑方面存在争议。不过,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入刑这件事已经是中国立法很大的进步了。

图注:三江源村民与野生动物的故事:当保护动物成为一种传统文化。图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公共政策和法律能发挥多大作用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实施。自然之友现任总干事刘金梅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让我印象很深:以机动车右拐不让行人这一问题为例,虽然交通法规将其定性为违章行为,扣3分还要罚款,却因为发生过于频繁而处罚轻微。几年前自杭州、上海等城市开展严格执法后,情况得以改观,现在杭州、上海等地的不少市民都以此作为城市文明的值得自豪之处。严格执法、有效落实法律政策,能把法律变成社会习惯,随后成为个人习惯。“红灯停、绿灯行”就是严格执法的例子,而非原生的社会惯习。以此类推,法律已有了一定进步,但人和动物关系的文明程度的提升还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严格地执行法律,并以此为基础再进步。不过要推行类似于欧洲的动物福利和权利法律,我们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要走。”
益盒:您认为现在的公益组织可以考虑在野生动物保护框架下融入对动物福祉的关怀吗?
张伯驹:“ 这种尝试肯定是有益的,但需要考虑时机问题。比如,野生动物的主体性如何界定,在我看来首先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栖息地能提供保护。其次,现在还处于以“去除三有”为代表的去资源化阶段,野生动物不是食物、衣服或药品,这几年的攻坚还是在这一层面 [2] 。如果现在考虑“动物自身对福祉和诉求的关怀”就有点超前。节奏很重要,公益要引领社会,但有效公益也需要注意适应整个社会的节奏。就好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北京推行垃圾分类是很难的一件事一样,当时有公益人士放弃了推动,理由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太超前了”。意义是肯定有的,而且当时的先行者令人尊敬,但从效果上来看,就不得不接受“试点难以推广”的现实。虽然现在推动垃圾分类依然不易,但相对25年前而言,社会氛围好了许多。
[2]编者注:“去除三有”指调整《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简称《三有名录》。”
益盒: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积极拓宽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诉讼范围。您觉得这一进展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
张伯驹:“ 我认为主要推动力是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当然其中也有民间力量的推动,以及配合《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检察机关作为环境法治进程中重要的推动方,积极参与其中,对野生动物保护有着正向意义。
环保组织是拓宽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范围的推力之一,也是提起相关诉讼的主体之一。在环保组织外,检察机关也是环境公益诉讼的重要诉讼主体,他们在案件数量等方面还有一定的绩效指标,在全国各地发起了很多环境公益诉讼,希望未来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环保组织和检察机关都能够持续发力。
《野生动物保护法》此次修订之后,禁止野生动物商业化利用有关条款的落实是很大的挑战,这也属于环保组织需要持续努力的地方。在法律修订过程中,由于一些环保组织和学者在这个方面的公开发声和倡导,已经引来了很多野生动物养殖户要“拼命”。其实这对于环保政策的推动者有一定的风险,这背后更显示出了法律条款进步同时带来的张力——如何平衡相当数量的养殖户的政策性经济损失?如何实现公共政策的“软着陆”?怎么平衡这里的张力,就是政策具体落实过程里需要重点关注的细节了,这很关键。还是那句话,对于成功的政策倡导,政策文本的改变不是终点,甚至只是一个长期过程的开端。”
益盒:您是否关注海洋野生动物的组织,或者是否考虑将公益诉讼推演到海洋领域呢?
张伯驹:“ 有民间组织制作过中国海洋保护民间组织的名录,有兴趣的话可以下载查看 [3] 。
[3]编者注:https://www.jica.go.jp/china/office/about/ngodesk/ku57pq00002266f9-att/ngo_09c.pdf
民间组织在海洋野生动物保护这个领域提起公益诉讼的挑战比较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并未明确规定社会组织在海洋省生态环境收到破坏后的诉权,自然之友曾经在2017年这部法律修订过程中努力推动过,可惜目标没有实现。今年五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份《关于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专门规定对于破坏海洋生态的行为,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但仍然没有社会组织的相关条款。
在此之外,社会组织在海洋领域、尤其是针对海洋野生动物类提起公益诉讼,有两个主要难点。第一,走私类的情况往往难以取证,大部分取证在海关层面发生,民间组织难有常规渠道和一手信息来源;第二,在海洋领域的公益诉讼中,民间组织真正能提起诉讼的角度更多是栖息地而非物种,比如自然之友之前做过的针对中华白海豚(印太洋驼海豚)和珊瑚栖息地的诉讼,多是以非法填海或石油泄露这类毁坏栖息地的情况提起诉讼。

图注:2020年5月3日,一头中华白海豚在广东省江门台山市烽火角附近一处海岸搁浅。当地民警与江门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工作人员迅速展开救援,最终成功助其返回大海。图源「光明网」
关于海洋野生动物的贸易和走私问题,相当一部分是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之下贸易层面的博弈。贸易监管主体包括国家的濒危物种管理办公室,执法过程中也会直接由公安系统介入。因此这方面的现状是公检法是主力,民间组织并不处于行动的核心。当然,这些年来依然有一些环保组织积极地进行推动和探索。更多是按照CITES公约直接和公安合作打击走私、非法贸易以及非法跨境贸易。”
益盒:据了解,修改《慈善法》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2022年的任务之一。您认为慈善领域如何能更好地与环境保护及动物保护相结合?
张伯驹:“ 就我之前的经验而言,针对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慈善法》并没有太多直接的指向。
从广义上来说,《慈善法》是让自下而上的力量能参与到包括政策倡导和直接提供公益服务在内的各个环节的博弈中。不论是倡导还是服务,如果新修订的《慈善法》能进一步开放社会参与的空间,让民间力量在建设性的规范下有更多活力,那么在此基础上,不管是环境保护、动物保护,或是其他领域的社会组织,都能在大的生态中有更好的发展。”
立法是撬动整体改变的杠杆但远非终点
益盒:促进政策倡导、推动立法改变是一件具有成本效益的事情吗?如何看待系统改变和直接行动之间的张力?
张伯驹:“ 推动立法的时间尺度至少以“10年”计算,一旦有变化就可能是整体性的变化。比如针对土壤污染就有很多组织在做不同的事情,有的组织像调查记者一样“揭黑”,有的直接救济污染受害者,还有的可能直接研发更好的土壤修复技术等。
自然之友所做的就是推动法律条款从无到有,这需要很多年时间。其路径是政策研究、建立与立法机关的沟通渠道、专题政策和实务研究、参与立法项目“竞标”,甚至还有真实诉讼案件的积累。最终还是回归到这样的看法:不要把政策制定想象成“铁板一块”,做出每一项工作落实每一个行动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只是体制会带来一定的规律性塑造。
在倡导过程中,风险也是有的。自然之友在此之前为了推动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者担责”原则的相关条款,启动了一系列土壤污染的公益诉讼,差点把自己打“破产”,因为当时土壤污染的一个案件诉讼费动辄上百万元。当时“常州毒地案”一审输了,法院要求原告社会组织缴纳189万元诉讼费,我们别无选择,积极上诉,二审如果再败诉,诉讼费就要乘以二。这就是真实存在的风险。

图注:紧邻常州外语学校的有毒土地,曾经是几家化工厂的厂址。图源「新华网」
这样的风险很真实。常州毒地案一审败诉后,许多人提议自然之友众筹诉讼费,但我认为不能筹。从伦理上看,一家公益组织做得出起诉的决策,作为原告就得有与“败诉”相应的风险预测,风险兑现了就要去承受。如果输了官司,就让大家捐钱,是不可持续的。
这样的倡导活动风险的确挺大,不过一旦可以成功推动法律条文的修改完善,就能直接影响上万亿的土壤污染修复市场的进一步规范,成规模地遏制土壤污染及二次污染的发生,从机制上保护公众的环境健康权利。
所以你要问这些年值不值?我认为做成了就非常值。如果推动一项政策改变就能影响上万亿的市场,虽然可能还存在各种风险,对于专业性和耐力的要求也相当高,但这种工作一旦做成,撬动社会问题解决的杠杆效应远超其他很多行动方式。我会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的事情。不仅从公益组织的角度,更是从捐赠人和基金会的角度。
当然,不是只有政策倡导才是有效的路径。整个的行业生态要更具活力才行,大家其实是在不同位置、不同频道上发力,只不过我们选择了其中的某个“生态位”。如果只靠自然之友推动政策倡导、发起环境公益诉讼,那些被有毒土壤毒害的孩子可能并不能很快得到救济,而通常一起诉讼耗时要三年或更长,所以那些直接救济污染受害者的组织很重要。但如果我们也去做救济污染受害者的工作了,缺乏政策和法治上的倡导与推动,上万亿的市场缺乏制度性约束,土壤污染事件可能会更层出不穷,受害的孩子也会更多。”
益盒:在自然之友参与的过往案例中,比较成功的、有影响力的有哪些?
张伯驹:“ 影响比较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再加上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一系列司法解释所推动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时间跨度从2005年到2015年,总共11年时间,还有后续的修订,到现在有17年了。把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从无到有做起来,自然之友是一个关键因素,但还有很多关键因素构成了整体的生态系统,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者,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环保总局)、(原)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等公职人员和相关智库,最高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众多媒体和公益组织等。
自然之友在2011年提起了首个草根环保组织发起的实验性案件“云南曲靖铬渣污染公益诉讼案”,为《环境保护法》的公益诉讼条款提供了重要的试点和案例;2015年提起的“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则成为了《环境保护法》公益诉讼条款生效后全国首例环境公益诉讼。再往后,几乎每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年度典型案例中,都会有自然之友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相当于自然之友的诉讼案例每年都会成为全国法院系统学习的案例之一。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梁从诫先生在2005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关于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提案时,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过于理想化,但十年后,在自然之友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合力推动下,这个梦却成真了。

图注:云南曲靖铬渣污染公益诉讼案。云南陆良化工曾历史遗留的铬渣堆场与南盘江仅一墙之隔,拍摄于2011年8月25日。图源「澎湃新闻」
其次是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还有刚才提到的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土壤污染防治法》)从无到有等,不光是单一的法律制订,还包括相应的规范性文件、标准的制订以及司法实践。
此外还有湿地保护。自然之友从2015年开始推动,从北京市的湿地保护地方条例到武汉市、湖北省的湿地保护地方条例,再到202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以下简称《湿地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我们推动了这些法律条文的一些变化,主要在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以及一些维护公共利益的条款当中,以及推动一些配套性文件的出台。
当然,之前我们也有过一些经历,很成功地影响了一些政策条款的出台或改善,却缺乏后续落实阶段的参与和推动。比如曾经在一次倡导工作中,通过一系列有效的行动,总理直接批复了我们的报告,我们的诉求也几乎全部在修改后的政策文本中实现了。但我们在开心之余并没有进行后续跟进,后来发现这些条款并没有实际落实以促成真实问题的结局,非常令人沮丧。当时觉得自己胜利了,后来发现时真是当头一棒。现在这是我在公共政策课上经常会讲到的案例——典型的失败案例。它所引起的思考是使命驱动的组织如何看待倡导的有效性?如果我们的定位仅仅是“提出政策建议”的智库,那这将是我们的一项“高光”业绩;但如果我们关注的核心是解决社会问题——那光有政策出台和领导批复就远远不够了。
这样的经历,也让我们进一步看清了政策倡导工作的“生命周期”。比如,在政策倡导的过程中,不少公益组织的政策倡导工作局限于提出两会提案,也将此作为成功指标,但那只是一个环节,或者说只是一个起点,更需要关注的是提案最终是否被落实或有没有反馈,以及是否推动了长效解决机制。”
益盒:您提到确定某件事是否“做成”,需要关注后续立法后执法环节的落实情况。那“做成”的标志到底是什么?
张伯驹:“ “做成”是指真正能够有成效地解决社会问题、保障公共利益。立法有立法目标、倡导有倡导目标,倡导对组织而言是策略或手段,而不是使命。组织的使命并不是倡导,而是非常具体的“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的内容,比如是保障残障群体获得更完整的权利、更多的机会,或者保护某个野生动物种群及其栖息地。
举个例子,自然之友为什么要推动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倡导?因为上万亿元的市场单靠企业自觉是管不住的,靠社会组织和检察院起诉是告不完的、“揭黑”是揭不完的,只有靠国家立法才能加以规范,确立“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和相应条款,否则会出现污染者将土地污染后直接卖给别人的现象,这样是变相地鼓励污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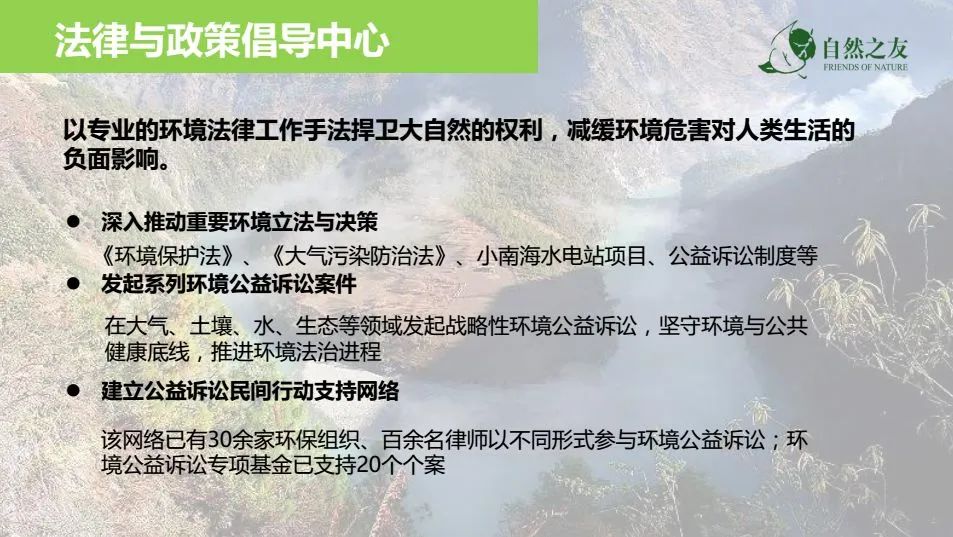
图注:慈善募捐 | 联劝(自然之友)专项基金界面。图源「联劝网」
推动立法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法律变化,或者广义的公共政策的变化,在政策的有效落实后规模化地解决问题,而不是“case by case”。而做案例是在设定议题后开展一些试点,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学院派的政策过程,但得根据最后落实的效果再修订法律。
以土壤问题为例,最终要判断价值上万亿元的市场是不是真正有效地管起来了。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后,要看被禁止商业化利用的野生动物是不是还是能随随便便被端上餐桌。自然之友这些年最有代表意义的成就之一是推动了公益诉讼制度。但这样的成就是否真正产生了足够的社会价值?应该在这一制度正式实施5年后、10年后再做回顾,分析评估到底有多少起公益诉讼、有多少具有诉权的社会组织、通过公益诉讼如何维护了公共利益、效率几何等。
我一直觉得政策倡导或证据应该是可评估的,而不是“全凭一张嘴”,可以有更多的证据,包括前后对照的文本、与各节点接触过程中倡导的动作等等。之后再看倡导动作的时点是否与这项政策出台的时间相关,以及政策出台后是否能产生真正的影响,进而得到投入与产出的杠杆率。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北美和欧洲国家的慈善家愿意支付长达20年的政策倡导成本,长期坚定地支持政策倡导的行动和组织,因为他们能看到其中极高的杠杆率。虽然现在中国这方面的慈善家和基金会很少很少,但并不需要抱怨什么,因为公益行业本身需要有进化的过程。本土公益组织要自强,要持续推动真实的行动,坚持住,要得有能力用更多实际案例去证明政策倡导的有效性。”
益盒:国外并不忌讳谈论失败的公益案例,但国内目前暂时没有形成这样的氛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状?您提到的这类“立法上成功,但最终没能落实”的案例多吗?
张伯驹:“ 从民间组织的角度出发,很多人都太需要成就感了,而失败打击的恰恰就是这种成就感。但成就感并不是可持续的动力来源,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异化我们的行动方向和战略定力。
事实上,我们做政策倡导就是“胜少败多”。哪怕是被广泛认可的公益诉讼,也有很多值得探讨之处。外界评价我们打了51个案子,只输了1次,即“常州毒地案”一审,但我们自身不能这样看。胜诉只代表你在法律上赢了,但一起诉讼的核心目标能否达成,还有待观察和长期评估。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政策倡导的失败的案例没有那么多,可能还因为案例总数就不多,真正投入其中的公益组织数量也很少。”
益盒:如果民间组织持续保持关注,政策落实的成功率会更高吗?
张伯驹:“ 这是当然。民间组织一方面要参与落实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要扮演监督者的角色,比如一个全国性法律的落实,就面临着各地条例是否要跟进、是否要评估的问题,官方评估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民间评估一年就能出来。很多法律到省一级的条例的评估工作,国家需要两三年。民间组织也可以做,甚至同时做个“影子报告”,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它是有用的,一定能促进法律更有效地落实和完善。

图注:环保民间组织助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论坛在昆明。图源「中华环保联合会」
在这个过程中不管你是参与落实还是监督落实都是有价值的。
我猜想你的问题背后还有一个问题:“一个组织一条龙干得下来吗?”,当然是不行的,很多时候需要依靠行业生态。以信息公开为例,2007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信息公开条例》),卫健委等各部门都有相关的办法出台。而在当时,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环境领域的信息公开力度是比较大的。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环境主管部门需要借助公众的力量给自己赋权;第二,环保组织的能力和对这方面的关注度较高。自从《信息公开条例》出台后,包括马军老师和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就大量提起环境信息公开申请,目的是帮助体系练出功夫,因为从法律的出台到最终落实需要一个“熟悉”、“熟练”的过程 [4] 。如果没有人参与和推动,整体系统慢慢就“钝”了;当然,这其中还要有更多的行动方式,如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及媒体及舆论监督等。
[4]编者注: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IPE)创始人、主任,也是该组织的创建者。
横向对比,环保部门的信息公开能力很强,在各部门中名列前茅,在国际上都有名。但也不能只靠一个民间组织来推动,马军老师所创立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是推动环境信息公开的头部组织,影响力很大,但他们并没有单打独斗,而是积极营造行业生态,支持同行成长与成就,如今环保行业中有几十家公益组织将环境信息公开作为日常业务进行推动。如果只有IPE一家,他们也顾不过来。在推动社会问题解决的路上没有“包打天下”,那对于任何一家组织来说都不现实。”
政策倡导的道与术
益盒:自然之友在政策倡导的不同层次都做了哪些工作?
张伯驹:“ 自然之友基本以国家层面的政策倡导为主,省级层面以北京市为主。我们在2017年研发了“政策倡导研修营”,目前有上百家组织完成了学习。不仅仅是环保组织,参与者还包括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等。政策倡导研修营的议题包括工业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涉及的内容很全面,比如如何运用法治工具、了解公共政策、参与信息公开、如何跟政府部门有效沟通等;也有包括提起并推动两会提案、在一分钟内跟政协委员或“关键人”(key person)说清倡导内容等基础技能,这些都需要务实的训练。
截至目前,自然之友的政策研修营已经做了七期。我们也配合目标开展了一系列动员资助方的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环境领域的不少基金会现在都对环境法治和政策倡导方向的项目和组织进行资助,不过额度依然比较小。包括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等资助方也愿意资助政策倡导类的能力建设活动,这些都是令人欣慰的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不少参与了自然之友政策倡导研修营的伙伴机构在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倡导工作已小有成就,尤其是在本地的政策层面,一些组织已相当具有影响力。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从“生态位”的视角出发,并不是所有公益组织都要推动国家层面的立法,很多地方性的政策法规以及重要立法的落实特别有价值。
2015年3月,全国人大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此次修订内容非常重要,除了公众参与条款外,更重要的是将立法权下沉至设区的市一级,降低了公共政策的门槛。假如我是安徽省芜湖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一员,那我推动与芜湖市青弋江相关的保护条例就是好的倡导,而不必非得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为什么说最好的是本地倡导?因为地市级的环境保护协会的成员在当地有一定渠道和影响力,他们认识当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媒体机构,他们受到当地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的信任,他们能够在当地能串联本地资源、影响本地政策、推动有效落实,之后再基于一系列案例和试点逐步向上取得更多影响,这才是真正“自下而上”的力量。
《立法法》出台后,我们发现了这一政策进步之下巨大的需求。2017年开办“研修营”就源于此。不少地市一级人大在立法能力和资源方面都有需求,具备一线能力和真知灼见的民间组织有很多与地方人大进行政策沟通的空间。2015年以后,经常出现地方人大在制定地方条例时邀请自然之友参与的情况,例如《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的制定等。

图注:《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五条,因铁腕治污“一刀切”导致排放磷、氮等污染物的企业和项目无法新建、改建、扩建,而备受争议。图源「财新传媒」
政策倡导听起来很难,但近年来真实的需求使得它的门槛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学术界一直讨论我国到底是“开门立法”还是“关门立法”?我认为至少在越往基层的地方,民间组织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越有发挥的空间,但真正的制约因素在民间组织的能力。此外,“实战”非常重要,在推动《长江保护法》时,我们会和长江沿岸的多加民间组织共同就该法律草案进行分析研讨;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时,我们会基于之前通过政策倡导研修营等工作形成的网络,组织七八家一线机构、部分资助方机构以及智库机构在一起开展集体学习和立法研讨会,并与一些资助方和学者合力推动立法。”
益盒:您认为民间组织在参与政策倡导工作中最需要关注的细节有哪些?
张伯驹:“ 首先,民间组织一定要思考,什么样的问题应在国家层面加以解决?资金来源是通过民间筹资,还是公共支出?一定要明确组织自身政策倡导的框架定位。
政策倡导是必需的,但却不是万能的,我认为不应让老百姓捐钱做基本服务的事。当时推动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核心就是如此。在当时,企业污染了土壤,但土壤修复的钱却来源于财政。财政资金本都应该用于民生,为什么要填补企业污染的后果?我国环境的立法原则之一是“谁污染谁负责”,商业部门造成的污染不能用公共资金修复,更不能让公益资金兜底,这就是我们当时倡导的核心。从框架来看,民间组织就一定要做倡导,而不是在民间筹资修复土地。

图注:自然之友的公益律师带着专家在广西一处铅锌矿污染的地方检测稻谷的样本,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超标。图源「自然之友」
其次,政策倡导是需要讲策略和技巧的。以自然之友为例,之前,人大的立法听证会、咨询会以及一些部委的立法咨询活动会都会邀请我们。
主要的原因有三。第一,自然之友会遵守会场秩序,尊重其他参会方;第二,自然之友会配合会议的保密工作,不随意对外公布会议中的相关信息;第三,有足够的专业性和拥护意识,能从立法者和法律未来使用者的角度看问题,如此提出的意见更有可能被立法者所看到,而不是停留在呼吁性的倡导,需要翻译为“法言法语”。在提建议的时候,民间组织需要关注如何在保持专业的基础上为政策制定者留有足够的行动空间、行动选项。”
益盒:除自然之友外,您是否了解其他比较有影响力的进行政策倡导的民间机构?
张伯驹:“ 在环保领域,马军老师非常有政策影响力。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以及其创始人吕植老师也是如此。还有全球环境研究所,他们在中国海外投资、“一带一路”等政策方面有一定影响力,也会直接去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做政策影响工作。创绿研究院定位为环境气候领域的民间智库,近年来做了大量国内和国际政策研究工作,产出多部报告,在一些议题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性。
环保领域外,已开始进行政策倡导业务的有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虽然并不作为核心业务,他们还是会积极参与一些政策推动工作。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现在正在把政策倡导做成一项业务并长期推动。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的女童保护项目(以下简称“女童保护”)这些年来的基础也打得非常好,他们在每年“两会”期间举办的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很有潜力。主要原因是民间组织做政策倡导需要找到渠道代言人,而“女童保护”通过座谈会,可以接触到包括全国人大、政协、检察院,以及体制内的妇联等在内的各类渠道,实现有效的沟通。

图注:2021年3月2日,2021年“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在北京举办。会上发布了《“女童保护”2020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图源「腾讯网」
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在两三年前就明确将影响政策作为重要的业务领域,并已取得一系列成果。教育领域的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政策倡导的主力。还有我非常尊敬的反家暴网络等一系列妇女保护组织,他们在反家暴立法过程中有很多“高光”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在那个时代做了杰出的工作。可惜的是我们这一辈没有机会与他们共事和学习,所以我准备把这个经典案例重新“挖”回来。”
益盒:您认为机构的核心人物是否需要对业务有长时间的观察和经验?
张伯驹:“ 我认为是需要的,团队领导者在这方面一定要有能力、视野和格局,将政策倡导在战略层面进行推动,并且有持之以恒的定力。例如自然之友现任负责人,她与司法体系、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沟通能力比我高很多,这非常重要。又如融爱融乐的现任负责人,支持团队将政策倡导从想法发展为业务,并且持续取得影响力。而且他们有共同的特质,就是坚信公共政策倡导的价值。”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