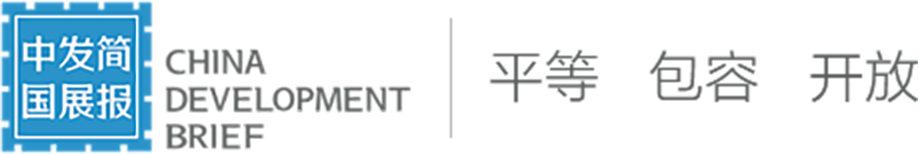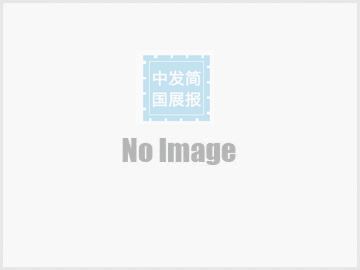2022-04-15
2022-04-15
 266
266
“我是高级社会工作师”系列讲座活动于2022年3月15日“国际社工日”启动,首位演讲人邀请到协作者(Facilitators)创始人、高级社会工作师、民政部首批全国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才李涛,分享《信念与现实——基于协作者的本土实践》专题内容。李涛主任在讲座中分享了他从事公益20年,在社会工作领域扎根一线,用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做好每一项服务的故事。本期开始,协作者云社工将连载李涛主任分享的专题内容。

李涛,“协作者”(Facilitators)创始人,北京协作者中心主任,高级社会工作师,民政部首批全国社会工作专业领军人才,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妇儿工委儿童工作国家智库专家。他于1996年担任媒体记者时参与社会公益,2003年发起成立国内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之一“协作者”,致力于赋权流动人口,发展本土社会工作,推动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学界的跨界合作。
高级社会工作师除了能够综合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开展服务之外,还承担着发挥示范引领的作用,以更好地推动行业发展,带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使命。
基于这个使命,北京协作者的“协作者学堂”和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工作系的“学艺讲堂”、美亚联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社会工作》杂志融媒体四方联合发起了“我是高级社会工作师”系列讲座活动,该活动也得到了风直播、益直播的公益支持。非常荣幸我能负责讲座的第一讲。
自从我考取了高级社会工作师之后,很多人都很关心“我是怎么成为高级社会工作师”以及“怎么一步步地成长起来的”。从我1998年开始接触社会工作,到2003年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工作这个领域当中来,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处境,我都不会去质疑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也不会去否定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的存在价值。对专业本身的批判性探讨我是非常欢迎的,但我从来没有做过对它的否定。所以在这么多年当中,很多人就有一个问题,觉得很奇怪,问我说:“你为什么对社会工作专业这么坚定,这么相信这个专业?”这就涉及一个基本信念的问题,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我之所以能够成长为高级社会工作师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在这个信念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我坚守下来,一步步地成长为高级社会工作师?我会从三个方面和大家分享。首先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服务农民工;其次是“做什么”,在专业服务方面,我重点在哪些领域开展了这些工作;最后是“怎么办”,在专业服务过程中、在我个人专业成长过程中,都遇到了哪些挑战,以及我对此的一些反思和建议。
01 我为什么服务农民工
根据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视角,在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框架下,除了我们说的基因、生物因素之外,人的选择还受制于大环境的影响,我们的成长经历决定了我们的今天。因此,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我“为什么”要服务农民工,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问过我的一个问题。
01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曾经在农村的姥姥家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是胶东半岛的一个山村——这就是我生活过的院落,我的童年在这里度过了大概有七八年的时光。在这段时光当中,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中国农民的朴实、勤劳、善良,他们养育了我。所以若干年之后,当我在城市里遇到了进城的农民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不是为别人在服务,是为我的父老乡亲们在服务。
我的妈妈是一名医生,我童年里有一段时间,跟着妈妈住在医院的家属宿舍里。那个医院在镇上,周围全都是乡村。我小时候比较好奇,医院旁边有太平间,每当死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跑到太平间去看。在北方的农村,每当到了农忙季节,大概就是在六月份左右,隔三岔五,就会有自杀的人被送过来,而且大部分都是农村妇女,其中有些我还在集市上面见过。在镇上,每五天一个集,很多妇女拿出最好的衣服、打扮得非常整洁地去赶集。我至今都记得她们的样子,非常有活力,非常阳光,非常漂亮。
但是后来,我突然之间就会在太平间里面发现,这个自杀的女性不就是我在集上曾经见过的吗?这些农村妇女的自杀都非常惨烈,要么是喝农药,要不就是跳井,要么是上吊,主要是这三种方式。若干年之后,我也在一些文献材料中发现,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在农忙的季节自杀的人很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忙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辛苦。而女性,除了要去做地里的活儿,还要负责做饭,照顾家里人。往往这个时候,会发生一些矛盾,比如说,因为送饭不及时,丈夫骂她,甚至打了她;因为家里找不着东西,婆婆就怀疑是儿媳妇把这个东西藏起来了,或者拿走了——会发生类似种种的矛盾,然后妇女就选择自杀。那个时候我曾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委屈,让她们一定要选择死亡?死了之后不就不能讲话了吗?”我当时是想不明白的。
我的姥爷是乡村里的一个知识分子,他也是一名医生。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姥爷就订了全村的第一份报纸——《参考消息》。那个时候,在乡村可阅读的东西并不多,所以我大概从三四年级开始,每天放学回家就会看报纸,看《参考消息》,慢慢就知道了有记者这个行业。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长大了,我愿意做一个记者,去帮助那些没有办法说话的人,替他们去把声音传递出去,不至于让他们去自杀,这是我小时候最简单的一个愿望。
02 我的故乡

我的故乡是非常漂亮的,这是我故乡的照片,有山有水,而且到处都是果树环绕;我家乡的小伙伴也都非常聪明。我的父亲是青岛市里人,我有时候要跟我的父母进城,然后有时候会回到乡村。比较起来,小伙伴们很羡慕我,因为我在他们的眼里是一个从小可以捧“铁饭碗”的人——当时把有城市户口称为“铁饭碗”。但我也很羡慕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特别心灵手巧,一块泥巴、一根树枝在他们手里,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特别精巧的玩具,而我做不到,这是我当初对他们的看法。

若干年之后,我到大学里面学了新闻,我真的成了一个记者,后来我再回到我的家乡,我发现我的山村变成了这个样子。因为我的家乡在山区,它盛产花岗岩,这种石材特别受欢迎,比如我们天安门广场的石头,就是地面铺装的那个石头,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于我的家乡。各种企业都来到我的家乡,我的故乡变成了一个被开采、被污染的地方,当地的癌症发病率非常高,而当地的农民只能挣到很微薄的工资。
这个事情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在想,这究竟是不是我们要的经济发展?当人们行走在城市的街头,不经意间见到的那些各式各样的精美的石材,构建了这个城市的繁华和华丽。但是对于我的家乡来讲,它是以牺牲了它的环境,甚至是它的可持续的生命力为代价的,这些都对我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03 我为什么服务农民工
我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去工业区的时候,非常震撼。下班的时候,工厂的大门一开,就会看到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年龄差不多,穿着一样的工装,脸上的表情甚至都是一样的,向你扑面而来。这个时候,你真的就会感觉他们像行走的机器一样,他们是整个流水线上的一个生产资料、一个生产的元素。在整个工业生产的环境当中,农民工确实也被视为廉价的劳动力,但是他们在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是被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的农村有很多剩余劳动力,可以鼓励他们进城,让他们学习一些技能。
他们进城来,一方面可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吸引更多的资本到中国来投资;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挣到钱,这个钱就会寄到家乡,寄给他们的家庭,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会得到改善,家乡也能够发展。这其实就是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基本发展思路:我们鼓励他们掌握一些技能,既能和资本结合解决就业,也能带动经济的发展,他们找到工作也能挣钱,能推动家庭和个人的经济发展。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知道,他们除了是一个农民工、一个生产者之外,其实在他们的工装下面,都是一个个年轻的鲜活的生命。
有一个小姑娘,叫小英,她在1989年外出打工。她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帮她的父母减轻经济压力,让哥哥更好地考上大学;另外一个是她希望到更广阔的世界当中去看一看,能不能追求自己的梦想。当时她只有15岁,借了堂姐的身份证外出打工。但是,在1993年,她外出第4年的时候,她变成了这样。她所在的这个工厂,发生了一场大火,烧死了80多个人,小英是幸存者,她前后做了300多次手术。后来她的哥哥确实考上了大学,但是她却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这张照片上的打工妹都是小英的工友,她们没有小英幸运,全部在那场大火当中失去了生命。如果她们活着,她们的年龄应该跟我差不多大。那场大火发生在1993年的11月19日,在深圳一个叫致丽的玩具厂里,所以被称为“致丽大火”。
这场大火,把很多人,尤其是社会学界和社会发展领域的人烧醒了。大家第一次开始质疑一个问题——这是我们要的经济发展吗?农民工进城找工作、挣钱,真的是这样一个发展逻辑吗?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农民工进城后,他很可能找不着工作,或者是他找到工作之后并不能够拿到工资。即使他拿到工资,也很可能因为职业安全事故丧失健康。也就是说,当脱离了社会保障的基本条件,这样下去,我们的经济能不能真正地可持续发展,能不能造福于我们这个社会,这是当年很多人的反思。

这张照片是我2003年在重庆拍摄的,这是当年农民工的输出地,他们的家乡最常见的一个场景。很多人在外面辛辛苦苦地挣钱,挣了钱之后,回家盖一个更大的房子,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但很不幸,这张照片上的主人已经不在了,这个家庭夫妻两人都得了尘肺病。他们当年也是外出打工,去生产榻榻米,一种出口日本的用品。他们负责一道叫“拔草”的工序,即把草放在绿色的泥浆一样的东西里染色,之后再把烘干的泥抖掉。整个过程中不仅有大量的粉尘,生产车间的条件也非常不好,基本上都是家庭作坊,他们在里边工作一会儿之后,除了眼球和牙齿是白的,整个人都是灰黑色的。但他们居然在那儿工作了十年,然后得了尘肺病。尘肺病是不可逆转的一种疾病,得了这个病,基本上就会慢慢死去,死亡过程也会非常痛苦,肺部就像灌满了沙子一样,慢慢地失去它的活力,人最后是被活活憋死的。
这对夫妻还有两个孩子,当时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大的孩子大概只有八九岁,小的只有四五岁。我听完他们的故事之后,我觉得非常不可理解,也非常气愤。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即使没有太多的职业健康知识,也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工作对身体有害,对健康是有影响的,你们为什么居然能够在里面工作十年的时间?这个大姐,她沉默了半天,才跟我说:“没有办法,我们知道对身体不好,我们就想,挣够了钱回家把这个老房子翻修成楼房,我们就再也不出来了。”我就问她说:“这个楼房对你们这么重要吗?”她说:“是的,如果我们不能盖起楼房来,不光我们,我们的孩子未来在村子里面也抬不起头来。”
就在那个瞬间,我有很多的触动。那个年代,我们追求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我进入这样一个乡村里,更真切地看到了这种变化。物质水平确实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他们的家庭里边没有人气,是冷冷清清的。因为当他们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在逐渐丧失劳动能力,甚至在慢慢等待死亡的时候,整个家庭甚至整个村庄都将失去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我去的那个村庄,50多户人家,大概有30多户人家里夫妻两个都得了尘肺病,这将是一个没有办法呼吸的村庄。所以做完这个采访之后,我写了一段话, “他们忍受着资本的盘剥,也在无形的话语之下成为消费主义的奴隶,这种双重盘剥,既来自全球化下的城市,也来自城市化下的乡村,就这样,物质成为衡量人生幸福的唯一标准,生活本身却被置于生活本意的别处。”这些经历,都促使我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思考。
在20世纪90年代,我的成长经历当中,还有一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大概在1998年的时候,我当时在《中国妇女报》做记者,1998年1月10日,河北坝上——就是我们现在冬奥会举办的地方发生了地震,当时死亡60多人,形势比较严峻,我就被借调到灾区,做了为期三年的抗震救援工作。一开始是做紧急救援,一边做采访一边做救援,后来慢慢地参与到灾后的重建当中去。在灾后重建的过程当中,我和当地的农民,还有当地的政府干部们一起,做了大量的促进乡村发展的尝试和探索,看怎么样更好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怎么更好地来推动社区发展,改善农民的生计。

这张照片是灾后重建阶段,我和当地农民在一块儿。当时有五户农民,他们联合起来决定不再种粮食,因为当地缺水,他们决定种草——集资购买了一种从俄罗斯进口的用于饲料的草籽,看看能不能通过种草,来发展畜牧业,来改善他们的环境。
后来,这个试验失败了,我参与了很多这样的试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几个发现,一个是,我们的农民实际上是非常勤劳的,而且非常有智慧。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思考,他们并不甘于在命运当中沉沦下去,他们是非常理性的。另一个是,我也发现他们其实也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一盘散沙。
当他们想明白之后,他们会因为他们共同的需要组织起来,比如说这五户农民,他们就组织起来,共同凑钱、派人外出学习、采购种子,回来改善他们的经济。但是之所以失败,我认为是因为中国的农村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我们原来认为,是因为地少人多,大量的农民没有地可种,但经过那几年在农村的体验,我感觉可能不是这个原因。我看到更多的情况是,农民有地也不种了,我们的传统农业实际上是破产的。农民不应该再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需要更多元的、更自由的选择,进城务工是其中一个选择。
这是我对中国的农村、农民、农民工的一些认识,也是我为什么后来坚定不移地来为农民工,为农民来服务的原因。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