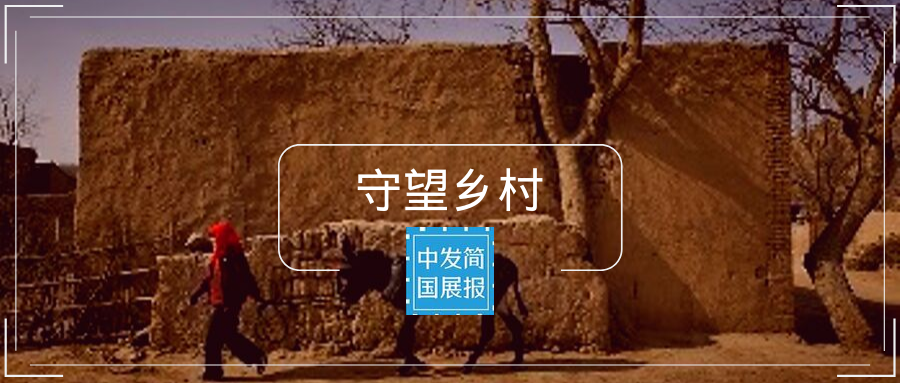2025-02-28
2025-02-28
 176
176引言
塑料污染,包括海洋环境中的塑料污染,对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11月25日-12月2日,旨在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塑料污染(包括海洋环境中的塑料污染)国际文书(《应对塑料污染的全球公约》)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5次会议(INC-5)在韩国釜山召开。INC-5发布了主席案文(Chair's Text),明年各方可能会围绕此案文开展磋商。从目前的版本来看,案文强调了基于科学的决策以及科学、经济、社会和技术信息,包括传统知识和本地知识体系,对全球减少塑料污染,加强各国对塑料全生命周期以及全球塑料污染影响的认识至关重要。尽管在原则、资金机制等方面仍有诸多不同意见,不过主席案文在废弃塑料污染防治的下游环节,如减少塑料制品泄漏到环境中(第七条)、塑料废物管理(第八条)、现有塑料污染整治(第九条)以及公正转型(第十条)方面,呈现出比较一致的意见,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方对下游管理以及公正转型重要性的共识。
根据主席案文的第七条“排放与泄露”第一款,“每个缔约方应当(shall)采取措施预防、减少并尽可能消除渔业活动的塑料污染,包括但不限于在海洋环境中丢弃、遗失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废弃渔具,并充分考虑[……]手工和小型渔民的相关需求。
根据第八条“塑料废物管理”第二款,每个缔约方应当(shall)在结合各自国情的情况下,“预防并禁止塑料垃圾在海洋环境中的[……,]倾废和露天燃烧,以及预防并减少遗弃、遗失或其他原因废弃的塑料渔具。”
根据第九条“现有塑料污染”,各缔约方应该(should)“以环境友好的方式采取适当措施来移除现有环境中的塑料污染”(第一款),并且“促进原住民、当地社区、民间社会、科学家与私营部门的参与,并促进技术、经验与教训的交流”(第二款)。
根据第十条“公正转型”,各缔约方应该(should)“考虑相关行业的正式及非正式从业者的情况,包括拾荒者、手工与小规模渔民、中小企业、以及与塑料全生命周期相关且受转型影响较大的原住民、当地社区、女性及儿童等群体。”(第二款)
值得一提的是,防止塑料从陆地塑料管理体系中泄漏到海洋,以及移除已经存在于海洋环境中的塑料,即海洋废弃塑料的截流与移除,是塑料废物管理的下游环节。与相对完善的陆地塑料废物管理体系相比,末端治理仍属于目前塑料管理体系的边缘,行动的成本高、回报低,受到的关注和资金投入相对有限。
绿研长期关注可持续蓝色经济及蓝色产业转型议题,借INC-5召开之际发布《海洋废弃塑料截流与移除》政策简报,分享我们对海洋废弃塑料截流与移除的主要措施、现有政策与资金支持情况以及未来多元资金参与其中的机遇的初步分析,以贡献于废弃塑料下游治理的相关讨论。本文为简报重点内容的速览,请点击“阅读原文”或扫描二维码查看完整内容。如有不当之处,请各位伙伴批评指正(ocean@ghub.org)。

本次INC-5期间,绿研团队远程参会,欢迎各位伙伴与我们交流(plastic@ghub.org),共同关注全球塑料污染治理谈判及行动的新进展。
背景
海洋塑料污染是全球塑料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塑料生产和使用规模呈现指数级增长。大部分塑料因为使用寿命短而迅速成为废弃物,这些废弃塑料的大部分未经妥善处理而泄漏到环境中,其中又有可观数量的废弃塑料最终进入到海洋,在各类海洋生态系统中积累了不容忽视的数量。如果不加干预,未来每年流入海洋的废弃塑料量将持续增加,导致海洋塑料累积量不断上升。
海洋塑料污染受到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分别将治理海洋废弃塑料作为防治海洋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内容。旨在达成上述《应对塑料污染的全球公约》的政府间谈判也将减少海洋塑料污染作为关注点之一。
海洋塑料污染的根源在于陆地。作为前端治理的重点,陆地塑料污染防控已获得了广泛关注和投入。现有废弃塑料治理体系的目标是在减量的基础上,实现塑料从生产、使用到回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防止塑料泄漏到环境中。然而,这一目标尚未完全实现,大量塑料已泄漏到陆地环境中,其中一部分最终进入海洋。这些污染因治理力度不足仍然在海洋中积累,威胁着海洋环境。
根据Eunomia汇总的统计数据(如下图所示),截至2018年,每年从内陆流进海洋的塑料为50万吨,从沿海地区流进海洋的塑料为900万吨,从海上活动进入海洋的塑料为175万吨(其中来自渔业活动的为115万吨,来自航运的为60万吨)。这些塑料大部分(94%)沉入海底,达到每平方千米70千克的密度,5%停留在海滩(2000千克/平方千米),剩下1%漂浮在海面上(18千克/平方千米)。
不同来源的塑料进入海洋环境及其分布情况 | 绿研团队译制
因此,本简报重点关注作为末端治理环节的海洋废弃塑料(不包括微塑料和纳米级塑料)治理中的截流与移除工作:在全球致力于减少环境中的塑料废弃物、优化塑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背景下,防止陆源废弃塑料入海、防止废弃渔具弃置、管控海运过程中的废弃塑料排放以及清理现有海洋漂浮塑料,构成了应对海洋废弃塑料问题的四大关键途径。本简报对这些关键途径所涉及的现有技术和商业解决方案及其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并辨识出在截流与移除海洋废弃塑料过程中蕴含的投资机会以及政策需求。
治理海洋废弃塑料的关键途径
陆源塑料入海主要通过沿海地区直接排放和河流从内陆输送至海洋,其防治工作需要防止陆源塑料进入水道或清除水道中的塑料,以阻止其最终流入海洋。海上活动产生的废弃塑料主要来源于泄漏到海洋的渔具和海上航运产生的其他废弃塑料,防止海源塑料入海需要重点防控这两类来源。过去塑料的生产与使用导致海洋中已累积大量废弃塑料,现有海上漂浮塑料的清理问题亟需考虑。以下将从问题本身重要性和特点、国内外对应政策规制框架、具有代表性的技术方案及其效益、不同类型资金参与机会等角度对拦截和移除海洋废弃塑料进行简要分析。
(1)防止塑料从河流入海
陆源塑料是海洋废弃塑料的主要来源,它们通过多种途径进入海洋,包括沿海地区的直接排放(如通过河流运输、直接丢弃、潮汐运输、风力运输等)和河流从内陆输送至海洋。
规制框架:1972年《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规定,缔约国需要采取措施有效控制所有污染来源,防止污染海洋。中国作为公约缔约方,履行防止倾废污染海洋的义务。针对防止陆源塑料入海的工作,2020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将开展江河湖泊、港湾塑料废弃物清理作为治理目标,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明确了不同主体的权责分配,2024年施行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增设条款为相关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技术方案:对于塑料等废弃物的拦截,城镇给排水系统中已有相应的技术实践。这类拦截活动处于塑料生命周期的上游,对塑料的拦截行动发生在越上游的环节,拦截的效果越好(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河流处于塑料全生命周期的中游环节,从河流中捕获塑料可以有效减少海洋废弃塑料。目前从河流中捕获塑料的技术创新主要有两类:直接清除技术和拦截清除技术。直接清除技术通过驳船等装置设备将河流中的塑料收集到装置内,再运输到岸上集中分类并回收;拦截清除技术则通过围塑网、围塑栏等装置设备将河流中的塑料截留并集中到岸边以待收集和回收利用。
资金支持:上述技术创新完全依赖于公益性的资金支持,社会公益资金的参与对于技术的成熟至关重要,包括商业赞助、基金会捐赠、私人捐款和众筹等方式。这些技术目前主要处于试验、试点和小规模投入使用的阶段,若要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可能面临更大的资金需求。在一些项目中,市政府是项目委托方,可以提供一定的财政资金支持;当地相关政府部门是项目运营主体,负责清除设施的运行和维护,同时也是清除设施和回收塑料的所有者。由此可见,初创企业或组织的技术创新所服务的最终客户是政府。在这些项目中,投资者可能有机会找到一些同时实现环境效益和投资回报(主要来自于财政资金)的机会。而上述企业的商业化前提是自身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成本下降和政府用于购买这些技术的相关预算的增加。这也解释了为何这些项目大多在较富裕的国家发生。但从河流中清除塑料的行动与上述上游的拦截行动相比可能不具备优势,因此相应技术在获得资金的竞争中并不具备优势。
(2)防止渔业作业泄露渔具
在所有海洋废弃塑料来源中,对海洋生物多样性最具威胁的是渔业作业泄漏的塑料渔具。这类渔具为废弃、丢失和丢弃的渔具(ALDFG),通常被称为“幽灵渔具(ghost gear)”。过去数十年来,随着渔场扩张、捕捞强度增加以及渔具材料向更耐用和浮力更大的方向发展,进入海洋的渔具的数量、分布范围和影响都大幅增加。
规制框架:粮农组织(FAO)建议的减少渔具海上丢弃的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鼓励预防性行为,包括使用渔具标识来确定其所有者,鼓励其对渔具进行负责任的管理;改善报告和回收的机制和方案,提高渔具丢弃的透明度和回收的效率;管理渔业行为,避免非法捕鱼和高风险捕鱼。国际法中,渔船的管理责任在于船旗国。中国将治理渔网渔具归属于建立和完善农村塑料废弃物收运处置体系之下。2020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将规范废旧渔网渔具回收处置作为治理目标,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明确了各部门的权责划分,2024年起施行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则增设条款提供法律依据。
技术方案:治理渔具的工作可以分为“预防性”和“补救性”两类措施。预防性措施主要集中在塑料生命周期的上游,包括减少塑料用量、废物收集、回收利用和污染预防等,旨在减少渔具问题。预防性措施主要涉及改进渔具的设计、生产材料和技术,制定和应用可持续性标准,加强执法和海洋空间规划,建设回收渔具的港口设施,以及加强对各利益相关方的能力建设和激励。补救性措施则主要针对减少渔具在海洋环境中停留的时间和产生的影响,主要围绕渔具的监测、报告和回收而展开。补救性措施相较于预防性措施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而预防性措施在减塑方面更具影响力。预防性措施需要广泛实施才能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实践仍以回收渔具的补救性措施为主。
资金支持:减少渔具的丢弃和遗失高度依赖于渔民行为的改变,因此,相关政策和项目需要为渔民提供足够的激励以促进这一行为改变。如果缺乏后续的高价值再利用,仅靠公共资金或自愿行为在废旧和遗弃渔具收集上所能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对于投资者而言,塑料再生企业利用回收渔具的项目可能存在一定的机会。这些企业如果能够协调港务局、渔业协会等利益相关方,建立起渔具的管理体系,就可能形成一些新的商业机会。然而,企业搭建这一体系的过程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关注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投资者和资助方可以对这一过程予以支持。此外,影响力投资者也可以关注涉及渔具管理的渔业管理改进(FIP)项目。此类项目不仅可以整合资源以降低总体成本,还可以确保渔具管理的实施效果。通过管理改进,渔业项目可以形成价值上升的渔业资产(如捕鱼权、渔船、海产品加工设施等),这些资产的提升有可能为投资者带来投资回报。
(3)防止船舶倾倒塑料
海运塑料是指海上航行的船舶产生的进入海洋的废弃塑料(除渔业作业中泄漏的渔具外),包括在航运、捕鱼、休闲船只和游轮上产生的、意外或故意弃置的一般废弃塑料。继前文所述捕捞作业泄漏的渔具之后,海运塑料是海源塑料的第二大主要来源。从船舶上故意向海洋倾倒塑料违反国际法,但这种做法却普遍存在,并随着商业航运的发展而不断增加。
规制框架:《伦敦倾废公约》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有效控制所有污染来源,防止海洋污染。21世纪以来,国际海事组织(I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国际组织持续推动各缔约国制定或修改相关法律文件,形成了以《伦敦倾废公约》为基础的管制海洋倾废(包括塑料废弃物)的法律文件体系。关于防止海运船舶倾倒塑料入海方面,中国在立法和执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1983年):第七章对船舶垃圾的管理提出了初步要求,包括塑料制品不得入海。在权责划分方面,《“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2021年)明确交通部牵头负责督促船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收集、转移和处置包括塑料废弃物在内的船舶废弃物。在资源配置方面,中国目前没有针对防止船舶废弃物入海的专项财政预算,而是以交通系统的现有制度架构来落实上述工作。
技术方案:监测海上活动和违规行为历来困难,几乎无法将废弃物与特定船只关联起来进行追责。因此,船舶改进这方面行为的压力非常有限。该挑战与管理渔具丢弃本质上相同,因此解决方案也集中在港口的作用和有效激励的提供方面。与渔具相比,船舶垃圾的成分更复杂,更接近于岸上的生活垃圾。处置未在海上焚烧的塑料垃圾需要在港口与陆上的垃圾管理体系进行有效对接。
资金支持:在政府支持和优惠政策到位的情况下,以下几个领域存在可以投资的商业机会:一是海上焚烧技术的清洁化和高效化;二是降低监管成本的数据收集和应用技术;三是高效的港区垃圾收集技术和商业模式。特别是在整体塑料再生产业的发展和企业ESG要求的带动下,对海洋废弃塑料的溢价也提升了这些商业项目的盈利能力。
(4)清除现存海上漂浮塑料
基于洋流特性,现存海上漂浮塑料主要聚集于公海(五大环流垃圾带)和沿岸海域。关于海上漂浮塑料,最著名的是全球五大巨型废弃物环流,其中最大的是太平洋垃圾带(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海上漂浮的塑料制品会分解成塑料碎片乃至微塑料。塑料碎片越小,其浮力越小,会逐渐沉入海洋变成海底沉积塑料而难以清理。
规制框架:塑料污染治理国际文书的谈判草案已在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会议上汇集了各方提出的重点内容,特别设定了章节来探讨海洋中现存的废弃塑料问题。草案要求各缔约方需对海上漂浮塑料密集区或受影响最严重的区域进行评估、确认,并优先处理。中国对海上漂浮塑料的治理主要聚焦于近海区域,对此,2020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旨在通过港口塑料废弃物清理和海滩清洁活动来减少污染,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计划》明确了各部门权责分工,2024年起生效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提供了法律依据。至于公海区域,中国目前尚未制定具体的治理漂浮塑料的政策措施。
技术方案:对于现有的海上漂浮塑料,当前的主要解决方案集中在直接从公海中捞取塑料。太平洋垃圾带中的一些塑料已经在其中存留长达半个世纪,而且这片垃圾带仍在快速扩展。面对这一挑战,一些环保组织开始探索清除这些塑料的创新技术,并取得了初步成果。
资金支持:这些技术仍处于开发阶段,主要依赖于公益性资金。虽然公益资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此类技术的研发与初期应用,但当这些技术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在广阔海域的应用仍然面临成本高昂的挑战。因此,技术开发者和利益相关方需要明确这些技术后续的发展路径,并探索可行的商业化模式。回收的海上漂浮塑料的可追溯性为其对应的再生塑料制品带来环境溢价可能是机遇之一,但市场对此类溢价的接受度存在上限。若企业能通过创新设计提升再生塑料制品的质量,进而使产品的自身价值足以吸引消费者承担起环境溢价,便有可能构建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盈利模式。在此背景下,那些具备出色设计能力和能够生产高附加值塑料制品的企业,可以成为潜在的优质投资目标。
表1 截流和移除海洋废弃塑料的关键环节
注:绿色区域突出了绿色金融已经覆盖的部分,淡蓝色区域突出的是由于存在集中收集的渠道因而可能盈利的活动,蓝色金融可以在这方面提供额外的支持 | 绿研团队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投资机遇
对于防止塑料从河流进入海洋,现有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和社会公益性资金,投资者参与的机会主要在于可以投资承担政府部门采购的塑料截流和移除项目的企业,例如掌握了相关技术和开展技术研发的企业,投资回报来源于财政资金。对于渔业作业泄漏塑料渔具,在“预防”方面,投资者可以参与投资以渔具管理作为重点的渔业管理改进项目,投资回报来源于价值上升的渔业资产;在“治理”方面,投资者可以投资渔具回收再生及随后的高价值再利用环节,例如投资拥有塑料再生技术的企业和制造业企业,投资回报来源于渔具的高价值再利用。对于防止船舶倾倒(渔具之外)塑料,投资者可以投资于提供清洁节能的海上焚烧设备、组织港口垃圾卸载转运体系等的企业以及塑料回收再生企业和制造业的生产企业,投资回报的来源有待通过实践进一步探索和明确。对于清除现存海上漂浮塑料,投资者可以参与的机会更加有限,在海洋废弃塑料可追溯性认证带来的相关制品溢价的前提下,投资于具备优秀设计能力的生产高附加值再生塑料制品的企业可能可以带来投资回报。
表2 截流和移除海洋废弃塑料的关键环节
来源:绿研团队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结论
基于分析,本简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塑料污染治理政策体系可以进一步明确海洋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为海洋废弃塑料治理提供顶层设计和制度支持。全球塑料污染治理不断加强已成趋势,释放了明确的政策信号。在本文所讨论的四个关键途径的行动中,都需要政府的具体规制和引导。首先,制定塑料废物管理的强制性要求和激励性政策是船企等企业改变行为、配合塑料废物收集,从而避免废物进入水体的基本条件。其次,政府在财金方面的优惠措施和提高垃圾处理便捷性可以激励船舶采取更环保的行为。随着监管技术和信用体系的发展,这种激励作用可以进一步增强。此外,创新塑料废物收集的管理模式,例如建立政企联动的废物来源追溯体系,可以为海洋塑料废物收集及循环利用的环境溢价提供支撑。政府部门可以加强对海洋废弃塑料问题的识别和界定,引导私营部门投资者的参与。这些作用都是其他主体无法替代的。
第二,塑料废物截流与回收环节的经济效益存在差异,需要多元资金支持。目前面源的、已经进入水体的塑料废物的收集活动主要依赖公共资金和其他公益性的资金。多边开发银行主要聚焦在循环经济、固体废弃物管理等方面,减少塑料入海的同时也为收集来的海洋废弃塑料提供循环利用的机会。私营部门也通过塑料管理回收方面的技术创新来参与到上述的海洋废弃塑料防治活动中。一旦规制和引导政策进一步推进这些活动的规模增长,不同类型的资金需求也会同步增加。
第三,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对海洋废弃塑料防治活动的识别和界定,引导更多私营部门投资者的参与。相关产业和金融主管部门可以制定蓝色产业支持目录和蓝色金融目录并纳入海洋废弃塑料治理的关键途径。通过制定蓝色产业目录,明确海洋废弃塑料治理活动的类型与边界,有助于金融机构识别同时具有环境效益和盈利空间的海洋废弃塑料治理活动。蓝色金融的分类标准可以纳入的活动可以包括:(1)船舶塑料的收集及进入塑料回收利用体系前的预处理;(2)涵盖了改善渔具管理的渔业管理改进项目;(3)回收利用企业主动对接可溯源的海洋塑料。如果这些活动和项目所涉及的产品和服务可以被纳入到蓝色金融的标准和指引中,金融机构可以识别并支持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项目。
塑料废物越早被收集,其回收利用或处置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越高,这也是目前塑料管理的改进活动聚焦在完善陆地上的管理体系方面的原因。海洋塑料废物管理也同样高度依赖于提前截流和回收措施。目前,陆源废弃物的截流和回收的相关活动已被纳入绿色金融的框架之内。发展中的蓝色金融可以进一步识别和细化与海洋废弃塑料相关的截流和回收活动,支持政府与市场主体在这些工作开展更高效的协作。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