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7-08
2022-07-08
 1649
1649导读
2021年8月,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外交部、商务部审议通过《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这一《办法》使民间组织首次具有了参与中国对外援助体系的制度空间,被认为是揭开了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对外援助历史新的一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确实在海外做出了一些成绩,在人道救援、发展援助、环境保护等领域更加活跃。但是总体上,中国涉外社会组织的比例不达1%,很多社会组织希望“走出去”,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本文综合4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从业者的经验分享,针对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原因、做法、挑战以及建议和展望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l 佟丽华,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儿童法联盟主席
l 李博伦,Diinsider联合创始人
l 周静怡,Diinsider传播经理
l 何国科,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致诚社会组织团队负责人
为什么要“走出去”?
—— 社会组织肩负独特的使命与关怀
佟丽华:为什么要“走出去”?社会组织是非营利的,是有自己价值取向的。因此,我们要思考,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要传播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为什么往外走?想不清楚这个问题,就无法制定组织的国际化战略。
我认为,走出去需要考虑社会组织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能做哪些积极的事。比如为人类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做什么贡献?
盖茨基金会2020年的公开信里有一句话,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慈善事业不会——也不应该——代替政府或企业的角色,但慈善可以承担政府无法承担和企业不愿承担的风险。
因此,社会组织还可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承担更多创新的使命。怎么花小钱办大事?怎么最大化项目的效果和贡献?可以去尝试那些政府、企业无法尝试的想法,其中的一些可能带来社会进步的重大突破。
—— 全球发展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
李博伦:目前,国内很多社会组织主要是在公共服务中作为补充政府的角色,发挥一些辅助作用。但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社会组织能扮演的角色会更大,发挥更多积极作用。中国目前的对外合作项目中,政府的援助和大型企业项目还是占主导地位,因此,社会组织走出去可以丰富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参与。
我们经常讲一个概念叫“多元主体”。所谓多元主体就是有很多可以参与全球发展的相关方,不仅仅有政府/官方机构,也有非官方机构,比如企业、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等。在多元主体的参与下,更有可能丰富东道国对中国、对与中国进行发展合作的认知。
从工作形式上看,社会组织更灵活。社会组织可以更容易与东道国的社会组织合作,甚至是发起新的机构,如成立社会企业等等。这样在本土较容易开展工作,工作范畴和方式会多一些,与此同时依然可以和中国的官方机构合作。
在海外,社会组织可以做些什么?
—— 发挥中国的技术优势
李博伦: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涉及的领域是很丰富的。我们合作比较多的有从事全球健康、清洁能源、环境保护、社区发展类的机构,他们已经有海外落地经验。此外还有从事难民、儿童、性别、海外投资的社区沟通等工作的。
在某些领域与技术的结合可能是中国社会组织的一个优势。在这方面,企业基金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基因检测、卫生、新能源技术等方面,很多在海外有工厂或者有较多业务的企业成立了基金会,结合他们基金会自身的定位,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就具有技术上的优势。比如,一些中国医院在海外能做相对复杂、专业的手术或医疗救助,这也是一个优势。
何国科:一些慈善、扶贫济困类的慈善组织,他们在国内已经有非常成熟的项目,可以推广到国外。尤其是通过互联网手段开展的慈善项目。国内比较领先的互联网公益模式和互联网筹款。比如蚂蚁森林、蚂蚁庄园,这都是新的一些玩法,我认为这些经验在国际上是可以宣传推广的。
我们很熟悉的社会组织大部分是公益慈善类的社会组织,但其实社会组织的类别很广。除了公益慈善类的,还包括一些民办的学校、医院,以及行业协会商会等等。在经济、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各个领域,社会组织都在发挥很大作用,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
有些事情,政府、企业是做不了的,比如制定国内、国际的行业标准,这需要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去做,社会组织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 更进一步,制定国际标准
何国科:那么,中国的社会组织能不能去制定国际标准,建立国际体系?我们服务的一个机构是建筑领域的行业协会,中国在这个建筑领域的原材料生产占到世界产能的70%以上,非常之大。但是这个领域国际标准是谁制定的?并不是中国企业制定的,是外国协会制定的。
进一步来说,在科技领域,我们的人工智能、5G已经发展到世界前列,但这些领域国际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并不在我们自己身上。为什么国际标准只能是外国的NGO制定?我们国内的社会组织,比如行业协会商会,能不能走出去,去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标准的制定?建立产业或行业的标准,这也是需要社会组织去参与,也是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努力的方向。
社会组织“走出去”面临的挑战?
—— 内外交错的结构性挑战
佟丽华:第一,在大的政策背景上,我们国内总的来说还缺乏一套行之有效、可操作的法律政策体系,包括资金怎么走出去,包括跟国外的社会组织怎样进行合作等等。
第二,我们缺经验。中国的社会组织走出去到底怎么做?发达国家很多社会组织已经摸索出来一些经验和方法,我们目前的总结并不够。
第三,我们缺人才。人才是非常难得的,既得了解在国际上应该怎样开展工作,又得了解国内到底什么情况。不仅仅是语言要求,更要对中国社会组织和相关领域的情况都不了解,其实对人才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因此,我们缺政策、缺经验、缺人才,也缺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组织走出去面临相当多的挑战。
—— 生态系统还没形成,海外项目的可持续性并不好
李博伦:目前,所谓的“圈子”或者说“气候”还没形成。比如,在特定的一个区域或者一个领域,中国的社会组织目前还比较稀少,而且项目不是特别稳定和可持续,项目的长期影响很难去叠加出来,这样就可能经常会有一种浅尝辄止的感觉,相对而言话语权会弱一些。
而且,大部分社会组织还有自身运营的各种压力,所以目前在海外或在发展中国家有长期、规模化影响的项目,还是比较少。
为什么海外项目难以做到可持续?我接触了很多机构,有的是自己的原因,比如对具体工作的认知有偏差、不是很适合在海外开展工作;有的可能是主要合作伙伴或资助方存在一些问题,或者是当地环境和情况发生了变化等等,很难说是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可能是多个因素叠加、共同存在的。
—— 认知上还有“真空地带”
李博伦:一个海外项目或一项工作做得好不好,有时候取决于“工作能力”,更多时候取决于“态度”,最常见的是“认知”问题。在一些比较极端的失败案例中,社会组织对海外情况、当地需求不了解,就盲目地往外走,还带着高人一等的态度,这是不可能真正做成事情的。
对于社会组织而言,意识提升、能力建设是很重要的。否则,大家可能会陷入“自弹自唱”的困局,不知道事情原本可以做得更好。
有时候,一些人不理解其他国家思考问题的角度,仅停留在自己的预设立场的时候,拒绝接受别人的立场。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要引起广泛重视。
倡导认知层面的转变,需要耐心和契机。很多社会组织的认知是在不断变化的,而认知又受到包括来自资源方等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
周静怡:个人体会,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海外真实需求及当地人的想法之间,可能存在一个“真空地带”。我的同事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调研时,发现了一些类似这样的“真空”。他们把这些观察写成一部小说,叫《新城与旧序:西哈努克港之浮世绘》,里面有一句话:“一座城市,在中国人和西方人、投资者和援助者、外来人和当地人眼中,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文中提到一个典型例子,一个国际NGO想改善当地孩子教育不足的问题。于是,他们去劝说父母不让孩子打工,来免费学习。一位家长直言,“不行,去接受教育和培训是不可持续的。”在深入了解后,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假如一个柬埔寨女生学计算机,她除了自己创业,几乎没有好的工作可选。这个国家的机会太有限了,所以大家才必须拼命抓住眼前机会。
因此,在当地的需求和这个NGO的工作之间,一个真空就产生了。这种真空属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对未来发展有什么建议和展望?
—— 用交流、协作,改善生态系统
李博伦:现在,很多中国的社会组织在同一个地方做类似项目,其实大家可以组合一下各自的调研、评估和传播需求,避免重复劳动。一些伞型的、网络性的社会组织,可以多去进行类似的协调工作。
社会组织“走出去”是一个必然趋势。目前,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社会组织本身,对于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认知一直在提升。但这种认知或预期,不一定特别符合海外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在很多时候,社会组织是资源弱势的一方,需要大家互相之间不断合作、交流,进一步提升和拓展认知。
另外,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之间,在海外活动的分工上可以更加明确。政府应该资助更多的社会组织,但是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要有分工,要有不同的工作目标,这样社会组织在海外才能得到认可。
—— 期待社会组织与政策发展的良性互动
佟丽华:社会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怎么理解呢?
中国的社会组织走出去能做什么?现在还是一个讨论的命题,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可能也不知道社会组织到底能做什么,对国家发展有什么意义?制定政策的动力也不足。但是,我相信随着更多社会组织走出去,有越来越多不同的做法,它的意义就会展示出来,国内的环境也会更好。社会组织工作的开展和外部环境的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其实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的:总要有一些人去趟路,去探索。在你探索的过程当中,不仅有困难,而且有风险。你需要有创新的能力、创新的思想,还需要有敢担当的心理准备。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心态:总要有人去探索。探索的人多了,政策环境也就会改变。这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
案例: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有哪些经验?
佟丽华:从中国的基层出发,走出去到别处的基层
在最早的时候,国际化并不在我们的发展战略之中,也没有要主动“走出去”的这种意识,但我会进行国际交流、到国外考察,我的目标是很清晰的,为了能够更了解中国。这个过程也让我了解了世界。我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也去欧洲、澳大利亚考察过,跟很多国际组织有进行交流。因此,我对国外社会组织到底怎样发挥作用有过近距离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
2017年,我带着三位同事去日内瓦三周,全程参与了人权理事会的会议,而且开了两个边会。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标志着我们开始主动地参与全球议题,并且有了很多实际行动。

▲ 2017年6月,在日内瓦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
但是,这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全球治理是必要的,社会组织参与全球议题也是必要的。然而,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缺乏根基的。
社会组织要参与全球治理,依然要做实际的工作。我是从一个基层专业人员成长起来的,对中国未成年人、农民工权益保障领域有深入的了解,清楚实际情况,知道相关案件的来龙去脉。基层的专业经验让我能去参与国家层面的立法政策改革。
对于全球治理也是一样,要从联合国议题这种宏观的、更高的层面上走下来,要带着解决问题的思路,去做实际的、草根的、基层的工作。这是能给普通人带来福祉的,真正有意义的事。同时,有了基层的经验、解决了实实在在的问题,社会组织再“走出去”,也会更有底气。
所以,我们很快开始了一个新的国际化工作布局,关注其他国家儿童保护的人才和社会组织,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对他们的需求,我们往往会把握得更好。
首先,“专业”是关键点,也是痛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儿童保护组织,其实很需要能办案子、能推动法律政策改善的律师。我们做Global Child Law Fellowship,就是希望能分享一些我们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的专业儿童保护法律人才、社会组织的成长提供支持。
另外,“国际交流机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很重要,所以“走出去”以后,我们搭建了国际儿童法的平台,2018年开始主办包括“A20”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研讨会,是希望能为其他国家里更多的人提供这样的机会。
因此,“走出去”并不是一个前置命题,不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未来,我只希望更多的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有更多专业的儿童保护组织成长起来。其中一些组织能有优秀的法律专业人员。
当然,我并不想成为国际儿童保护领域中一个所谓领导者的角色,而是更想作为一个积极推动者的角色。从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谁做领导者”并不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命题,最关键的还是要看谁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有“合作伙伴”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互相学习、共同成长、平等对话,这也是我在国内各地设工作站,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思路。
在国际上的工作也一样。只有当地的儿童保护组织真正成长起来,才能更好地去承担相应的使命和责任。我不倾向于去很多国家设代表机构,或把人直接派过去。这么做无法解决他们国家所在领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无法发挥本土组织的作用。

▲ 发展中国家的儿童保护组织负责人来到北京,双方开展交流。
Diinsider:以全球发展为使命,理解受众的需求
Diinsider的定位是一个全球性的机构,我们希望关注全球的发展问题,同时也会调整在不同国家的工作策略,以适应、符合特定国家自身的需要。
在人员上,我们目前在每个国家只招募本地员工,还没有把中国员工派到其他国家去。在工作或项目的海外传播上,我们也会注意受众和角度,挑选侧重点。
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不同主体的需求可能是不一样的。援助方的工作有时候直接来源于受援国当地的需求,这很好。如果不是,我们希望能在其中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并且做一些倡导类的工作。
因为我们接触不同类型的机构,他们之间的诉求可能差别很大。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受众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Diinsider会做英文媒体,在非洲做倡导,在东南亚做项目,这些服务的受众都不太一样,提供的价值也不尽相同。因此,每项具体工作的受众是明确的,提供的价值是可靠的,那么它就有存在的意义。

▲ Diinsider联合创始人Gladys Llanes于菲律宾拍摄纪录片
Diinsider做国际传播,而且是为底层人群服务,把底层人群的故事、境况讲给非底层听。因此,我们在不同平台做传播工作,会考虑不同的目标受众,让传播效果更好一些。
Diinsider旗下杂志《创变》(Change)由菲律宾团队负责内容生产和运营,它是一个讲述草根群体故事的国际媒体平台。杂志作者是我们的“全球通讯员”,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可以去到当地的村镇,采集鲜活真实的一手信息。
这些故事的主要目标受众是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创新组织或NGO,我们除了说故事,还会提一些反思或建议。我们的目标是想促成当地基层社区创新,对这个行业里的不同机构提供借鉴和引导。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去改变一些情况,帮助底层的人。
再比如Diinsider“中非健康与发展传播项目”的主要目标受众是中国的发展和传播工作者,致力于通过内容生产、能力建设活动、意见领袖互动等方式支持中非健康与农业发展合作等领域的传播和倡导工作,进而鼓励更多相关方参与中非发展合作,造福贡献非洲可持续发展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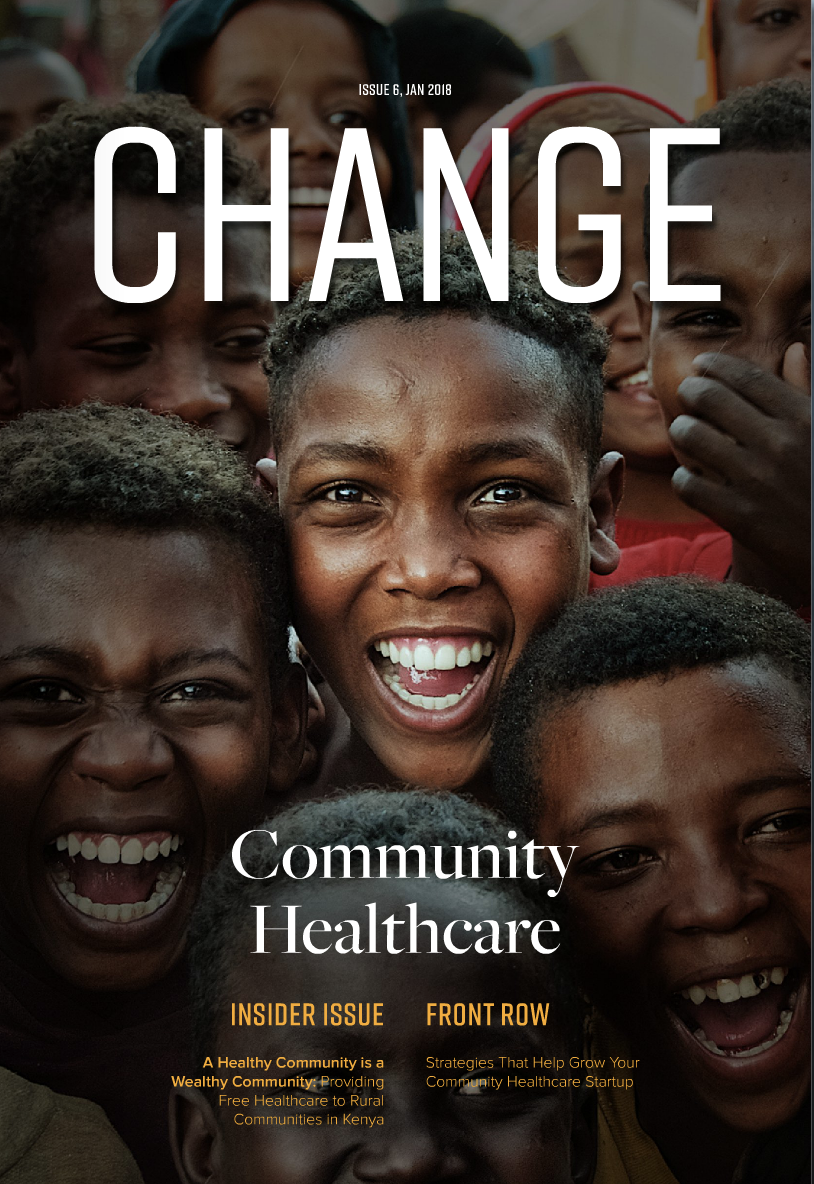
▲ Diinsider《创变》杂志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