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30
2022-06-30
 306
30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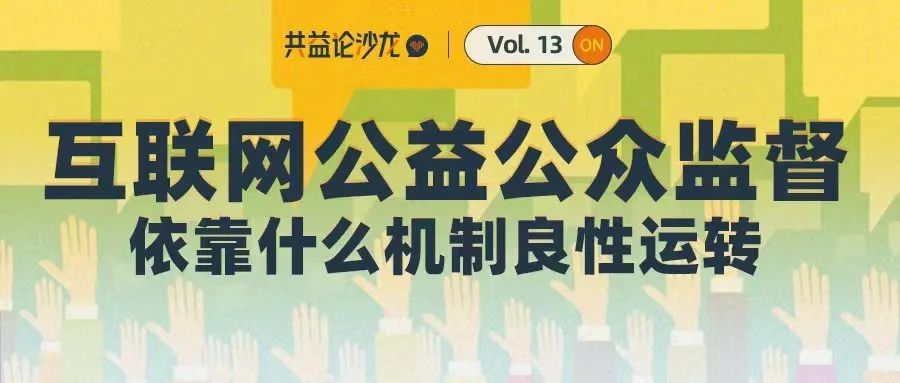
本文改编自“共益论沙龙”嘉宾分享内容,经作者本人审订
2022年5月,腾讯公益与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联合恩派公益、方德瑞信、七悦公益、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互联网公益公众监督行动”,接受公众对腾讯公益平台上的公益活动和项目进行监督。
在我看来,“互联网公益公众监督行动”并不仅仅是一个公众监督,而且是一个行业的协同自律。
从郭美美时期开始,就不断有各种让公众产生质疑的事件,这些事件既包括一些公益现象,比如说对某些公益组织的质疑,也包括一些实际上并不是公益现象,比如说在个人求助中的一些套捐现象,但都会涉及到人们的爱心。公众很容易把它们混同起来,最终认为公益不可信。
对待这样的现象,原则要清晰,但手段不用太激进。
因为,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单方面的问题,而是在目前的公益生态之下所产生的一种现象,这个现象中既有问题又有误解,然后又有各方面的可解决,和不可解决的因素。
如果说这个“公众监督行动”是谁的需求,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行业自身的需求,是公益组织自己的需求。它实际上是劣币驱除良币的问题发生之后,良币自己不想让劣币驱逐而产生的一种自证的需求。如果有某些规则没有被清晰地呈现出来,甚至根本就成为了一种潜规则,良币是没有办法按正常的方式运行的。
比如说,一个有权力的部门给你打电话,让你帮他办一个事,你不帮就会很被动。但如果一些规则被清晰地呈现出来,甚至建立了一个制度,再有这样的电话打过来,你就可以说,我特别想帮你,可是你看我帮不了。这个行业就可以保护自己。
目前的“公众监督行动”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规则呈现出来,当规则清晰地呈现出来之后,人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保护自己。比如逼捐,如果行业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不能逼捐),想要逼捐的人就可能会说不出口,就算他能说出口,但是对方也会有理由去拒绝。
所以,在原则上要清晰,但我为什么认为在手段上不用特别激进?
因为平台并没有执法权,平台也不是一个有权力的部门。平台更主要的作用不是个监督者,而是公益之中的一员,是参与者。而且像腾讯这样的大的平台,它还是一个规则的制定者和创生者。它就应该在规则的制定和创生的之中引导公益的方向,其实无论是逼捐,还是套捐的问题,都可以在规则的迭代演进中加以解决,规则本身就是一种筛选机制。
如果想要防止劣币淘汰良币,平台可以创生一种筛选机制,让良币更有利,然后让劣币作为一个理性的组织,意识它的某些行为对它自己也是不利的。好比说,不该放一条鱼让猫看着,又对猫说不能去抓鱼,这种考验就很残忍。可以让猫和鱼之间有一个屏障,比如说有一个笼子,甚至有一个隔墙板,让猫根本看不见鱼。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理性的猫,它就会扮演它应该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天天惦记着不属于它的鱼。
这种理性规则的制定对于平台而言特别重要,而这些规则也是需要去摸索的。腾讯公益今年提出了对一些好组织进行奖励,包括提高月捐的配比等等,其实就是规则的迭代。我觉得在迭代过程之中,它本身就起到了监督作用,而不一定只是接受举报再去查处。
只要规则迭代的方向是良性的,一定会产生出一些更有利于良币而不利于劣币的,甚至让劣币自己就想去转变成良币的机制。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很多套捐、逼捐行为其实都是长期的现象,现在主要的举报都集中在大病筹款,但其实大病筹款并不是一种典型的公益现象,而更类似于个人求助借了公益的平台,以公益的形式在出现的一些现象。
这是因为公众在捐的时候,很多人想要捐给自己知名知姓的人,而不是捐给一个公益组织,就更不用说是一个行业支持型的组织了。个人求助,目前在中国远远比公益筹款要兴盛。
这个现象表明中国公益依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甚至还没形成一个公益生态。我们有公益相关的需求,也有人们的爱心,但在需求和爱心之间并没有一个公益生态把它们对接起来,大多数人依然基于爱心直接对接。
这个时期,公益行业需要要回到公益目的的本身,把个人求助慢慢地识别和引导出来,也就是要在规则层面,让那些真正有公益目的的组织呈现出来,个人救助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呈现方式,两者的区分是很重要的。
在具体的解决方法上,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在混沌之中试图去改变旧的观念,改变旧的环境,但确实非常难;另一种思路是创建新秩序,把良币作为种子,然后让这样的种子不断地生长扩延,进而让一片土地变得越来越肥沃。而劣币的一边,也不一定要怎么去对付它,如果良币发展得好,劣币相对就弱化了
第一种思路是一种抑制性的策略;第二种思路是一种提升性的策略,让好的规则生成出来。
首先要看到,公益行业里的组织并不是都处于同一层面的,有一些公益组织直接面向受益人,也有些面向公益组织的公益组织。
这次参与发起“互联网公益公众监督行动”的公益组织几乎是不直接面向于受益人的,属于公益行业之中的二级结构,他们是公益组织的支持者、联合者,是公益组织的再组织化。
公益组织至少可以分成两个大类,而且公益行业并不仅仅只有两层,面向公益组织的组织完全可能形成更多的层次,在此之上,是服务于公益行业的互联网平台,然后才是实施监督的主体,不管是公众监督还是政府监督。
不同层次的公益组织,承担着不同层次的责任。如果要看责任主体,应该遵循自下而上的递进性原则,也就是说,直接面向受助人的公益组织去筹款、去花钱,它是一级责任者,出了问题首先是它自己的责任,然后是行业的自律责任,包括平台的责任,最后才是监督者的责任。
同时,监督者的责任和公益参与者的自我管理或说行业自律的责任不太一样。行业自律可以说一直在路上,永远可以做得更好,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追求;但公众监督、特别是法律监督,应该是底线责任。
监督者的责任,不是要求怎么做得更好,而是不允许有人突破底线。比如说不能欺骗、不能去诈捐,不能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这两种责任之间要有一个明确的区分。
其实,监督最好是建立在一个丰富、有效的行业自律之后,有一种总是用不到监督者的感觉。就像一个好的法律体系,它的法很完善,但是最好总是碰不到它,而不是靠打官司来进行日常的运作。公益行业也是一样,如果日常要通过监督来运行,这就不正常了。一定是监督规则作为遥望的警戒线,促使公益组织明晰自己的责任。
所以,互联网公益想要得到有效的治理,还得依靠行业自律,而公益的组织原则,一定是一个自治性的原则。
在自治原则下面,责任体系应该是要自下而上地去推演的。同时,每后一层次的责任是要去辅助前一个层次实现它的自治。这里要提到一个概念叫“辅助原则”,辅助原则的核心理念是,在特定公众和组织无法自主实现某种目标时,高一层级的组织应该介入,但仅限于出于保护他们的目的;并且,高一层级社会团体或者政治组织只能处理那些低一层级的社会团体或者政治组织无法独立处理,而高一层级的机构又能更好完成的事务。
根据辅助原则,每一层的公益组织都应该去明晰自己的辅助对象,也就是说,他要帮助前一个层次去实现他的自治目的。换言之,最好的监督就是帮助公益行业实现它的自治、自律。
而公益行业在进行自治与自律时,应该要促进和帮助公益慈善组织实现自我责任,进而帮助受助人实现他的自我发展。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公益组织不是要去施舍,而是要去帮助公众实现自治;整个行业也不是要去告诉公益组织该做什么,不做什么,而应该是支持公益组织的自治。这就是一种自下而上递进的自治原则,同时,每上一个层级要去帮助下一个层级实现他的自治。
这样的自治原则下,从公众到公益组织、行业支持类的公益组织、平台,行业联合体,最后是公众和法律的监督,所有的主体都在这个体系之中有不同的定位,有不同层次的参与。
我期待腾讯公益平台更多通过规则的迭代,去成为一个新秩序的创生者。这样公众不仅仅是一个监督者,也是参与者和选择者。通过新秩序、好秩序的创生,来实现公众的良性选择。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