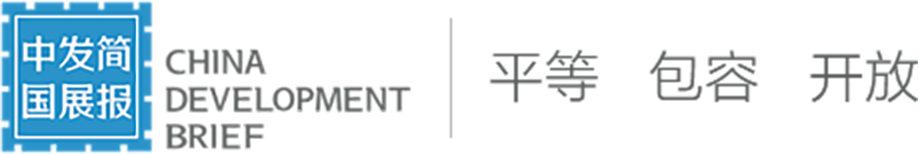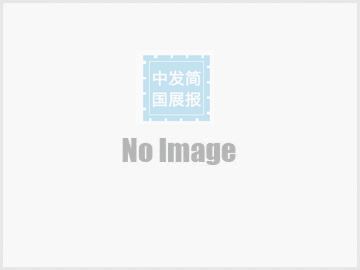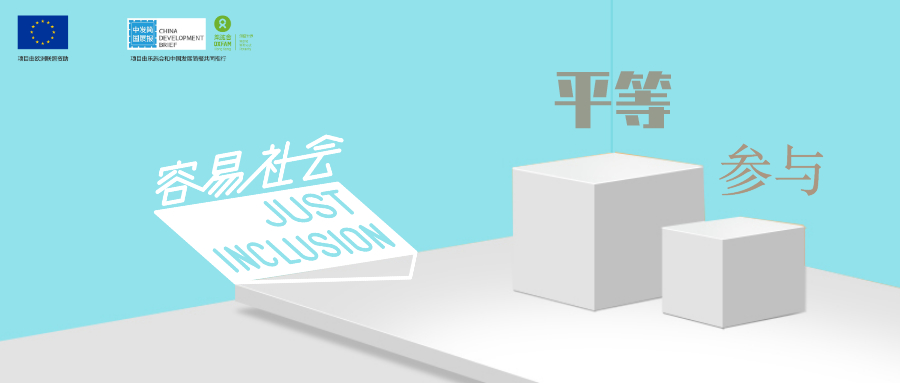2021-03-08
2021-03-08
 5350
5350
作者 . 手记
人总是难以摆脱刻板印象,就比如我,因为要采访一位重症肌无力患者,总预想着会听到一个很苦、很艰辛的故事。
“那么,现在您怎么看待自己的疾病呢?”我慎重的问。
她异常爽朗地说:“现在我并不觉得它是个可怕的病。你想,高血压、高血糖,还有痛风什么的,不都是治不好也不会死的病吗?这不过是人间百态中的一种。”事实上,她是一个生而自由的人。
“那是一种没有尊严的生活。”
周亚生在云南,长在云南。大学时她赴天津读书,学的是新闻传播学。毕业后,她刚好遇上纸质媒体的衰落期,于是去了杭州一家化妆品公司做企划。
周 亚 (作者供图)
那时,她意气风发,对自己的未来发展十分清晰。二十多岁的年纪,写字楼里的朝九晚五,刚接手了公司的一个项目,因工作压力太大崩溃痛哭过,也因颇有希望晋升满怀欢喜。她恋爱甜蜜,事业起色,设想着在杭州安顿下来,结婚生子,过美满的家庭生活,然后某一日回云南终老。
转变开始于2012年的夏天。在公司的安排下她去甘肃平凉做公益,给那里放暑假的孩子讲讲课,也记录当地的生活百态。习惯于摆弄单反相机的周亚在某一天突然发现,她再也拿不稳相机了,画面在镜头里不断晃动,无论怎么努力,也握不稳相机,“感觉不受她控制”。
起初,她像许多重症肌无力患者一样,觉得自己“只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就会好转。可是,当热情的甘肃孩子给老师送来新鲜玉米,周亚发觉连玉米都啃不动、吃不下去了。于是,她隐隐知道,自己应该是得了什么病。
至今她还记得确诊重症肌无力那天,那位年轻医生对她说:“你还是回老家吧,想见什么人就见见,想做什么事就做。”她昏昏沉沉地从医院走出来,在西湖边一个人坐到夜幕降临,医生给她宣告了“死刑”,她思绪万千,不知道怎么办。
“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医院就在西湖边上。”周亚对我说,“记得很清楚,但我不记得是怎样从医院走到湖边的。”
周亚的病确诊得快,恶化得也很快。2013年端午节前后,周亚已经做不到生活自理了。那时,她住在陕西姐姐家,起床、吃饭、洗澡都要人帮忙,有时连话都说不出来。她记得自己为省力买了一支电动牙刷,但刷牙时即使靠在墙上也站不稳。上厕所时要有人搀扶,需要别人在一旁辅助才能把裤子脱下和提上来。至于洗澡,那更是一项她难以自己完成的“工程”。
一向身体健康、酷爱排球、时常扛着单反飞奔的周亚每天躺在床上,依靠别人才能做以前轻而易举就完成的一切事。这样的生活落差不仅让她自己难以接受,也震惊了一众熟悉她的朋友和亲人。
“那是一种没有尊严、没有隐私的生活。我连生而为人最基本的自尊都不能保持。”周亚回忆说,微微叹了口气。
“我选择有尊严人生。”
在那样暗无天日的消沉日子里,周亚遇到了一位很专业的医生。经过临床观察,这位医生分析:如果她不用激素治疗的话,不必承担激素的副作用,但可能要一辈子在床上躺着,什么都做不了。如果使用激素,会有一些副作用但她的症状可以很大程度缓解,可以完成日常基本生活。
周亚无法接受前一种生活,她要有尊严地活着。
“我那时候20多岁,一辈子还很长呐。”她对我说,“一辈子需要有一个人在床边照顾我。我想吃的东西吃不了,想看的东西看不了,想做的事情做不了。想到这些我宁愿承受激素的副作用,过有尊严的人生。”
所以,一直拒绝使用激素的周亚动摇了。她开始常年接受激素治疗,症状很大程度缓解。代价是,本来只有90斤的她像吹气球一样胖起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涨到了140多斤,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很壮实”的女孩。
“我也是个女孩子呀,怎么会不在意自己的身材呢?”周亚说,“但是首先我想像正常人那样活着,我没有别的选择。”
她还记得有一次下班,天下起了雨,而她自己没有力气把雨伞撑开。她试着向路过的人求助,但人们多是以怪异而戒备的眼神注视她,然后转身走开。后来周亚没有再求助,她是一路淋着雨回家的。
“但我特别能理解。”周亚笑着说,“大家会觉得,一个这么壮实的女孩还撑不开伞,这里面肯定有诈啊。”
2013年中秋,她在杭州做了胸腺切除手术。她的家人很担心她,于是一路从云南赶到杭州,但也只能远远地看着手术区的周亚。实际上,周亚姐没有向我描述很多她关于手术台和病房的记忆,只是很平淡地说,她对那年中秋的月饼都没有什么印象,姑且算得上一点小小遗憾。
同样被平淡描述的,还有那时爱人的突然离开。周亚手术后恢复得不错,已经能够恢复工作了。但就是在一个下班后的傍晚,她回到家,发现男友带走了他所有的行李,并且删除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从此杳无音信。
“那,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联系吗?”我问。
“没有联系了,后来就一直没有再联系。”周亚说,“本来那时候已经打算结婚了。”
“这只是人间百态中的一种。”
“那么,现在您怎么看待自己的疾病呢?”
其实这是我最抗拒的问题。当做这样一个提问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是残忍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问题是在期待一个经历不幸的人对你承认,不幸是命运的馈赠而非命运的不公。
好在周亚并不介意我言语间的迟疑。她异常爽朗地对我说:“现在我并不觉得它是个可怕的病。你想,高血压、高血糖,还有痛风什么的,不都是治不好也不会死的病吗?这不过是人间百态中的一种。”
在她看来,一切都不过是选择。得病与否,就像高中时选择文科还是理科,毕业后选择当医生还是老师一样简单。人们不断选择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一点点累积成为不同的人生。唯一的区别在于,重症肌无力是一个被动而非主动的选择。
“我大概知道如果不生病的话,我的人生轨迹会是怎样的。”她说,“患病突然让我的生活多了很多未知,让我走了另外的一种人生,我觉得这也还算不错。”
而这个被动的选择对周亚而言,还意味着一颗对美好之物更敏感的心。她说,假如没有生病,自己大概会像之前认识的前辈一样,升职、赶飞机、加班、跳槽,忙到两眼漆黑,可能会遇到有趣的人,也应对着数不清的挑战。
“可是那样的话,就不会知道杭州的西湖是什么时候开始飘雪,不知道树是什么时候绿,花是什么时候开。”周亚说。
恰恰是在得了重症肌无力后,她才开始发觉杭州是一个多么适合闲散而居的美丽城市。她去花园闲逛,去植物园观光,去灵隐寺散心。喜欢听溪水叮咚而鸣,也爱看脚下野花绵延远方。因地铁里便利的无障碍通道而惬意安心,为朋友、家人相处中自然而然的搀扶与关切倍感暖意。如果身体状况允许,她也会像患病前那样,拿起单反边走边拍,累了就原地休息,回家还能用拍到的照片练习修图。
“生病之前,我感受不到这么多美好和善良。”她这样说。
而在最初的逃避与抑郁后,在数次复发、数次好转后,她已经能把自己的疾病当玩笑话和旁人提起。朋友时常打趣她说“我就不欺负你这个肌无力的人了”,她就顺势佯装无力地端着水杯,嘴里喊着“哎呀,快来帮我这个无力的人端杯子吧”。
现在的周亚身体状况已经稳定下来,只要按时服药、定期检查就能维持正常生活。她笑称自己为“一个看起来除了胖一点没有其他问题的人”。她从杭州化妆品公司辞职回到家乡,在普洱开过客栈,又尝试和朋友一起做云南竹笋的生意,把新鲜的当地笋运往全国各地,成为人们餐桌上鲜美的笋片。
“我算是看过外面的世界又回来的人。”周亚说,“我们这里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因为偏远不被外人所知。如果能把这些东西传递到更多人的手中,我觉得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这些年里,她也一直关注着身边重症肌无力患者们的生活。她和病友们一起徒步观光,去医院探望那些病情严重的患者。她说,比起那些健康、正常的普通人,她的出现会给病友们更感同身受的慰藉。
“我因有人驻足聆听而感激。”
要如何形容呢?听周亚讲话时,你会觉得她是一个自由的人。她的生命不属于痛苦,不属于风雨,不属于大道理和传统思考,而只属于她自己。即便不再能如往常一样自在奔跑,即便她的四肢被病魔束缚,你也依然感觉到她灵魂的自由。那份自由里有杭州的雪、普洱的花,平凉的玉米穗,有尊严、勇敢、善良与热忱。
“现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太多的信息要接触,不被理解是正常的。”周亚对我说,“但如果有人愿意听一听我们的经历,愿意去理解,我会觉得很感激。”
聊天接近尾声时,周亚姐轻快地对我说“朋友来接我了,我等下又要去忙啦”。而我挂掉电话后沉思了许久,想的是,但愿患者们都能像周亚姐那样好好生活——有尊严,有自由。而这两者,往往最简单也最难得。
延伸 . 阅读
重症肌无力 是一种神经免疫性疾病,因神经传导障碍引起全身骨骼肌无力,可治疗、不遗传,病情呈波动性。一般症状可能出现眼睑下垂、面肌僵硬、咀嚼吞咽困难、抬头困难、举臂困难、登高困难、呼吸困难等。通过服用抗胆碱酯酶抑制剂、激素、免疫抑制剂、胸腺切除手术治疗,可以缓解病情。据《重症肌无力专家共识》的发病率推断,我国可能有65万重症肌无力病人。由于免疫性疾病受到环境、情绪、生活节奏等诱发因素影响,任何人可能后天发病。近年来,发病率和患病人口也在呈逐渐上升态势。
2018年,重症肌无力被列入《中国罕见病名录》
作者简介
杨天慧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科班出身,爱力传播志愿者。在《南方都市报》实习期间,开始关注重症肌无力患者群体,未来希望成为一名有深度有温度的媒体人,前行路上温热赤诚,质朴始终。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