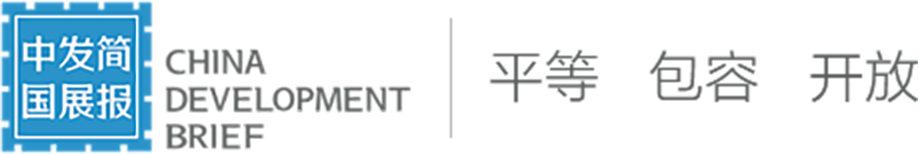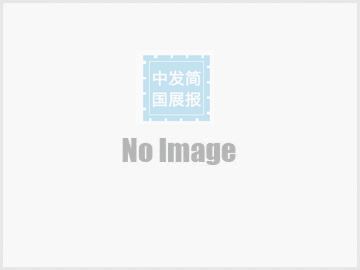2012-05-11
2012-05-11
 2415
2415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东北部的 9级强震和海啸给日本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地震和海啸引发的福岛核电站爆炸和核泄漏、核辐射,同样对周边社区乃至日本全社会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创伤。随着时间推移,来自大自然的直接伤害正慢慢消退,但福岛仍将长期被置于难以消弭的核辐射阴影之下。 2012年1月13~15日,核事故发生接近一年之际,应日本NGO--和平之船国际(Peace Boat International)和东亚环境情报所(East Asia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Center)邀请,笔者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其他来宾参加了为期一天的福岛当地社区考察,并于14~15日赴横滨参加了全球无核化大会(Global Conference on Nuclear Free World)。短短3日之内,除实地了解到福岛县居民所处的种种困境,还见证了日本国民高涨的反核意识。来自全球各地的NGO行动者,正通过行动呼吁世界各国放弃核能,探寻可再生能源的替代方案。1月12日,笔者和“蔚然大连”的程淑玲女士一同从东京乘坐新干线,在夜幕中抵达福岛市,入住离车站仅仅步行1分钟距离的酒店。当晚空气清冽寒冷,地面上的积雪还未消融。抬头仰望,夜空中似有星光闪烁,路上行人稀少,时有汽车驶过,并未感到异样之处。只有在晚餐时分,主办方向来宾致辞,谈起福岛的现状和第二天访问临时安置点以及受辐射影响社区的行程,气氛才开始有些凝重。尤其当发言人告诉大家,第二天的最后一站是遭受地震、海啸和辐射三重打击的南相马市,将乘坐大巴穿越一段政府划定的撤离区,心情才有些紧张起来。
“台湾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徐诗雅小姐对笔者坦言,来福岛前自己一度对此行的安全问题非常担忧,因为一直跟踪福岛核事故,了解情况的严重性。3.11地震后,日本政府对有关核电站的信息发布一度相当滞后,并不明朗。台湾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第一时间与福岛关注核能的当地团体取得联系,持续将事故情况和辐射污染情况向台湾岛内传递,比媒体还快。但担忧归担忧,因为亲历福岛是难得的机会,也是职责所系,于是她就“豁出去了”。入住福岛当夜,全球各地远道而来的近100位来宾中,一定有人和笔者一样,怀着有些忐忑的心情入眠,或者无眠。
来自民间的真相
第二天早上8点半,一行人浩浩荡荡从酒店步行到附近的福岛会议中心,听取当地NGO和社区组织介绍情况。刚出酒店,韩国NGO代表就拿出测试仪,放在地上检测辐射量,引得大家纷纷对仪器上的数字围观拍照。测得的数值是每小时1.011微西弗,是常规安全值的10倍。福岛市是福岛县首府,位于福岛第一核电站西北60公里。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尽管位于政府划定的禁区外,但辐射水平仍然非常高,对长期居留的当地居民而言,影响可见一斑。
当地NGO代表和来宾们挤满了会议室,在过道上站立的各国记者的长枪短炮包围下,福岛NGO代表轮番介绍核辐射的影响和社区的应对行动。
对于福岛居民而言,异地疏散造成了普遍的家庭成员骨肉分离。核事故导致被迫撤离的周边人员达到8.5万人(Nuclear Monitor 730,2010年7月15日)。福岛大学助理教授、灾害响应研究所(Institute for Disaster Recovery)的创办人丹波·史纪(TAMBA FUMINORI)组织完成了一项针对3万人的调查,发现81%的受调查者因为撤离辐射区被迫与家庭成员分离。远离家乡的人们至少要在异乡滞留5年,他们对何时能够回归家园感到迷茫。
“政府宣称辐射污染已经被控制住了,没有人相信!” 史纪表示。政府从“化解居民恐慌,打消不必要的担忧”原则下出发进行了健康调查,做出了“辐射影响非常有限”的结论,但NGO通过独立的民间调查提出了质疑。根据会议现场发放的资料,2011年9月9日,日本一家反核组织(Fukuro-no-Kai)发布了一份监测报告,根据7月22~26日抽取的15例福岛儿童尿液进行检测的结果,发现通过呼吸和饮食渠道导致了明显的体内辐射,建议政府对当地儿童进行全面体检并考虑预防措施,扩大撤离区的范围。
同样,NGO根据自己的调查发现,至今仍受到严重污染的福岛县Watari 区尚未被政府划定为撤离区。从2011年6月到10月,当地NGO多次根据检测到的高辐射和土壤高污染数据,与政府交涉要求将此区划为撤离区,但遭到了拒绝。即便是希望远离辐射,一些居民因为担心失去工作和家庭分离,也不愿搬离。
福岛市民MARUMORI Aya 参加过一次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会上,政府试图让公众打消疑虑,告诉大家污染已经控制住了。Aya 质问政府代表:“你们是怎样从福岛的5个不同地方的检测点获得数据的?”对方的答复却让她大吃一惊:“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数据。”
“政府是在没有数据支撑的情况下做出了政治决策,”Aya说,“我们有权利自己决定在必要的时候是否撤离危险区。”按照史纪的统计,出于对辐射问题的担心,在政府划定的撤离区之外,还有5万人选择志愿撤离,其中福岛有1万人。
相比之下,转移到安全区的儿童是幸运的,但也出现了寄读儿童在学校被歧视的情况。“福岛核电站所发电力其实并未用在福岛,我们持续20年向日本社会供电做出了贡献。” 因为孩子受到歧视,一位母亲觉得这很不公平,向史纪哭诉。史纪在会上告诉大家:“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担心福岛核事故会慢慢被外界遗忘,成为福岛自己要去独自面对的问题。”
福岛市民的行动
与以前的多起大灾一样,相比政府表现的不尽如人意,日本市民再次显现了很强的自治能力。由于缺乏国际通行的核辐射安全距离和污染标准,福岛市民只能自行采取措施应对。市内各处辐射水平的分布并不均衡,也无法采用日本中央或者地方政府的应对框架,Aya 担任理事长的市民放射能测定所(CRMS)在2011年6月应运而生。作为民间的独立第三方,CRMS在福岛设有9个监测点,在东京设有一个监测点,对室外辐射、食品、水和土壤成份进行检测和信息发布,并在专家学者和医生的支持下开展健康问题研究和儿童健康咨询,帮助市民提高防护能力。像Aya 一样,CRMS的发起者中有很多人是孩子的母亲。
参加交流会的几家日本组织都是福岛事故后成立的。福岛是日本著名的有机农业的主产区,除了有机种植户外,另外还有不少家庭正逐步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向有机农业过渡。核事故使土壤受到严重污染,当地的有机农业遭遇沉重打击。这些农户组成的福岛有机农业网络,现在转向了土壤除污和生态恢复。
妇女儿童在灾害中更是脆弱敏感人群,他们的健康问题成为NGO特别关注的议题。不少日本NGO和社区组织开展了儿童救助活动。Hiroyuki Yoshino是福岛救助儿童免于辐射网络(Fukushima Network for Saving Children from Radiation)的成员,他的妻儿已经撤离,自己留在福岛开展活动。由于留在福岛的孩子每天除了上学路上,其他时间都只能呆在室内,生活空间大大受限,该组织正在筹划一个项目,将滞留在福岛的孩子临时接到外面的安全地区生活一段时间再送回来,避免不间断地置于辐射危险中。日本地球之友等四五家组织也正在筹款开展类似项目,将福岛市内污染严重的Watari区内家庭转移到市内其他安全地区的旅店疗养几日。
由于政府反应滞后,福岛县有一个村遭遇强辐射两个月才撤离,村民们非常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一位村民说:“由于辐射的影响可能要10~20年才能显现出来,我们必须把现在的经历书面记录下来,作为证据保留。”人们已经意识到,核事故的影响,将持续到难以预见的未来。
伊达:难以言说的伤痛
从福岛会议中心结束交流,一行人前往半小时车程外的伊达市(离福岛核电站40公里),听取Litate村的奶牛养殖户、前田区前任区长谷川建一(Hasegawa Kenichi)讲述他的经历。
快要到达当地社区中心的时候,预计到这里的辐射程度会比较高,主办方在驾驶座旁边准备了口罩,请大家下车时自取。我拿了一个口罩,犹豫了一下没有戴上去,代表中也几乎没有人取用。在社区中心外面的安置房边,韩国NGO的仪器显示,地面辐射值超标数倍到10倍左右不等。进入会议室内,看到有人穿着塑料雨衣摆弄着摄像机,在心理上给人一种紧张感。
长谷川建一说,3月12日一号反应堆发生爆炸,3月14日三号反应堆发生爆炸。14日,他从辐射检测工作组专家那里获知当地辐射量已达到每小时40微西弗,当晚就急忙赶回村里,第二天召集全体村民告知情况的严重性并要求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3月15日,他又从记者口中,得知检测到的数据达到了每小时100微西弗,于是动员大家撤离。尽管从政府3月15~30日公布的当地辐射数据来看,辐射强度是在逐步下降,但长谷川建一并不相信,因为他从其他渠道得知的数据,最高的时候达到过每小时1 000微西弗。
Litate村民的生计来源主要是奶牛养殖。从3月12日到6月12日,养殖户们一直将污染后的牛奶倒掉。后来,无奈之下村民们集体决定放弃奶业。经过屠宰检测,需要将村里的奶牛运走杀掉。长谷川建一说,村里一位妇女眼见着自己的奶牛被运走,她追赶着远去的车子,难过地哭泣着。他自己也放弃了从事十年的制奶业。
更让人震撼的是,长谷川建一在邻村的一位奶农朋友,因为无法承受压力自杀了,留下7岁和5岁大的两个孩子。这位奶农精神濒临崩溃达到极限,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如果没有核电站,我的生活会一如既往。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去和核电站抗争。”他在遗言中这样写到。
长谷川展示了一张村民们外出到西伊豆堂一座岛屿旅游观光的集体照。现在,这个250人的村庄已经四分五裂,相片上的人们已四散迁移到不同的临时安置点,唯独这张照片留下了社区曾经的美好记忆。
但是,生存的希望并未泯灭。选择留下的村民们现在成立了24小时的志愿巡逻队,每月两次检测辐射量,并试图开展除污行动,慢慢恢复稻田的种植功能。但对未来,清醒的长谷川建一并无把握。他说,计划持续5年的除污行动,有可能被证明是一场徒劳的努力。村民们发现,辐射物在土壤中并不固定,而是通过水和风向村里的安全地带移动。就在考察团到达的当天,村民们还在当地多个地点检测到高辐射,而政府并未提出有效的回应措施。
随着时间推移,曾经成为全球新闻热点事件中的福岛,似乎面临着渐渐被淡忘的危险,长谷川建一正筹划到日本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他要告诉人们,不能忘记福岛,不能歧视福岛。这里的人们,还在直面辐射的威胁。
与Litate村的情况类似,由于缺乏有效的财政支持等种种原因,不少居民无法迁往异地,选择了留守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女家住伊达市和南相马市之间,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20公里。她说,她所在的社区被划定为撤离区。但是,社区居民对核辐射的危害缺乏真实了解,在突发的异变面前,在这里生根的人们还缺乏信心前往异地开始新的生活,除了选择留下来,似乎并无他途。在留还是不留之间,人们互相猜疑,邻里关系被割裂。在一家NGO的帮助下,这位母亲把孩子临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却被邻居指指点点,似乎她在做一件奇怪的事情。儿童伙伴之间也对此议论纷纷。在农村社区,多数老人固执地否认自己听到的有关辐射的信息,固执地鼓励或者强迫家人吃自产的蔬菜。而有的家庭担心孩子的健康,开始挑选食物的产地。这些变化像隐形的刀子,给原本和睦的社区打上创痕。
“你看着天空,似乎看不到任何区别,日常生活也一如往常,我们只能依赖电视台等渠道发布的消息,我们谈论这些问题,却无力采取任何行动。”这位妇女眼里充满无奈。在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下面,这里的人们在被动中默默承受着。
南相马:失落的非遗
离开Litate村,大家一路心情沉重,向距离福岛核电站更近的南相马市进发。南相马是座海滨城市,位于福岛第一核电站北面10~40公里,遭受了地震、海啸和辐射的三重打击。大巴车一路前行,所经之处的路边商店即便开着,也是门可罗雀,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各行业尽显萧条之态。
南相马的地理形状是南北纵深20公里的狭长地带,南部被定为撤离区或者控制区。海啸和核事故发生后,曾经7万人的南相马人去楼空,仅仅剩下1万人,现在慢慢恢复为4万人,略微有了一丝生机。
核事故前的每年7月,这座知名的旅游城市都要举办为期3天的赛马会(Soma Nomaoi)。赛马会是延续了1000年历史、能够回溯日本战国时代的著名传统文化盛会,是日本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由于核辐射的影响,现在被迫停止,迁往其他城市小规模举办。
现在,南相马的很多年轻人都撤了出去,城市失去了活力。老一辈们则坚守在这里,成立组织,采取行动,希望唤起年轻人对社区的信心。“我们希望继续在这里生活,这不是一座死城!”当地一位NGO代表说。
在政府支持不力的情况下,南相马的市民还成立了一个有30位专家支持的研究所,记录儿童医疗档案,开展去污研究和行动。年轻人高桥(Takahaxi)以前就在核电厂工作,发生核事故后,他在过去的10个月内一直钻研核能和辐射问题,在前来南相马提供救助的NGO的支持下,制作了辐射污染地图,为公众提供咨询,提高公众防辐射意识,推动公众自主决策采取应对措施。
在南相马,来访的代表们曾抵达离福岛第一核电站仅20公里的地方短暂停留。这里公路已被阻断,不再允许社会车辆进入。几位NGO人士拉起了横幅,对福岛核电站提出抗议。
由于13日这一天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凑,代表们当晚要赶回横滨参加第二天开始的世界无核化大会,大家的中餐和晚餐就在大巴和高速列车上吃便当解决。在不同访问地点之间乘坐大巴往来的间歇,主办方见缝插针,还安排当地几家NGO在车上介绍他们开展的工作。
外部NGO转型应对
核事故发生后,一些福岛以外的日本NGO,包括曾专注于海外援助的组织纷纷转移工作重心,投入到辐射受害社区的救助和倡导工作中。Saito先生是一家总部设在伊拉克的日本NGO的代表。1991年海湾战争中使用的贫铀弹,对伊拉克儿童产生了严重的辐射影响,罹患白血病、癌症和先天性畸形的比例大大增加。这家日本组织为伊拉克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援助。现在,该组织抽出部分资金帮助福岛儿童。
有着十年历史的日本自然育儿之友(Friends of Natural Mothering)是日本一家倡导母乳喂养、分享育儿经验的NGO,在全国有2000个成员。事故发生后,来自外部的在线咨询需求蜂拥而来,大部分都提到食物安全问题。由于福岛受到辐射的母亲的母乳内检测出了辐射物,原来的自然育儿经验已经不再适用。这家组织将工作中心转移到了福岛等地,寻求医学支持。他们主动与福岛议员讨论滞留孕妇的育儿问题,告诫母亲们注意选择安全的食物,对辐射超标区的母亲,则与专业医生接洽,提供咨询意见。
2011年6月,自然育儿之友组建了一个由20家NGO参与的全国性的防辐射网络,与地方政府对话,就学生安全问题与卫生和教育主管部门进行磋商。9月,又与福岛NGO联合举办了有关儿童的研讨会。2012年4月,还将组织福岛300名儿童前往东京参加一次会议。
在“出人意外”的福岛核事故之后,即便是从事灾害救助的日本NGO,也并不拥有现成的应对经验。上述两个例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NGO为参与应对,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进行调整的努力。受辐射影响的社区还催生了不少由居民自发生成的组织,这些组织与市民和外部NGO一起行动,探求真相,守望相助,一方面反映出日本国民的自治精神已积淀为应对危机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政府在核事故上的决策和应对措施受到了民间质疑,国民的知情权和参与决策权并未得到充分保障。
一天的紧凑活动很快结束,留在心中的,有沉重,也有感动。面对前所未遇的核灾难,在遭遇生计、家庭和社会心理和文化创伤的境况下,日本市民、NGO和社区组织并未放弃努力,表现了积极自救的精神。福岛核事故的危害和应对将是长期困扰日本社会的一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岛不应该被淡忘,而应成为全球严肃反思核能未来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起点。
3.11以来,如此规模的国际代表团到访福岛,与当地居民交流尚属首次,活动的组织者、“和平之船国际”的创办人吉岗达也(Yoshioka Tatsuya)希望代表们将当地的消息带出日本,促使全球共同关注福岛的境况。他说,“我认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我们将持续组织这样的活动。”
 表情
表情
 最热
最热